 |
相關閱讀 |
戊戌變法的另面
 |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 簡體 傳統 |
撰文:茅海建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自序 盡管從廣義上說,戊戌變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相關的史料也極多,一輩子都無法讀完;但若從沿革的政治意義上去分析,戊戌變法大體上就是“百日維新”,是一次時間非常短暫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動著北京、在政治上層,且只有少數人參與其間,絕大多數人置身事外,聞其聲面不知其詳。又由于政變很快發生,相關的人士為了避嫌,當時沒有保留下完整的記錄,事后也沒有詳細的回憶。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毀。也就是說,今天能看到的關于戊戌變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康有為、梁啟超,政變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關于戊戌變法的著述,也成為后來研究戊戌變法的重要史料。毫無疑問,康、梁是當事人,他們的著述自然有著很高的價值,但他們著述的目的,不是為了探討歷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爭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著諸多作偽。康、梁作為政治活動家,此類行動自有其合理性,但給今日歷史學家留下了疑難,若信之,必有誤,若不信,又從何處去找戊戌變法的可靠史料? 臺北中研院院士黃彰健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員陳鳳鳴先生分別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和檔案館、中國第―歷史檔案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了大量檔案或當時的抄本,主要是康有為等人當時的奏折,揭示出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偽,對戊戌變法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當此項史料搜尋工作大體完成后,還有沒有新的材料——特別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來研究戊戌變法? 正因為如此,當我讀到“張之洞檔案”中關于戊戌變法的大批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尋多年的目標突然出現時那種心動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變研究計劃,專門來閱讀與研究這一批材料。 我在閱讀“張之洞檔案”的過程中,最為突出的感受是,這批史料給今人提供了觀察戊戌變法的新角度: 其一,張之洞,陳寶箴集團是當時清政府內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為主張革新的團體。他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看法,對變法的態度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戊戌變法是體制內的改革,須得到體制內主要政治派系的參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當人們從“張之洞檔案”中看到張之洞集團以及當時主要政治人物對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敵對態度,似可多維地了解變法全過程的諸多面相,并可大體推測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變法史研究,經常以康有為、梁啟超的說法為中心;而“張之洞檔案”中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讓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場來看待這次改革運動。兼聽者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變法中所犯的錯誤。 其三,由于這批材料數量較多,準確度較高,許多屬當時的高層秘密,可以細化以往模糊的歷史細節,尤其是歷史關鍵時刻的一些關鍵內容。這有助于我們重建戊戌變法的史實,在準確的史實上展開分析,以能較為客觀地總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也就是說,原先的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并進行了多次辨偽識真建立起當今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正面”——盡管這個正面還有許多瑕疵和缺損;那么,通過“張之洞檔案”的閱讀,又可以看到戊戌變法史實結構的“另面”——盡管這個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體的,多維觀察的重要意義,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對于閱讀歷史的讀者來說,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夠閱讀到歷史的“正面”同時又閱讀到歷史的“另面”的機會并不多。這是我的一種幸運。 導論 張之洞是那個時代官場上的特例。他有著極高的天分,使之在極為狹窄的科舉之途上脫穎而出,又在人才密集的翰林院中大顯才華。他深受傳統經典的浸潤,成為光緒初年風頭十足的清流干將。他尊崇當時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師傅的清流領袖李鴻藻(亦是同鄉,直隸高陽人),而李鴻藻則歷任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等高官,又使之身為疆吏而“朝中有人”。曾國藩、李鴻章雖同為詞臣出身,然以軍功卓著而封疆;張之洞的奏章鋒芒畢露,博得大名,竟然以發文章發達而封疆,實為異數。此種最為關鍵者,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睞,從殿試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員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數次關鍵的時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或顯或隱的“慈恩”。 “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十日之飲”、“申旦高談”,表明兩人(編者按:張之洞、康有為)有著很長而且很熱烈的談話。而張于此時花大量時間與康交談,實則另有隱情。兩人在馬關議和期間皆主張廢約再戰,在換約之后借助張變法自強,在此性情志向大體相投之下,雙方的相談也很成功,張當時對康的評價很高。由此,張決定開辦上海、廣東兩處強學會。其中上海一處,張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辦理,廣東一處交由康有為辦理;而汪康年此時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會由黃紹箕、梁鼎芬、康有為等人先辦。黃紹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張之洞的門生,侄女婿,時任翰林院侍講,恰在張之洞幕中。他當時不可能親往上海。梁鼎芬是張的重要幕僚,此時亦準備臨時回湖北。黃、梁皆是遠程操控,上海強學會實際由康有為一人主持。 康有為用孔子紀年,乃效仿基督教用基督誕生紀年,這是“康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現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圖。張之洞與康有為之間最重要的學術分歧乃在于此,然以當時的政治觀念而言,奉正朔用紀年當屬政治表態,立教會更有謀反之嫌,康此時雖絕無于清朝決裂之意,但此舉必引來許多不利議論。此在康似尚屬理念,在張則是政治。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為與張之洞之間有著兩個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間,南京的十多天大約是他們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靜的日子還維持了一段。梁鼎芬、黃紹箕奉張之洞之命還在勸康;大約從十一月起,裂縫越來越大,以致最后破裂。從此兩人再無合作。 從事情本身來探討,兩人破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兩人性格,康有為、張之洞皆是自我意識堅強的人,康不愿屈從權貴,而自認為是后臺老板的張決不允許康如此自行其事;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謂“康學”,這本是學術之爭,然到了此時,已成了政治斗爭,張也不允許將《強學報》變為宣揚“康學”的陣地。 張之洞精心籌辦的《正學報》,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詳。以我個人的揣度,其未刊原因大體有二:其一,《正學報》的班底皆有較深的學術功力,似此可辦一學園式書院(或近代書院),各自講學研究,千妍萬艷;而若要同心協力共辦一份政論性的報刊,未必如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康們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為總負責的梁鼎芬,其對學術精神的追求,可能會過于雅致而細碎,這作為學者當屬及其自然與正當;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處處計較,將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寫作。作為后臺老板張之洞,對報刊文論時有苛求,往往揪其一點而不及其余,切手頭事務極多,呈上稿件經常不能及時返回,這一作派明顯不利于刊物的定期發刊。其二,光緒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維新”開始之后,京師的政治局勢變動極快,這本是各類報刊充分成長的最好時機,可隨時發布評論或消息,且有眾多讀者而市場擴大;而《正學報》作為代表張之洞政治觀念與立場的政論性刊物,企圖對全國的思想和學術進行正確的指導,很難在紛亂的政局中,找到并堅持那種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場和學術態度。從前引陳慶年日記中可以看出,張之洞及其幕中人物雖在武昌,但關注的是京師,任何景象與氣溫的變幻,都會在他們心中激起重重漣漪。政治家與政治評論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種平靜的態度和適度的言論,以能在政治風波中保持其穩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評論家那樣,在政治動蕩中指引人們的前進方向。而到了秋天,政變發生了,變法中止了,此類刊物也頓然失去存在的條件和原有的意義。 如果張之洞入京輔政,他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很可能成為此期朝政的綱領;而他對康有為及其學說的敵視,將會全力阻止康有為一派的政治企圖。他對“迂謬”理念的反感,也將會全力阻止極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動。若是如此,清朝的歷史之中是否就會沒有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沒有義和團和庚子事變,而提前進行清末新政? 歷史沒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設。于是,治史者與讀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緒、萬般的感嘆和那種不由自主的暗自神傷…… 第一章 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在數量極其龐大的“張之洞檔案”之中,有數以百計的文件涉及戊戌變法,而能讓我眼前一亮、怦然心動者,是其中一件精心制作的折冊,木板夾封,封面的簽條寫“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石芝所藏”(以下稱《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的一些信件透露了戊戌變法中的重要內幕。 正當我為“石芝”其人感到極為困惑時,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的茹靜女士向我提供了情況:“石芝”很可能是李景銘,該館另藏有“李景銘檔案”8冊,裝訂樣式大體相同,也有3冊亦署名“石芝”;其中一冊題名已脫落、封套題為《李景銘存清室信札》者,頁內有紅色鉛筆所寫字樣:“信札共9冊。56、4、27萃文齋,共價60。00,總59號”。由此看來,《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原是李景銘所收藏,于1956年4月27日由近史所圖書館購自于北京琉璃廠舊書店“萃文齋”;又由于該冊題簽為《張文襄公家藏手札》而從“李景銘檔案”中抽出,羼入“張之洞檔案”。 李景銘,字石芝,福建閩侯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清末任度支部員外郎;北洋政府時期任財政部賦稅司司長、印花稅處總辦等職。他對清朝歷史較為熟悉,著有《三海見聞錄》、《閩中會館志》等書。然他又是從何處搜得這些信札,情況不詳。臺灣大學歷史系李宗侗教授的經歷,可能對此會有所幫助。李宗侗曾著文稱: 昔在北平,頗喜購名人信札,所積至萬余件,帶至臺者不過數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吾所注意與收藏家不同,收藏家偏重人與字,而吾則重內容,若內容重要,即片簡斷篇亦所不計。文襄遺物多經后門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諸肆甚近。憶曾購得兩木箱,雜有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與親筆電稿若干件,現回憶之,皆可謂為至寶矣。 李宗侗為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孫,他從地安門外舊物店收購了兩木箱的張之洞遺物,李景銘是否亦是如此?而李宗侗于1935年因故宮盜寶案離開過北京,他的收藏是否另有出讓? 《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貼有李景銘所寫的五張簽條:一、“張權,字君立,直隸南皮人,文襄公長子。戊戌進士。戶部主事,禮部郎中,四品京堂”。二、“此三紙系楊銳號叔嶠所寫。”三、“張檢,字玉叔,直隸南皮人,文襄公胞侄。庚寅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外放江西饒州府知府,升巡警道,署按察使。”四、“張瑞蔭,字蘭浦,直隸南皮人。文達公子,官□□道監察御史。”五、“石鎮,字叔冶,直隸滄州人。為文襄公內侄,官安徽候道。”由此看來,李景銘對張家的情況亦有初步的了解。 《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共粘貼張之洞家屬書信計24件,另有其門生楊銳來信1件。我之所以對其感興趣,是因為其中的7件,即張之洞之子張權來信4件(1件為全,1件缺一頁,2件為殘)、侄張檢來信1件、侄張彬來信2件(1件稍全,1件為殘)。這些密信寫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彬的一殘件寫于光緒二十一年),皆是向張之洞報告京中的政治情況,涉及戊戌變法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核心機密! 以下逐件介紹張之洞收到的這批密信,并結合“張之洞檔案,中親電報,加似背景的說明。 《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所貼第22件,是張權的來信。張權,張之洞長子,字君立,生于同治元年(1862),光緒五年(1879)中舉。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等人在京發起強學會。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他進京參加會試。張之洞對此十分關心,親筆寫了大量的電報;亦曾于四月十八日發電指示其殿試之策略。張權此次會試,中三甲第63名進士,五月十三日光緒帝旨命“分部學習”,任戶部學習主事。 張權到京后,除了應試外,張之洞也命其報告京中密情。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一日(1898年4月2日),張之洞發電: 京。化石橋。張玉叔轉張君立:四數已匯,到否?場作速鈔,即日交郵政局寄。勿延。近事可詳告。壺。卅。 “張玉叔”,張檢,后將詳說。“壺”為引之洞發電給親屬及密友的自稱。四月初七日(5月26日)又發電: 京。化石橋。吏部張玉叔轉交張君立::榜后何以總無信來,奇極。即日寫―函,交郵政局寄鄂。行書即可,不必作楷。壺。陽。 “近事可詳告”、“即日寫一函”等語,說明了張之洞交待的任務。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即會試、引見各項結束后,張之洞發電張檢、張權: 京。張玉叔、張君立:急。分何司?即電告。前交郵政局寄《勸學篇》一本,當早接到。有何人見過?議論如何?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韜、叔嶠與之異乎?同乎?眾論有攻擊之者否?即復。壺。宥。 “仲韜”,黃紹箕。時任翰林院侍講。“叔嶠”,楊銳,時任內閣候補侍讀。兩人皆是張之洞在京最親信的人,這封電報中開列出張之洞所需了解的情報內容。除了私人性質的張權分戶部后又掣何清吏司外,主要有三項:《勸學篇》在京的反應;二、康有為、梁啟超在京的活動;三、黃紹箕、楊銳與康。梁的關系。至于第三項,很可能是張聽說黃、楊等人參加了康有為等人組織的保國會的部分活動。六月初三日(7月21日),張之洞再電張檢、張權: 京。化石橋,張玉叔、張君立:急。折差寄《勸學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韜、百本交叔喬,百本自留,親友愿看者送之。康氣焰如何?黃、喬、楊與康有異同否?戶部難當,只可徐作改圖。堂官已見否?前電久未復,悶極。速復。壺。 由此可知,張之洞為《勸學篇》在京發動了巨大的宣傳攻勢。“黃”指黃紹箕,“喬”指喬樹枏,“楊”指楊銳。張之洞再問此事,仍是保國會的傳聞,他還沒有收到張權的回電。 張權的這封密信,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寫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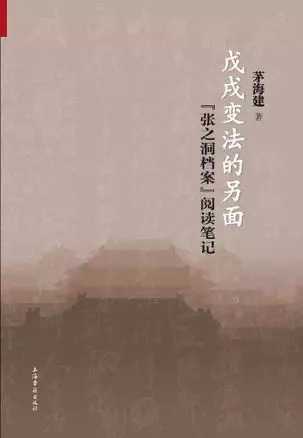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33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