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硅谷深處的憂慮三篇:時間篩選了誰、未知的自由~Google X、誰喚醒了惡魔?
 |
>>> 春秋茶館 - 古典韻味,時事評論,每天清新的思考 >>> | 簡體 傳統 |
硅谷深處的憂慮(1):時間篩選了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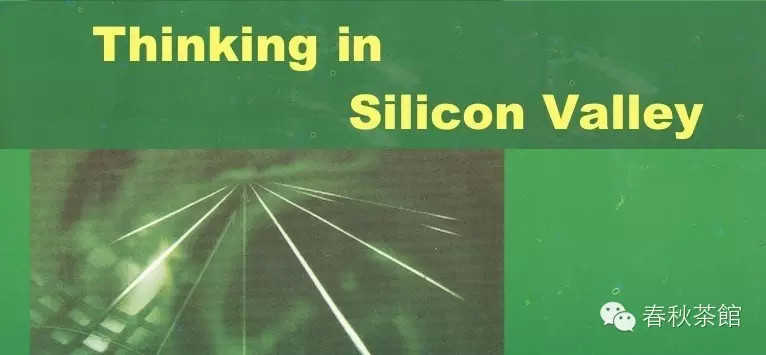
去年,在36氪硅谷站的Demo Day上,我有幸結識了一位優秀且年輕的女性創業者,Erica。在我看來,她創辦了一家非常了不起的技術型公司,TCPEngines,其核心產品是一種新穎的算法,可以被用來增加任何網絡的數據吞吐量(throughput)。在交談之中,我可以感受到她盈盈一笑的自信與輕松,但同時也能感受到,她那纖細的肩膀上正扛著令人窒息的壓力。創業,即使是對于她這般優秀的人來說,也充滿了各種不可預測的未知。盡管我主觀上相信,她可以在這條道路上走向成功,但所有所有的一切都仍需漫長的時間來檢驗。
人們常說,時間是一面篩子,但這面篩子并不總是汰沙而存金,尤其是在硅谷高科技的商業史上,有許多曾經代表了某個時段的最先進技術,竟爾未能在商業戰場上生存下來,著實令人唏噓。當然,現在的我們知道了營銷包裝的重要性,知道了用戶體驗的重要性,知道了生態系統的重要性,也知道了華爾街靠山的重要性,但這一切在十幾、二十幾年前的時候,并不如此簡單易懂。
然而,即便你深刻理解了上述所有的一切,并且能力過人,你依然有可能在硅谷收獲一個“失敗”的結局,因為在硅谷創辦自己的高科技企業,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成功概率極低極低的樂透游戲。
硅谷最著名的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YC)曾給出了這么一個事實:從YC畢業的511家初創公司,在經過5年之后,只有37家公司被認定是“成功”的[1]。這里,YC對“成功”的定義是:價值超過4000萬美元。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標準,被美國的許多企業家和投資人認可。37 / 511 ≈ 7%,也就是說,另外93%都是失敗者。
YC是硅谷頂級的創業孵化器,其孕育出的初創公司,可謂星光閃耀,有:OMGPOP(被Zynga以1.8億美元收購),Reddit(一個基于新聞的社交BBS,估值2.4億美元[2]),Airbnb(在線短租網站,估值25億美元[3]),Dropbox(云存儲服務,估值超過40億美元[4]),等等。YC每年提供兩次入駐培訓,總共會收到數千份初創團隊的申請,其中只有3%~5%的幸運者能夠雀屏中選,“入贅”成功。由此可見,想從YC這條路徑上獲得初創成功,其比率約在0.21%~0.35%之間(3%x7%~%5x7%),而失敗的比率超過了99.6%。
當然,這只是來自YC的數據,但我們沒有理由去相信那些與YC無關的初創企業會有更大的成功概率,就像沒有人會認為來自杭州師范學院的學生會比北大清華的學生更容易成功:)
即使一個初創企業成功邁過了5年的檢驗期,后面的道路也還是荊棘密布。如果以“三十而立”來做為硅谷高科技企業的“高壽”標準,那么一個公司能夠創業成功,并“善始善終”的概率就更加微乎其微了。下面的例子,講述了一個曾經市值超過兩千億美元的巨頭公司,卻最終倒在了二十八歲年齡的關口。它的名字叫做Sun Microsystems。
2012年,有一次,我去位于Menlo Park的Facebook總部,不經意間,在Hacker Way的入口處,看到了這個園區上世代的主人Sun Microsystems所遺留下來的標記:公司門牌的正面是Facebook的“Like”標志,但門牌的背面卻是Sun的標志。起先,我稍有驚詫:難道Facebook不應該把Sun的痕跡完全擦抹干凈嗎?而后,我又有點兒明白了些什么:或許這是一種最佳表態,即能對故園主人的過往功勛以致敬,也能提醒后來者以前事之不忘。

Sun Microsystems創立于1982年,成名于上世紀90年代,在計算機產業的軟硬件方面各有一個扛鼎之作:Java軟件平臺,和基于SPARC處理器的高端服務器。在2005年,Sun推出了網格計算(Grid Computing)服務器領域的巔峰之作,被譽為“黃道星陣”的Sun Grid,裝配有3000個CPU,像是太陽系里3000顆璀璨的星辰。
然而,在“黃道星陣”面世之后,Sun沒能改變世界,反而陷入了連年虧損,近乎破產的境況,直到2010年被覬覦Java和服務器業務已久的Oracle以74億美元收購,價格僅值巔峰期的3%。Sun的兩個巨型園區,一個賣給Facebook,另一個歸于Oracle。唉,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像Sun這般強大的公司,技術、資金、人才,無一欠缺,竟還是失敗了。類似的例子,在硅谷還有很多:3COM、SGI、3dfx(3D顯卡的開拓者),等等(Intel, Microsoft, in the future?)。
好,現在回到本節的標題,在極其艱難的創業或商業道路上,時間的神諭究竟會選擇誰走向成功?創辦一個成功企業的方法,真的可以從那些MBA的教材里學到嗎?
我做為一個Geek,真地想把那些MBA教材統統燒掉。先讓我用略帶Geek味兒的描述來談一談“成功與失敗”。
從模式識別的角度來看,“成功與失敗”貌似是一個分類問題(Classification)。如果你熟悉機器學習話,你一定知道用一些線性算法來處理分類的問題,例如SVM(支撐向量機)。然而,"成功與失敗"的分類之難,在于其參數的維度太高,幾乎是無窮的。也就是說,你不可能設計出只有一百個參數的分類器,來解決有上千億參數的分類問題。
同樣的,對于Sun的覆滅,想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邏輯性答案,自然也是不可能的。每一個公司的功敗垂成,都牽扯了數以無窮的主客觀因素,甚至還有無法描述的“運氣”成份參雜其中。
倘若非要回答本節標題的提問,我寧可說:沒有誰可以笑到最后,時間會讓每一家公司都走向失敗與消亡,宛如我們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
的確,這就是時間對我們“注定殘酷”的篩選。當有一天,硅谷里滿是黃沙與落日的時候,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能回憶起那些孤獨可愛的創業者,她/他們的青春就埋在這里,夢也埋在這里。
硅谷深處的憂慮(2):未知的自由~Google X

我去過很多地方,但也有許多地方未去,我并不是為了去享受旅行的樂趣,而是為了獲得某種未知的自由。每一次,在出發收整行囊的時候,我都會有種奇妙的感覺,仿佛是宇宙洪流要把自己向世界的彼方推送,而那個“彼方”卻充滿了未知,以及天然的自由。在我看來,人生即是旅行,蕓蕓眾生,不過兩種人而已,自由的,抑或不自由的。
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復一日地做著重復性工作,這當然是沒有自由的;而另外一些人,卻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每一個細小的發現,都會重新標定整個人類的知識邊界,這在我看來,是“自由”的究極之境。確切地說,這是一種“未知的自由”,因為不曉得路在何方,便會有無窮多種選擇的自由。在信息論里,以“熵”(Entropy)來描述某個系統的自由度,簡單說來,確定性工作是沒有自由的,相當于“熵值”為0;而選擇性愈多,那么系統的“熵值”愈大,自由度也愈大。
通常,我們把這些探索未知的人稱作研究員,或科學家。對于巨型科技企業而言,科學家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為這些企業有雄厚的資金儲備,并不急于在某項產品上獲得短期效益,往往要規劃十幾年之后的“超級產品”,這種工作,工程師是無法勝任的,需要頂尖的科學家來探索那“未知的自由”。
對“自由”的探索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每一項新發現都極其艱難。然而,這艱難漫長的探索過程,在本質上,卻與企業的目標背道而馳。每一個企業,因其固有之商業屬性,無可避免地要以追求金錢利益為目標,而且利益越大越好,過程越短越好。隨著全球商業競爭的加劇,當年那些巨型科技企業也不得不面對現實,重新思考“自由探索”的必要性。
事實上,自2008年以來,科技巨頭們正在慢慢剝離自己的研究(Research)機構,有些改之為研發(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機構,有些干脆以減員關閉了事。舉例來說,IBM的裁員已成每年例行之事,僅在今年就計劃裁員13000人[1],其中位于德州的半導體研究機構里就裁去了上百人之多[2],這在當年那個以Power PC引領世界處理器潮流的IBM來說,幾乎無法想象。另一個此前從未拿研究院開過刀的巨頭,微軟,也在今年關閉了位于硅谷的研究院,波及50名研究員,占研究員總數的5%[3]。

兩大巨頭尚且如此,更別提諾基亞、摩托羅拉、HP、AT&T、朗訊,這些正在走下坡路的企業。原來被認為是最穩定的科學家們,也變得惶惶不可終日。無怪乎,工業界里有種論調:科學研究,正以宿命之姿走向消亡。
真的如此嗎?回答是否定的。這世上,至少還有一個企業,正在雄心勃勃地向長期研究投下巨額賭注。它,就是Google。

Google于2010年,以“未知”之名,創建了秘密實驗室~Google X(X的意思是:unknown)。Google X座落在Google園區里一個不起眼的邊緣處,三層的小樓,沒有任何標識,你甚至以為這里只是Google的一個倉庫。當然,外表的平淡,并不能掩飾其內有的巨大張力。按照Astro Teller(Google X的實際負責人)的說法,Google X的目的是“以十倍的量級來提升現有技術,并打造如科幻一般的解決方案”(improve technologies by a factor of 10, and to develop science fiction-sounding solutions)[4]。
我們先來看看Google正在進行的幾個研究項目:
Google Glass:開啟了穿戴式設備的熱潮;
Driverless Car:集成多項先進技術于一體,為人類未來二十年的智能化做出鋪墊;
Project Loon:通過氣球技術,要讓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上網;
Project Wing:以無人機技術,使得城內的快遞時間縮短到分鐘級別;
Calico:研究“長生不老”之藥(Calico并不隸屬于Google X)。
這幾項研究,在短期內都無法帶來金錢上的利益,但卻能夠在未來極大地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其它企業研究院不同的是,Google X的項目,常常需要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員一起研究,而且這些領域并不僅僅局限于計算機科學。現在,Google X約有250名人員,他們中間有哲學家,藝術家,巡山員,機械專家,甚至還有一名研究員曾經獲得過兩次奧斯卡獎(Special Effects)[5]。就連Google X的主管,Astro Teller,除了是個人工智能科學家之外,還是個科幻小說家。
通常,我們對科學家的定義是:對越來越細小的領域,知道的越來越多(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6]。然而,這并不是Google X要極力招攬的對象。Google X更傾向于吸納一些有“哲學思想”的人進來:那些“對越來越宏大的領域,知道的越來越少”的人(Know less and less about more and more,相當于“無招勝有招”的境界)[6]。
其實,單就Google X實驗室而言,它的創建,本身也體現了“對未知的探索”,因為Google X這種揉雜了藝術和科學的研究形式,此前并未出現在任何其它的研究院里。也就是說,工業界的科學研究并沒有走向消亡,它不過是被移植到了人文與藝術的“花園”里,升華到了遠超以前的高度。
這,就像是一棵小小的鳶尾草,原本孤懸在峭壁之上,當被采摘下來,種在肥沃的花田里時,將會開出絢爛至極的花朵。
[1].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bm-layoffs-expected-2014-2
[2].http://www.myfoxaustin.com/story/22583328/ibm-job-cuts
[3].http://spectrum.ieee.org/view-from-the-valley/at-work/innovation/the-last-day-of-microsoft-research-silicon-valley
[4].http://www.wired.co.uk/magazine/archive/2013/11/start/destination-moon, Oct 2013.
[5].http://www.fastcompany.com/3028156/united-states-of-innovation/the-google-x-factor
[6]. 引自John M. Ziman的名言.
圖1.http://www.pitme.com/pitme-labs/
圖2. [3].
圖3.http://ad009cdnb.archdaily.net/wp-content/uploads/2013/10/525f0533e8e44e245100000a_secret-google-project-could-transform-construction-industry_googleplex.jpg
硅谷深處的憂慮(3):誰喚醒了惡魔?

我想先從一個流傳的故事來開始今天的探討[1]:
“在山里,住著一個農夫,靠自耕自種為生,但有一群野豬,經常出來啃吃農夫的莊稼,農夫試圖消滅這些野豬,便購買了獵槍,整夜地守在田地旁邊,一俟發現野豬,便開槍射擊。但這種方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因為田地很大,野豬又非常狡猾,不會固定地出現在同一個地點。農夫偶爾能打死一只野豬,但依然無法避免農田被啃的悲劇。
后來,農夫想出了一個高明的辦法。他把農田里最好最甜的玉米,摘下來,堆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引誘野豬來“免費”吃。起初,野豬們很有戒心,但吃了幾個月的甜玉米之后,發現非常安全省力,既不需要自己去“摘”玉米,又沒有農夫來襲擊,于是野豬們放心大膽地吃了起來。又過了幾個月,農夫準備收網了。他開始在外圍筑起高大厚實的木板,每天只筑一個木板,野豬們也沒有意識到危機。直到某一天,農夫把最后一個木板釘在地上,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圓形豬圈。此時,野豬們知道中計,想從豬圈里逃出來,但為時已晚。更何況,經過幾個月的飽食,野豬都變成了肥大笨拙的家豬,喪失了一切的戰斗能力。剩下的事情,就是,農夫一天拖一只出來...”
這個故事試圖說明一個道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一件事情,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免費”的,那么它一定隱藏了某種代價。
現在,我們來體會一下正在互聯網行業里大行其道的“免費”模式。這種新型的商業模式,正被一些大佬贊許為顛覆性的“互聯網思維”。然而,在我看來,這種商業模式是建立在一種“虛偽”之上。所謂“虛偽”,是指互聯網企業把“追求商業利益”的本質多繞了幾個圈圈,隱藏到消費者的視野之外。當然,這種“虛偽”并無任何貶義,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

其實,這種免費模式也并不新鮮熱辣,它在第一代互聯網公司誕生的1994年(以Yahoo為代表),就存在了。當時,人們不需要付費購買報紙,就可以自由地從Yahoo網站上獲取最及時的新聞。隨著Google的出現,這種模式被發揚光大。人們不僅可以從Google那里看到免費的新聞,更能獲得免費的郵箱、免費的云存儲、免費的視頻、免費的辦公軟件、免費的操作系統、免費的地圖......Google幾乎免費了一切。當然,這些“免費”是有代價的:人們需要把自己的“隱私”交給Google來管理,更準確地說,是交給Google那龐大的計算機系統來管理。
從模式識別的角度來看,一個人的某種“隱私”,相當于這個人的一種“特征”(feature)。一個真實世界里的人,在虛擬的計算機世界里,完全是由他的特征來表述。在理想情況下,如果獲得了足夠多的特征,那么計算機便可以完全洞悉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通俗地說,計算機具備了讀心之術。順其自然的下一步,就是計算機的“控制之術”了。
幾天之前,Elon Musk(特斯拉汽車CEO)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講座上,說出了他的担憂: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喚醒一個無法控制的惡魔[2]。(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summoning the demon. There’s the guy with the pentagram, and the holy water, and he’s like — Yeah, he’s sure he can control the demon? Doesn’t work out:我們正在用人工智能召喚起一個惡魔。就像有一些家伙,覺得自己能夠通過圣器和圣水來控制住惡魔,但實際上,這不可能。)
在我看來,Elon Musk的話并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可能。
其實,我們現在的許多行為,都已經被計算機所掌控。我每天收看的新聞,是Google推薦的,我網購的商品是Google推薦的,我預訂的旅館是Google推薦的,我去的餐館是Google推薦的,我開車的路線是Google推薦的,甚至連我旅游的日期也都是Google根據機票價格來優化安排的。我不費心,很省力,基本上快成為一頭“家豬”了。假如,我是說假如,Google想謀殺我的話,它只需要把我導航到懸崖上就行了 :<
如果說,第一代的Yahoo還只是把“玉米”堆放起來的話,那么第二代的Google已經開始在玉米周圍建筑“木欄”了。當然,現在離最后一塊木板還有很長的時間,但這種趨勢卻是潛在的,甚至是無法扭轉的。
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表面上看來,是人工智能技術喚醒了惡魔,但人工智能技術是要建立在我們隱私的大數據之上,而獲取我們的隱私是要建立在所謂的“免費”模式(互聯網思維)之上。但,為什么“免費”模式會興起呢?這是因為我們人性深處的潛藏之惡嗎?(比如,懶惰,逐利,虛偽)當我們體察到了人性深處的“邪惡”時,還會指責那個遙遠的“惡魔”嗎?
或許,是我們喚醒了惡魔;也或許,我們自己就是那個惡魔。
[1]. 該故事出自《洛克菲勒留給兒子的38封信》一書。這本書有可能是偽作,但本文只是想講述一個故事,而并不去考證這本書的真偽,也無意以洛克菲勒來妝點門面。
[2]. http://techcrunch.com/2014/10/26/elon-musk-compares-build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to-summoning-the-demon/
圖1. http://www.bidnessetc.com/28029-artificial-intelligence-is-a-demon-that-will-kill-us-all-elon-musk/
圖2. http://www.clickonf5.org/7023/google-empire-dont-be-evil/
作者注:該系列的第一卷探討當代硅谷的人文,第二卷將深入探討一些技術
硅谷寒 2015-05-14 10:05:13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