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條微信讀完《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文/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邵燕祥稱自己近來忙于“過日子”。這“日子”或許不限于眼前,還包括過往歲月——對于一個已屆八十高齡的老人來說,后者可能更為緊要。 新作《一個戴灰帽子的人》,記錄了邵燕祥從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歲月。“比起那些已經過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喪失了一切公民權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謂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說簡直在享受著被照顧的優遇了。——我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序言里,邵燕祥慨嘆道。 1960至1961年 饑荒陰影下,官僚大吃大喝 邵燕祥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月的秋風里,從勞動改造的農場,回到了北京。共和國“十周年大慶”剛過,他感受到的卻是靜——“出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寧靜”。他回到原單位中央臺工作,不同于公共場所的冷寂,機關里涌動著“反右傾”的熱潮。 1960年,邵燕祥被叫到說唱團幫忙,主要幫助相聲組記錄傳統相聲。在這里,他把故事改編成相聲,搜集資料,出過不少主意,如今回憶起來,感覺“亂紛紛”。 這一年,大饑荒的陰影已經顯現。上半年,邵燕祥在廣播學院上輔導課,從十一點起,站在講臺上兩腿就發抖,直到下課鈴響。為了補充機關食堂蔬菜的不足,不得不去“生產基地”種菜,邵燕祥甚至在大家的提議下寫了《種菜突擊隊之歌》,譜曲后,每天唱著這支歌下地。 有了“生產基地”,小官僚們時常飛車來去,以視察農場為名,直接去開小灶,大吃大喝。邵燕祥不能容忍這一類事情,他寫信給機關領導,反映這一情況。得到回復,其中說:“此風確不可長。當時我對他們說了,看來還要作進一步的規定。” 同年冬,邵燕祥的夫人謝文秀已懷孕半年多,想補充些營養,兩人商量后決定下一次館子。像去偷嘴,他們乘公交車西行,到公主墳下車,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買了飯菜,一聲不語悶頭吃。 這一次奢侈的舉動,讓他們覺得對不起父母,而沒有了解到“幾億衣食父母的農民正在大饑荒中忍受折磨”。當時,他們以為農村比城里強得多,理由是農民不但有自留地,利用宅旁園地蒔弄些瓜菜,更為方便、得心應手。 “可悲并可詛咒的,是我和相當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著城鄉二元化的蔭庇,同時又受報喜不報憂的輿論蒙蔽,長期對這樣悲慘的實況幾乎一無所知,因而仿佛毫無心肝地茍活著。”半個世紀以后,邵燕祥寫道:“作為這樣幸存的生者,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 1961年,饑荒陰云依然籠罩。物質需求之外,邵燕祥不失精神追求,用工資訂閱了《文藝報》、《人民文學》、《世界文學》、《文學評論》等報刊。也是在這一年,政府把一船從國外買來救急的度荒糧食,因為阿爾巴尼亞的求助,而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送給了這個“戰友國家”。 ▲邵燕祥與夫人謝文秀(紀紅攝) 1962至1963年 不時在山水市井間游走 1962年,光景好過前一年,用不著七八塊錢買一斤雞蛋了——那時,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不過三十來塊錢。這時候,學者似乎也有了閑情,與《紅樓夢》有關的活動、展覽、節目不斷涌現。 一件好事落到邵燕祥身上。內蒙古自治區紀念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文化界組團前往祝賀,其中包括邵燕祥。他們去鳴沙山,在沙上滑行,邵燕祥悄悄寫了一首七言古詩,以為是此行最大的收獲。此后,去青冢吊王昭君,去包頭拜五當召,“從旅行的角度看,真的不虛此行”。 從內蒙古回來不久,9月,邵燕祥被派往南京,本來是去某部隊文工團“取經”,卻成了訪古之游。坐在清涼山一塊石頭上,秋風拂面,一只蝴蝶飛到眼前,一起一落,邵燕祥得句“一蝶如葉墜秋風”。“真是多年難得的閑情了。”他寫道。 哥哥燕平定居南京十五年。在飯館,他給邵燕祥點了條魚,自己不動筷子,只是看著弟弟吃。在這魚米之鄉,大饑荒的痕跡雖然并不明顯,但余悸猶存。不過,此時,在邵燕祥眼里,“江山還是美好的”,“人生還是美好的”。 煩惱亦不斷。1963年新春,邵燕祥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單位的新聞人物。唐弢在《文學評論》雜志上發表《關于題材》一文,批評邵燕祥的作品《小鬧鬧》為“煩瑣的家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合的典型”。此外,還有數篇涉及《小鬧鬧》的批評文章。不過,只是在業內流轉,并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反響。 當年夏天,瞿希賢譜曲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傳唱全國。這首歌震撼了邵燕祥的心,激發他創作的沖動,寫了一首歌詞,寄給瞿希賢。她回信說,因為已經寫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想重復同一主題了。這樣的回復,贏得了邵燕祥的尊敬,更讓他尊敬的是瞿希賢晚年的反思。她對一位作曲家說過,看到一個材料,才知道大躍進年代中國餓死了很多人。當時,她在甘肅“引洮(河水)上山”工地上,應縣領導之請寫了歌,這支歌當即唱響工地,后來知道工程整個癱瘓,當地死了不少人。 “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多年后,瞿希賢說。 1964至1965年 像荒誕派或黑色幽默小說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此前,赫魯曉夫下臺。對于邵燕祥來說,個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面臨的“大事”是夫婦倆同時外出半年,參加“四清”(全名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把一雙年幼的兒女留給年屆花甲且病弱的母親,怎么辦?幸好,有一個熟識的老太太答應來給母親作伴。 邵燕祥隨隊前往河南安陽集訓。他聽說河南的基層干部,每逢離家上縣開會,比如三級干部會,離家時都像“三吏”、“三別”似的,留下不叫遺言的遺言,而且把頭發剃光,因為到了會上,常常不免要被揪著頭發批斗,甚而往墻上撞。不過,這一次集訓,倒沒有打人、揪頭發事件發生,“整個很文明”。 年底,“四清”工作隊進村,邵燕祥被派往一個叫西宋莊的村子。他訪貧問苦,空閑時寫下不少“緊跟時勢”的作品,如《派飯謠》,“寧吃貧下中農的蔓菁飯,/不吃地主富農的炒雞蛋。/寧吃清白干凈的蘿卜片,/不吃來路不明的羊肉面。” 事實上,這里還沒擺脫饑荒的影子,進村后,沒見過地主富農拉拢,村里人也許勉強能拿出炒雞蛋,羊肉面是絕無可能的。不過,之所以這樣寫,只因自以為是在寫詩。“現在想起這些,盡現當時的猥瑣尷尬之狀,像是荒誕派或黑色幽默的小說。”在新作中,邵燕祥寫道。 1965年4月,距告別西宋莊只有一個月,邵燕祥心情輕松而自由。他寫下一首《采桑子·野望》,最后說:“無限春光有限詩。”誰知道,過了一年,這首詩成為批判對象,“文革”的狂風暴雨劈頭而來。 本文根據《一個戴灰帽子的人》重述整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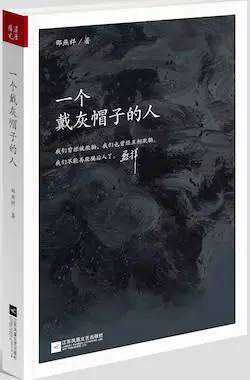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0:2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