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 于一爽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作者自拍效果圖 《同學聚會》講的是一個沒什么出息的中年男人"我"參加大學聚會碰見了當年的女同學,相互說得最多的話是"你胖了"、"你也胖了"。之后又見了一次,女同學在精神上受制于人已經難見當年面貌,只能借著酒勁兒拼命回憶,而"我"已經不想搞她,于是匆忙告別,去找了小姐。 我不相信也得相信,在我們見面之后不到一年,余虹就死了。她跟一男的在京津高速上鉆到一輛大解放里頭去了,聽說腦袋被削掉了一半兒。當老牛跟我說余虹腦袋削了一半兒的時候我只是覺得一陣惡心,她那個腦袋呀--我一點兒沒因為舊日感情而有絲毫悲傷,我倒想起那次同學聚會。但這并不能緩解我的惡心。 我叫劉明,屬鼠的。一般老喜歡跟人說我屬耗子。1972年出生的,眼下,我就快40了。如果2012只是開個玩笑的話,我倒真覺得失望,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的2013我能有什么改頭換面的地方。我在一家影視公司做文學總監。聽聽,聽著還真不錯是吧,可是這年頭,總監比耗子都多,何況我們公司,大老板喜歡女演員,小老板成天忙著給大老板找女演員。誰想做事兒啊?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也能混得挺好。誰要看見我現在這副德行,真想象不到我當年也是中戲的。往前倒退十幾年,中戲出來的可不像現在如過江之鯽,那會兒都特有理想,如果想到日后終會一事無成恐怕倒會活得老實點兒。 大概10個月前,也就是去年秋天,我接到老牛電話,說,聚聚?我開始沒聽明白,他又說,聚聚?老牛當年和我一班,我說,什么意思?他說,就快2012了,咱們老同學再不見就見不著了。 我當時掛了手機就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沒想到,我同學都這么庸俗了,聚聚就聚聚,提什么2012,又不是90后,真死了還有點兒可惜, 畢業十幾年,我正經聯系的沒幾個,跟老牛有時候打打電話,他在 社會上小有名氣主要是因為當年在劇組騷擾小姑娘上了新聞頭條。要我 說,真得怪這土鱉運氣不好,那會兒是90年代,壞風氣剛剛抬頭。 雖然啐了口唾沫,我還是同意去了。一方面閑著也閑著,二方面我 有點兒想重溫舊日情懷。這可真夠惡心的。 我們的同學聚會定在了三里屯的"一坐一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 其實也不是老牛提議的。說來也是,老牛混得也不怎么樣,他大概是想 拉一個更不怎么樣的墊底兒。 這么一想,我就舒服多了,也不像剛邁進門檻時候那么緊張了,自 我羞辱真叫人覺得輕松。 1994年我剛畢業,還是個挺利落的瘦子,現在肚子大得打炮兒都 得先挪后頭去。我媳婦兒跟我結婚十幾年,對我的長相先是從看不起到 壓根兒就不看。有時候我光著個膀子在屋里轉悠,她就跟沒這個人似的, 轉悠暈了她來上一句:"瞧瞧,瞧瞧你這肚子!" 我每次都說:"是,我哪兒像一搞文藝創作的啊,說我是劉屠戶還差不多。"那天進了包間,猛一看我真以為進錯屋子了。老牛挺大聲來了一句:"劉明,別找了,這,這來!"我才恍過神,這一屋子婦女還有大叔。歲月是把殺豬刀。 后來我找老牛坐著。又跟幾個人打招呼。應該是老年癡呆提前了, 張弛跟我說他叫張弛,我思緒萬千半天,張弛誰啊?我們班的?艾丹也 說:"嘿!劉明,你也不理我。"我哼哼哼!心想,艾丹?咱認識?接著又 哼哼哼,最后直接喝酒。我真跟你們這種混蛋做過同學,不能吧?當我這 么想的時候,我總是摸摸自己滾圓的肚子,我也不是當年的我了,可我 還是不愿意那么去想。于是又喝酒,我一個勁兒跟在座的,少說得有十 幾個人吧,干杯,一杯接一杯,壓根兒就沒吃上一口。還跟幾個人遞了名片,有幾個一看我就笑了,嘿,跟我一樣,總監,咱比耗子都多。哈哈哈,越到后來越暈,高興得不得了。其實,也不是高興,可我總不能不高興吧。就這么硬撐著。真他媽沒勁透了。印象中,我還摸了一姑娘的手,也不是姑娘,婦女了,就坐在我左邊的左邊。我右邊是老牛,左邊是誰來著,忘了。左邊的左邊說自己叫余虹,她說你還記得我嗎?她說我喝多了。我說那咱倆喝了嗎?因為有時候見面真沒什么可說的,于是我摸了一把她的手。 我說:"余虹啊,你就是余虹啊,你怎么胖了?" 她說:"你也胖了。" 我說:"我胖得不成樣子了。" 她說:"可仔細看還是你。" 我說:"是嗎?那你再仔細看看。" 后來我們就什么都沒再說。因為我左邊的一直哼哼,說別胡來啊,你媽的,你把余虹都忘了。我說老同學了,敘舊,你們別鬧。其實我還想說我內心無限傷感,可是胖子好像不能傷感,尤其像我這種胖子,猛一看以為混得特好,傷感,一準兒以為是閑得蛋疼。于是我松開余虹的手,正好憋得尿急,我去了衛生間。跨過幾個人的時候,我還拍了拍他們的肩膀,當然我也知道,這個世界光拍拍肩膀顯然是不夠的。 從衛生間回來之后,我稍微清醒了一點。這主要是因為,我想起余虹是誰了。一方面是我們做過同學,另一方面是,她是我追過的挺多女孩兒中的一個。至于其他那些女孩兒都哪兒去了,我想她們跟我再沒關系。 于是我回到座位之后,跟我左邊的換了位置。就算我不換,我也能挨著余虹,局已經亂了,有人喝得七仰八歪,一個勁兒地回憶往事。老牛說當年身體可真好,夜里玩兒牌,早晨操場沒人,正好踢球,踢到十點來鐘回宿舍睡覺,起床就去喝酒。著另外一個老女人。 我喝了幾口可樂漱漱嘴,坐到余虹的左邊兒去了。當我咕咚咕咚喝可樂的時候,我覺得我又回到了當年。余虹好像酒量不錯,她兩頰紅撲撲的,一舉一動都看著挺清醒,她正往嘴里扒拉一碗米線。我點了根兒中南海看著,我喜歡看女人大口吃東西了,我覺得她們只有吃飽了才有力氣做愛。當然,我現在想這些也有點兒沒必要,別說做愛,趁我尚還清醒的時候,我想了一下,我跟余虹好像只是拉過手。 "來點兒?"余虹指著碗跟我說。她一定覺得我喝多了,她想讓我吃點兒。我把煙掐了,用她的筷子胡嚕了兩口。然后放下筷子又點了根兒煙。我說:"這一晃,我們得多少年沒見了?" 四周亂哄哄的,我的問題怎么聽怎么像個傻B。余虹一笑,當她一笑的時候,我覺得她還是有20歲的模樣,或者她 壓根兒就沒有20歲的模樣,因為我只見過當年所以一直那么希望。我覺得我不討厭她。除了我老婆之外的女人,我都不討厭。余虹說:"給我來根兒。"我給她點了一根兒,我還問她:"中南海行嗎,點兒八?"我覺得女 人都得抽那種細細的,這樣才對得起生活。余虹說:"少來。"她這么說的時候,紅撲撲的兩頰上長出一個小酒窩。少來,呵呵, 可愛極了。 "你好嗎?"她問我。 沒等我說,她就又說:"可是和當年想的不一樣。" 我說:"什么?" 她說:"很多事情。" 我說:"干嗎傷感啊?" 她說:"不啊。" 我問她生活得好嗎。她說,還不錯,可是干的事兒和當年學的沒一點兒關系。其實我壓根兒不關心她干什么,別說干什么,她不干什么和我有關 系嗎。我是想問,你結婚了嗎?余虹聽出了這個意思,說,我結婚了。接著她哈哈大笑,說就那么回事兒,挺好的,也挺有錢的。我說,那就好那就好,結婚就好,有錢比什么都強。我又說,我也 結婚了,不過唯一的區別是,她還有個孩子,她說是姑娘,快10歲了。我又一個勁兒地說那就好那就好,其實我心里想的是,如果還沒有孩子那你的現狀還不是最壞。后來余虹說要去衛生間,我說,走,一塊兒。當我們倆一塊兒往外走的時候,老牛起哄,好像他掉了顆門牙似的。 我說馬上回馬上回。光天化日之下我還能干什么啊我,關鍵是我也不想,當年都沒有的事兒現在就更不想有了。但是從衛生間回來之后,我跟余虹又在過道里多站了一會兒,她說外面清凈。我說都好都好。 在過道站著的時候,我們時不時就得側過身子給路人騰地兒,有時轉得有點兒猛,余虹就會貼我肚子上,不過馬上就又分開了。兩人東扯西扯也沒什么可說的,女人最大的話題是孩子,可是我對這個想都沒想過。她問我,你就沒想過要一個。我說我沒想過,我又說我真沒想過。 當年我發誓娶我媳婦兒的時候,我也是非常非常愛她,她當年也想生,我總說等等等等,好在她現在生不了了。要是生了,醫生說,就得等著變成一大胖子,挺難恢復那種。她要真成了大胖子,我們倆就更沒性生活了。當然這些都是我的心理活動,我可沒跟余虹說半句。 我只是說:"真快,可真快啊,那會兒在學校的時候咱倆也老戳在過道兒。"不了,要早點兒回家,小孩兒等著呢,改天吧,改天去我家玩兒。 我說那好吧,她說你可一定來啊。我說來。她又說:"哦,對了,咱可連個電話都還沒留呢,別回頭一分開又是十幾年。"我想,再過十幾年,人肯定就聚不齊了。要是再過兩個十幾年,全一堆兒一堆兒的了。 后來她跟我說了手機號,我給她打了一個,她說:"那,先這么著。你再跟他們玩兒會吧。我走了。"我說:"行吧,再約。慢點兒。到時候電話。" 當我跟她這么說的時候,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還能見面。 人總是得講點兒禮貌不是嗎? 余虹走了沒幾分鐘,我就喝多了,我覺得沒必要再保持體面,我跟張弛啊艾丹啊老牛啊的來了個大滿貫,誰是誰我差一點兒就都想起來了。 回家的時候沒有1點也有12點半了,我媳婦兒贈了我個白眼球就上床睡覺去了。我當時借著酒勁兒挺想做愛的,褲子都沒脫就往她被窩兒里擠。我媳婦兒倒好,來了句:"你別強奸我。" "強奸,要強奸你還不是分分鐘。"我這么說的時候,主要是在吹牛。接著,我就打起了呼嚕。好像還被誰踹了幾腳。我罵了"騷B"兩字,很快就做起夢來。 我的一天總是在這種事情中結束。 我很生氣她壓根兒沒問問我同學聚會的事兒,我雖不是什么金元寶可也不至于一錢不值。 不過我也就那么想想。因為第二天起床我媳婦兒還問我:"你昨兒罵誰啊,我騷嗎?"我當時宿醉未醒,我說我沒聞過。她使勁捶了我兩拳,又問我:"頭還疼嗎?吃不吃阿司匹林?"我勉強點了點頭。 那天之后很久,我的生活又恢復了一如既往的平靜。那種生活對我來說之所以平靜,主要在于太過熟悉。我每天出去吃吃飯喝喝酒看看本子有時還見見北影中戲的女孩子。年輕的女孩子可真好,她們總讓我覺 后來有一天,我正在家上微博的時候接到一個電話,沒有顯示我也不知道是誰。但是所有沒有顯示的號兒我都聽聽,我是怕錯過什么機會,我媳婦兒老說我賊不走空。 "喂?劉明啊。"電話那頭兒說。 "嗯……"我猶猶豫豫,我覺得電話線里頭的聲音也不是特別陌生。 "行了行了,一準兒把我忘了,我,余虹。" "什么啊,余虹啊。" * 幸虧她提醒了我,那天喝多了,壓根兒沒存誰的號兒。我又臭貧了兩句,意思說這么多天了就等著她這電話呢。當我表達這個意思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有點兒沮喪。我覺得何必呢。 余虹說:"要沒事兒,明天來我家吧。"我說明天啊。我想了想(其實明天我沒什么事兒,我哪天都沒什么事兒,可我還是想了想。)接著她又說:"我孩子、丈夫也在,不然你叫你媳婦兒一塊兒,隨便吃個飯。其實那天還挺想跟你多聊會兒。" 我說:"是啊,那行吧。"后來她給我發了地址,真沒想到我們住得這么近。至于我媳婦兒,我就從沒帶她出來吃過一頓飯。我還沒想好明天跟余虹聊點兒什么。有什么可聊的呢?我們都這么大的人了。 第二天晚上到了余虹家,果然沒見到她丈夫孩子,可我還是問了一句。她說他們晚點兒回來,她說要不要出去吃,我說出去吃吧,想吃什么,得我請。她讓我在客廳坐會兒,她去換身兒衣服。我說你忙你的,我轉悠轉悠。我說你家裝修得不錯啊(這肯定是我編的,他們家是老干部風格,我覺得傻透了。主要是我實在不知道說點兒什么)。余虹說:"你就編吧。" 她這么一說,我覺得都怪我沒話找話,接著我又看了看她客廳里的結婚照。她本人可比照片上老了挺多,我說:"累嗎?平時。"她"呵"了一聲,好像這根本不是一個值得認真回答的問題。"走吧。" 鞋的女人,我很喜歡。我們出了門兒,我們去了一家廣東館子。 余虹點了幾個菜,她說喝嗎?我說都行。都行的意思就是喝,不然我們相視而坐實在尷尬得要命。廣東館子都喜歡在墻上掛個電視機,在我沒有感覺喝多之前,我一直盯著看,各種新聞。余虹說:"你看這個世界上每天都發生這么多事情。可是我們還活著。" 活著。她竟然說了活著。我想她瘋了。另外我真搞不明白她為什么把我叫出來喝酒。就像我說的,她是我追過的眾多女孩兒之一,可也就是拉拉手。如果拼命叫我回憶的話,也許能想起來--當初,我們一起做了四 年同學,還有半年時間在一個劇組實習。90年代中期,我們一起在大興安嶺弄一個戲,每天收工的時候,我們就一塊兒吃飯喝酒聊天,聊到熱情澎湃的時候,她總是拽著我的手,說是要為祖國四化做貢獻……那會兒我還是個童男,有次在大興安嶺深處(聽聽,這可真夠抒情的,也沒準是我編的)我說,那咱倆好吧。 我都忘了余虹當時怎么說的了,她大概是說--好?后來我們又說這說那……不過都是過去的事兒了,我也不怎么想回憶。我真担心我無非是在 夸大當初那點兒好感。也許僅僅是人到中年生活了無新意總想重拾一點舊日時光。再或者說,搞一下,這容易得不得了。"劉明啊,"余虹說完"可我們還活著"之后好像還沒完,又說,"你現在生活怎么樣,幸福嗎?"我說挺好的。其實同學聚會那天我就跟她說過,挺好的真挺好的。至于幸福嗎,我早就沒那么幼稚了。無論怎樣我們都還活著。"吃菜,多吃點兒。"我跟她說。什么活著死了的,現在哪兒有人聊 總說:"劉明啊,我覺得你特有才,以后你要出名了可怎么辦啊?"我當時總說:"出名!你罵我呢吧,這個時代只需要一般好的人,像我這種這么好的,哪兒能出名啊!"于是余虹總說:"吹牛。"當時我還真不是吹牛,我當年就是那么想的。 "還記得咱倆當初一塊兒在劇組實習嗎?"余虹夾了幾筷子菜在盤子里搗來搗去說。"是啊。"我說,"那是什么戲來著?"后來我們就想了半天,我們把90年代中期的幾個電視劇都回憶了一遍,可是好像沒有一部是在大興安嶺拍的。再后來出現了短暫的沉默,以至于我們在一瞬間都不再相信,我是不是真的在大興安嶺深處跟她說過那咱倆好吧。 好吧,無論這是不是當真存在,借著酒勁兒,我們又聊了各自的生活。自從學校分開之后,大家就斷了來往。余虹說怎么后來就沒見啊。我呵呵一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沒見,應該是都忙,她叫我閉嘴。她說:"知道嗎?你那會兒挺好的。"我說:"是嗎?當初還沒大肚子呢。" "唉。"余虹嘆了口氣。 我最不喜歡女人嘆氣,好像生活很值得惆悵似的。我一瞬間覺得女人都是一路貨,我狂喝了幾口,喝酒不就是為了喝多嗎?我想到我老婆。我還是沒想起那個電視劇叫什么來著,我覺得一切都不存在。 我跟余虹說:"我多喝點兒,你少喝點兒吧。" 因為她也不年輕了,不年輕的意思是--當我借著餐廳的燈光仔細看她的時候,她眼角的魚尾紋兒也不比別的女人少。 余虹一個勁兒說沒事兒高興唄,后來又說你他媽別不喝啊。我說好好好。可是我真不知道,她威脅我干嗎?還怪里怪氣的。這就像當年她問我什么是好啊,氣得我啊!當年我一個童男,你問我好不好,我沒試 回到學校就跟一個低年級的女同學上床了。 我當時肯定是覺得好,特好,好極了,我當時應該是一點兒都不在乎余虹了。當時班上造謠說我跟余虹在大興安嶺談戀愛的時候,我跟余虹都不怎么說話了。那些年,可真奇怪。不過很快彼此各奔東西。 "唉,別提這些了,現在我們不都挺好的嗎?"我說。"好?是啊,唉,好嗎?"余虹說,"劉明,怎么混了十幾年,你把自己混成了一個胖子。"當她這么說的時候,我瞅了一眼自己的肚子,我真不知道我的肚子 怎么招她惹她了。 "這話說得,跟我媳婦兒似的。"我嘀咕了一句。 "你媳婦?你提你媳婦兒干嗎啊?那我再問你,你知道我丈夫哪兒去了嗎?"余虹暈暈乎乎地說。 "啊?"我哼了一聲,我知道她這會兒是真的喝多了,我說我哪兒知道你丈夫去哪兒了啊? "是啊,你怎么會知道呢?"余虹說。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越到后來我越玩命兒喝啤酒,好像我覺得自己肚子還不夠大一樣,我真想把它喝成氣球帶我飄到房頂兒上去算了。余虹趴在桌子上,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我一個勁兒地點頭。我越來越覺得她和我媳婦兒真沒區別。她和很多40歲的女人都沒區別,全搞不清楚自己丈夫去哪兒了。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操一下她,她會不會停止喋喋不休。不過我只是那么一想,我肯定不會那么去做。可是我如果不去那么做一下,她為什么叫我來呢?她僅僅是想找個胖子一醉方休嗎?我就這么等待著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當我想不出怎么辦的時候我都是這么辦的。 大概晚上11點的時候,餐廳的人陸陸續續走了。我說:"余虹啊,你不回家看看孩子。" 她說你傻不傻啊你,她跟她爸去外地了。 我說哦。 沉默了半天之后我問:"那你怎么沒去啊?" 她哼了一聲,好像我是個完全不懂婚姻的傻B。 * "那,怎么著?"我說,"我送你回去吧。" 后來我起身,結賬,又像當年在大興安嶺一樣,拉著余虹的手。她用手抓了抓頭發,頭發全給抓亂了,我很想給弄平,但是我沒碰她。這絕不是因為我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我聞著她一嘴酒氣,我突然覺得不必了。 余虹屁股緊緊貼著椅子,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我說:"關門了,換地兒吧。"我這么說純粹是為了哄她,哄她回家,然后我也回家。我知道這個晚上搞砸了。有時候真應該相信那句話--其實還是不見最好。我拉著她的手使勁把她拽起來的時候,她嘴里又念叨我的名字。可是她都沒睜開眼睛看一下,如果發現劉明早就是個胖子的時候,她一定 覺得沒意思透了。當我把她拽到門口的時候,余虹說:"包。"她這么一說我就放心了,我讓她靠門框上等著,我重新跑到二樓去 把她的包拿下來。這點上,她和我媳婦兒真是一路貨,她們那包好像都是個什么牌子,我也不懂,我反正知道:貴的就是好的。女人想要的都是對的,我從不跟女人爭論這些,這主要是因為我能給她們的不多。 當我重新跑到樓下的時候,氣喘吁吁,余虹自己已經攔了一輛車坐在后面,打著雙閃,她這是也想讓我坐進去嗎?然后呢?我想了一下。我打開車門,她的頭靠在椅背上,頭發把眼睛遮住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還醒著,我欠著身子把包放她腿上,又使勁敲了兩下叫她拿好。她"嗯"了一聲,她把擋住眼睛的頭發別在耳后說:"劉明啊,我喝多了,對不起。" 我說:"哪兒啊,你一人能回去嗎?" 其實我這么問就已經不想送她回去了,否則我會跳上車什么都不說。或者直接緊緊抱著她。可是我不想,現在不想,趁著酒勁兒也不想。怎么說呢?要說的話就太殘酷了,真的,太老了,余虹太老了,那次同學聚會的驚喜也很快被這種相對而坐的細節取代,我們唯一愿意回憶的只是在大興安嶺的年輕歲月。 余虹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兒,她都長了這么多魚尾紋了她當然不會不明白我的意思。"劉明啊,劉明,我希望我們還能見。"她說,"你快點兒回去吧,不早了,下次我請你,本來說好我請你的。" 后來我關上車門,夜晚的出租車總是開得挺快。在街口的紅綠燈停了一下之后,一切都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我也馬上攔了一輛,司機問去哪兒,我說丹提。我沒有回家,我還是去了酒吧。在丹提門口的樹坑里,我解開腰帶撒了一泡尿。尿了挺長時間,我甚至覺得有點兒虛脫,后來我緊緊抱著一棵樹,我去找了小姐。 那次之后,我和余虹沒再見過,隔了一個春節,她給我發了短信,弄得我們挺熟似的。她說常聯系,我說沒問題。我還給她發了個笑話。再后來就是老牛跟我說余虹死了,車禍,車上還一男的,也死了,好像不是她丈夫。 這可真夠突然的。我當時有點兒不相信,因為不愿意相信,我說:"余虹?哪個余虹?咱班那個?" 老牛說:"×!你行不行啊?余虹,余虹啊,你初戀!" 我沒再說話,如果時間往回算的話,大概是的。當時班上只有兩個同學被選去劇組,大興安嶺深處,他們都說我跟余虹是一對兒。余虹是那會兒班上最可愛的,沒事兒就頂著倆酒窩"嘎嘎嘎"笑,我當時老想著找個機會問問她--你笑什么笑啊? 于一爽的小說 by 張定浩 "我喜歡她小說里一種輕的東西。"在于一爽的小說里,那個名字總是叫做余虹的女主人公在歡愛之余偶爾也會談論起文學。 "松弛。"那個名字總是叫做劉明的男主人公準確地回應道。 我相信每個認真的小說書寫者對于小說這門技藝都各自有其深切的認識,他們之間最終不可調和的區別僅僅在于,寫作是為了取悅他人抑或取悅自己,換言之,是依賴一些小聰明和花招,還是竭盡可能地忠實于自身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問題或許在于,小說家過分聰明而評論家過分不聰明。很多時候,那些聰明的小說家都太清楚評論家想要什么,雖然未必清楚自己最終想要什么。 于一爽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說一種松弛的語調和氣息。當然有時候某種松弛也會成就另外一種造作,這種造作在年輕一代男性小說家的筆下屢見不鮮,他們習慣于把敘事者首先設置成一個男性廢物,但卻是有可能被女人莫名其妙垂青的廢物,從而以一種反智主義的姿態來輕松贏得自己的魅力。所幸于一爽與此相去甚遠。她的小說中的確充滿了各種失敗者的群像,但這種失敗不是為了讓敘事者獲得某種類似無產者般的道德優勢,相反,她是嚴肅的,對這些失敗者痛徹心扉,但希望自己能夠理解他們。 在于一爽這里,松弛首先意味著一種情感上的不作偽。那種被性欲奴役之后作自責嘔吐狀的政治正確,不屬于于一爽,因為她相信,在庸常男女之間自愿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珍視和憐憫的,在這一點上,女作家似乎要比男作家勇敢,而于一爽更是其中較為勇敢的一員。她明白有些東西并非人性的弱點,而就是人性本身。她時常會超越性別的視角去靜靜地審視這一切,或是從他人的視角返觀自我,她樂意呈現某種真實,言談的真實、人類關系的真實乃至性事的真實,在生活之流中呈現。這需要天賦和反復的練習打磨。最終,松弛將走向準確,就像賣油翁將油準確地瀝入狹窄的錢孔,而準確才是每一門技藝基本的道德。 迄今為止,于一爽寫的都是短篇小說,其中都是同一種人,同一種狀態,雖然他們分身為男人和女人。有時我在想,也許她把這些短篇中的素材融合成一部長篇小說,效果會更好一些,至少,她不用讓她的主人公們一再地以某一方草草死去收場,在長篇小說中,他們只需要死去一次。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倘若要滿足一部長篇小說的體量,她就勢必要去編織或想象更復雜多變的情節,而由此勢必招致的某種虛假,或許又是她很不愿意看到的。有時候,閱讀她的小說的感覺有點像觀看旋轉木馬,那些成年的男女以一種不太得體的方式坐在旋轉木馬上,不停地繞著一個很小的圓圈飛馳,這場景起初是有些荒謬的,但又是令人感傷的,她不知道拿這些荒謬和感傷該怎么辦,也許她也不知道該拿自己怎么辦。她筆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很容易放棄的人,但這種放棄里面有一種極度真實的東西在。愛,對他們而言,既不是某種意義的開端也不是結尾,就像那些木馬無所謂起點終點。他們如《玩具》中的敘事者王羞所言,"無法控制事情發展的不完整",但這種不完整中有一種極度真實的東西在。小說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忠誠于這種真實。 《死亡總是發生在一切之前》,是于一爽另外一個短篇的名字。死亡發生在一切之前而不是之后,這可以視作一種小說家的洞見。有一個古老的猜測,革命后的第二天會怎么樣?與之類似,于一爽筆下的每一個故事,幾乎都像在描寫死亡后的第二天。那些衰弱和赤裸的魂靈還沒有渡過卡戎掌管的冥河,還在河的這一邊徘徊,他們不懷抱任何希望,卻也沒有剩下什么還值得絕望的。 接下來她要做的,或許就是要帶他們渡過河流,給予他們新的烈火,以及新的生命。這是有可能實現的。假如她真的懂得"現代主義者永遠不能與過去分手",那么她就應當試圖去找回那些人的過去,以及過去的過去。她或許應當成為一個歷史愛好者。唯有如此,在河的對岸,地獄的某一層,那些人才會忽然自己開口,說話。 俄羅斯文學中有"多余人",我們的時代亦有這樣一些異類,有時間、智力、機緣品嘗社會巨變帶來的成果(或后果)。不僅酒色財氣,也文化藝術,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敗和虛無交織的游戲。和年輕一代的反叛忤逆不同,自我毀滅和孤芳自賞是這幫人的宿命,也是其自主的人生道路。一條道走到黑,個個都是這方面的專家老手。將他們作為一個階層加以揭示,賦予文學形式,于一爽大概是女作家中的第一人。特別是故意設計的見證人的角度,使于的講述更具嚴肅性且真切可信。此外,她的寫作還顯示了一類好作家的諸多品性(有些是隱含的),比如克制、直接、專一,拒絕流行元素、主流話語,堅持抑制而非張揚知見才華。我相信,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層面,她的努力將會取得更加可觀的回報。——韓東 她的小說再次證明了北京口語在操弄小說中所具備的先天優勢。那種滑溜、機靈和生活現場感讓人驚嘆。她從最初就丟掉了經營文學的匠心和做作的"藝術考量"。她所著力的就是緊貼我們的肉身、匍匐于街頭巷尾,裸露出當代生活烏糟、渾濁和傷感的真相。她的小說人物觸手可及、體溫猶存而又面目模糊。與其說這些人物這些故事有什么意義,不如說她用他們表述了一種人類的存在形態。她是我見過的最為真誠同時又讓我難以捉摸的女作家。——曹寇 在她的這些小說里,沒有什么事是必須的,或者不得了的事,看起來有那么多的愛和性,只不過是大家來玩一下,過后不一定要忘記。每篇都有酒喝,酒好像是很重要的,她自己說:所有人物都會喝酒,但就是不知道酒是什么。所以我們才喝酒。寫東西也如此。——小安 她小說里的男女都意識到"自己不重要","忘言"是她小說最最讓人驚訝的特色,因為"忘言",她掙脫了"語言地心引力"的束縛,小說語言輕靈跳脫旁逸,敘述者似乎總是不知道說什么好,結果一躍成為說什么都好。這種語感,委實難能可貴。她本可以"姑妄言",汪洋恣肆,一瀉千里,但她的警醒真誠又讓她愈發克制。這種回流對應于小說人物內心靜止的情感風暴,相得益彰,讓人驚嘆激賞。——趙志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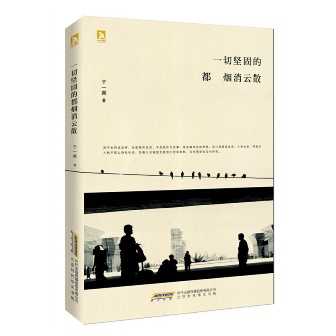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2: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