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上海大年夜 茅盾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跳舞》法國插畫師Yann Kebbi 在上海混了十多年,總沒見識過陰歷大年夜的上海風光。什么緣故,我自己也想不起來了;大概不外乎“天下雨”,“人懶”,“事忙”:這三樁。 去年,民國二十二年,歲在癸酉,公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恰逢到我“有閑”而又“天好”,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后想走動,于是在“大年夜”的前三天就時常說“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 天氣是上好的。自從十八日(當然是廢歷)夜里落過幾點雨,一直就晴了下來。是所謂“廢廳‘的十八日,我担保不會弄錯。因為就在這一天,我到一個親戚家里去”吃年夜飯“。這天很暖和,我料不到親戚家里還開著”水河“,毫無準備地就去了,結果是脫下皮袍尚且滿頭大汗。當時有一位鄉親對我說:“天氣太暖和了,冬行春今——春令!總得下一場臘雪才好!” 似乎天從人愿,第二天當真冷了些。可是這以后,每天一個好太陽把這“上海市”曬得一天暖似一天;到廢歷的“大年夜”的“前夕”簡直是“上墳時節”的氣候了。 而這幾天里,公債庫券的市價也在天天漲上去,正和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 “大年夜”那天的上午,聽得生意場中一個朋以說:“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過不了年關,單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東方面要求巡捕房發封,還沒解決。” “這就是報紙上常見的所謂’市面衰落‘那一句話的實例么?”我心里這樣想。然而翻開“停刊期內”各報“號外”來看,只有滿幅的電影院大廣告搜盡了所有夸大,刺激,誘惑的字眼在那里斗法。 從前見過店鋪倒閉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閃了一閃。肩挨著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緊閉著柵門,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只眼;小紅紙寫著八個字的,是“清理賬目,暫停營業”;密密麻麻橫七豎八貼滿了的,是客戶的“飛票”;而最最觸目的是地方官廳的封條,-一個很大的橫十字。 難道繁華的南京路上就將出現四五十只這么怪相的瞎眼?干是我更加覺得應該去看看“大年夜”的上海。 晚上九點鐘,我們一行五個人出發了。天氣可真是“理想的”。雖然天快黑的時候落過幾點牛毛雨,此時可就連風也沒有,不怕冷的人簡直可以穿夾。 剛剛走出弄堂門,三四輛人力車就包圍了來,每個車夫都像老主顧似的把車杠一放,拍了拍車上坐墊,亂嚷著“這里來呀”!我們倒猶豫起來了。我們本來不打算坐人力車。可是人力車的后備隊又早聞聲來了,又是三四輛飛到了我們跟前。而且似乎每一個暗角里都有人力車埋伏著,都在急急出動了。人力車的圓陣老老實實將我們一行五個包圍了。 “先坐了黃包車,穿過XX街,到XX路口再坐電車。怎樣?” 我向同伴們提議了。 “XX路口么?一只八開!”車夫之一說。 “兩百錢!”我們一面說,一面準備“突圍”。 “一只八開!年三十馬馬虎虎罷。” 這是所謂“情商”的口吻了。而且雙方的距離不過三四個銅子。于是在雙方的“馬馬虎虎”的聲音中,坐的坐上,拉的也就開步。 拉我的那個車夫例外的不是江北口音。他一面跑一面說: “年景不好……往年的大年夜,你要雇車也雇不到。……那里會像今年那樣轉灣角上總有幾部空車子等生意呢。” 說著就到了轉角,我留身細看,固然有幾輛空車子,車夫們都伸長了“覓食”的頸脖。 “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我大聲問了。其實我很不必大聲。因為這條XX街的進口冷靜靜的并沒為的是“大年夜”而特別熱鬧。 “哦——打仗的上一年么?隨便拉拉,也有個塊把錢進帳” “那么今年呢?” “運氣好,還有塊把錢;不好,五六毛。……五六毛錢,派什么用場?……你看,年底了,洋價倒漲到二千八百呀!” “哦——”我應了這么一聲,眼看著路旁的一家煙兌店,心里卻想起鄰舍的x太太來了。這位太太萬事都精明,一個月前,洋價二千七的時候,她就兌進了大批的銅子,因為經驗告訴她,每逢年底,洋價一定要縮;可是今年她這小小的“投機事業”失敗了,今天早上我還聽得她在那里罵煙兌店“混賬”。 “年景不好!”拉我的車夫又嘆氣似的說:“一天拉五六毛,凈剩下來一雙空手,過年東西只好一點也不買。……不像是過年了!” XX路已經在前面了。我們一行五人的當先第一輛車子已經停下來了。我付錢的時候,留神看了看拉我那車夫一眼。他是二十多歲精壯的小伙子,并不是那些拉不動的“老槍”,然而他在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錢么? 站在XX路口,我又回望那短短的XX街。一家剃頭店似乎生意還好。我立刻想到我已經有二十多天沒曾理發。可是我的眼光隨即被剃頭間壁的南貨店吸住了。天哪,“大年夜”南貨店不出生意,真怪!然而也不足怪。像這樣小小的南貨店,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級社會的主顧,可是剛才拉我的車夫不是說“過年東西只好一點也不買”么? “總而言之,XX街里沒有大年夜。” 坐在電車里,我這樣想。同時我又盼望“大年夜’”是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帶。 十字路口,電車停住了。交通燈的紅光射在我們臉上。這里不是站頭,然而電車例外的停得很長久。 “一部汽車,兩部汽車,……電車,三部汽車,四部,五部……” 我身邊的兩個孩子,臉貼在車窗玻璃上,這樣數著橫在前面的馬路上經過的車輛。 我也轉臉望著窗外,然而交通燈光轉了綠色,我們坐的電車動了。啵!啵!從我們的電車身邊有一輛汽車“突進”了,接著又是一輛,接著是一串,威風凜凜地追逐前進,我們的電車落后了。我凝眸遠眺。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廈高樓上的霓虹電光,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個尖角,而那長蛇形的汽車陣,正向那尖角里站。然而這樣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剎那。三公司大廈漸曳漸近了。血管一樣的霓虹電管把那龐大建筑的輪廓描畫出來了。 “你數清么?幾部?” 孩子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這不是問我,然而我轉眼看著這兩個爭論中的孩子了。忽然有一條原則被我發現了:今有所見坐車的人好像只有兩個階級,不是擠在電車或公共汽車里,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車,很少人力車!也許不獨今夜如此罷?在“車”字門中,這個中間的小布爾喬亞氣味的人力車的命運大概是向著沒落的罷? 我們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電車。“ 于是在”水門汀“上,紅色的自來水龍頭旁邊,我們開了小小的會議。 “到哪里去好?四馬路怎樣?” 這是兩位太太的提議。她們要到四馬路的目的是看野雞;因為好像聽得一位老上海說過,“大年夜”里,妓女們都裝扮了陳列在馬路口。至于四馬路之必有野雞,而且其數很多,卻是太太們從小在鄉下聽熟了的。 可是兩個孩子卻堅持要去看電影。 這當兒,我的一票可以決定局勢。我主張先看電影后看野雞。因為電影院“大年夜”最后一次的開映是十一點鐘。看過了電影大概四馬路之類還有野雞。 于是我們就走貴州路,打算到新光大戲院去。 我不能不說所謂“大年夜”者也許就在這條短短的狹狹的貴州路上;而且以后覺得確是在這里。人是擁擠的。有戴了鴨舌頭帽子的男人,更有許多穿著緋色的廉價人造絲織品的年輕女子;也有汽車開過,慢慢地爬似的,啵啵地好像哀求。兩個孩子拖著我快跑(恐怕趕不上影戲),可是兩位太太只在后邊叫“慢走”。原來她們發現了這條路上走的或是站著的濃妝青年女子就是野雞。 也許是的。因為鴨舌頭帽子的男人擲了許多的“摜炮”,啪啪啪地都在那些濃妝的青年女子的腳邊響出來,而她們并不生氣。不但不生氣,還是歡迎的。“愈響愈發”是她們的迷信。 我們終于到了新光大戲院的門口。上一場還沒有散,戲院門里門外擠滿了人。 而且這些人大都手里有票子。 兩位太太站在馬路旁邊望著那戲院門口皺眉頭。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他在學校里“打強盜山”是出名勇敢的),也把疑問的眼光看著我的面孔。 “就近還有幾家影戲院,也許不很擠。” 我這樣說著,征求伙伴們的同意。 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大些的孩子,一個很像大人的女孩子,眼光里有了這樣的遲疑。“不管它!反正我們是來趁熱鬧的。借電影院坐坐,混到一點多鐘,好到泥城橋一帶去看兜喜神方的時髦女人。” 又是我的意見。然而兩個孩子大大反對。不過這一回,他們是少數了,而且他們又怕多延捱了時間,“兩頭勿著實”,于是只好跟著我走。 到了北京大戲院。照樣密密的人層。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戲院的現象更加洶洶然可畏。轉到那新開幕的金城。隔著馬路一望,我們中間那位男孩子先叫起“好了”來了。走到戲院門口。我們都忍不住一股的高興。這戲院還是“平時狀態”。但是,一問,可糟了!原來這金城大戲院沒有“大年夜”的,夜戲就只九點半那一場,此時已經閉幕。 看表上是十一點差十分。 “到那里去好呢?”——大家臉上又是這個問號了。也許新光今夜最后一場是十一點半開映罷?那么,還趕得及。新光近! 真不知道那時候為什么定要看影戲。孩子們是當真要看的,而我們三個大人呢,還是想借此混過一兩個鐘點,預乍看看“大年夜”的上海后半夜的風光而已。 然而又到了新光了。十一點正,前場還沒散,門里門外依然擠滿了人,也許多了些。這次我是奮勇進攻了。五個人是一個長蛇陣。好容易擠了進去,望得見賣票處了,忽然又有些紳士太太們卻往外邊擠;一邊喊道:“票子賣完了。賣完了!”我疑心這是騙人的。為什么戲院當局不掛“客滿”的牌子?我不能再“紳士氣”了。我擠開了幾位攔路的時髦女郎,直到賣票.處前面。我們的長蛇陣也中斷了。賣票員只對我搖手。 好容易又擠了出來,到得馬路上時,我忍不住嘆口氣說: “雖然‘大年夜’不在XX街的小小南貨店里,可確是在每家影戲院里!” 以后我們的行程是四馬路了。意外地不是“大年夜”樣的。也沒看見多少艷妝的野雞之類。“摜炮”聲音更少。 兩個孩子是非常掃興了。于是“打嗎啡針”:每人三個氣球。 我們最后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沒有封皮的怪相“瞎眼睛”。 然而也沒有。 十二點光景擠進了南京路的虹廟。這是我的主張。可是逛過了浴佛節的靜安寺的兩個孩子大大不滿意。“沒有靜安寺那樣大。”是他們的批評。他們怎么會知道我是出來找“大年夜”的,而“大年夜”確也是在這座廟里! 后來我知道過不了年關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債權人請法院去封門。要是一封,那未免有礙“大上海”的觀瞻,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然而調解也等不及,干脆關上大門貼出“清理賬目”的鋪子也就有二百幾十家了。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 “你猜猜。南京路的鋪子有幾家是賺錢的?——哈哈,說是只有兩家半!那兩家是三陽南貨店和五芳齋糕團點心店。那半家呢,聽說是冠生園。” 回家的路上碰見一位鄉親,他這樣對我說。 鄉親這番話,我怎么能夠不相信?并且我敢斷定復雜的“大上海”市面無論怎樣“不景氣”,但有幾項生意是不受影響的。例如我們剛去隨喜了來的虹廟。并且我又確實知道滬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廳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們排日定完;這半年里頭,想在那大佛寺里“做道場”,簡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到家的時候,里內一個廣東人家正放鞭炮,那是很長的一串,挑在竹竿上。我們站在里門口看去,只見一條火龍,漸縮漸短。等放過了我們走進去,依舊是冷清清的弄堂,不過滿地碎紅,堆得有寸許厚。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大年三十·除夕守歲 圖·馮印澄 大年三十,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天。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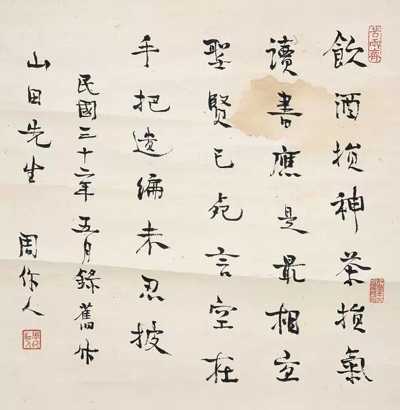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5:3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