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精選 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
 |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 簡體 傳統 |
譯 | 孫韜 轉自《人民文摘》2013年第1期 《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是第一部從希特勒閱讀的書籍中透視他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的著作,被評為“解讀最洞悉其思想、最深入其靈魂”的作品。它是一部隱匿在書架中的“希特勒傳”。 1915年11月,法國北部戰線后方兩英里處,福奈鎮。第16巴伐利亞后備步兵團的一名德軍下士,離開一棟兩層樓高的農舍——他的宿營地,來到了鎮上。往常,士兵們來到鎮上,不是去妓院里找樂子,就是去買煙買酒。而這位卻只是花4馬克買了本關于柏林文化寶庫的薄書。他被那幫通信兵同伴們稱為“藝術家”,他是他們尋開心的對象,這一半是因為,只要你跟他說“戰爭失利了”,就能惹得他冒火;一半也是因為,他總在不執勤的時候在戰壕里花上幾個小時俯身讀書看報。這位孤僻的步兵對1914年的圣誕停火協定頗有微詞,彼時英軍和德軍的士兵們友好相處了一天。當時唯一讓他保有感情、而且無條件服從他的活物,是一只從敵軍火線上迷失的白色小獵犬。 《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提摩西·里貝克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 他的這些習慣幾乎從未有過真正的變化。多年后,他仍會在晚間拋開同伙們,回到孤寂的書房,那兒有讀書時用的眼鏡、一本書和一壺熱騰騰的茶。曾有一次,他的情婦非常魯莽無禮地擾亂了他的靜思,結果被他大大訓斥了一番,紅著臉跑出了門廳。此后,他的門外便掛了一個告示牌,要求“保持絕對安靜!”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當他被大部分屬下拋棄、在“眾神的黃昏”中黯然謝幕時,攻入的蘇聯士兵在他柏林地堡內找到的屬于他的私人物品,僅有幾十本書。 在后人的印象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個焚書而不是個愛書的人。但據蒂莫西·W·里貝克在其《希特勒的私人藏書》一書中所述,他在位于柏林和慕尼黑的兩處住地,以及位于奧博薩爾茨堡峰上的阿爾卑斯山度假地,共有16,000多冊書。里貝克,一本研究達豪鎮的專著《最后的幸存者》一書的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殘存的希特勒的藏書,這些藏書主要為國會圖書館所收藏。通過深入研究希特勒在書上留下的標記和旁注,里貝克試圖重建希特勒在描繪他的世界地圖時的心理路程。研究的結果,就是這本并非完全有說服力,卻也能引人入勝的書。 希特勒也許從未完成過什么正規的教育,但是據他早年在維也納的朋友奧古斯特·庫茲別克回憶說,書“就是他的世界”。正如里貝克指出的,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希特勒作為羽翼未豐的納粹黨的領袖,不僅下力氣苦讀了數百本歷史和種族方面的書籍為其思想體系尋求理論支撐,還不遺余力地為該黨構建了一整套準則。在該黨的黨員卡上,希特勒為黨員們提供了一個推薦讀物的書單,并用黑體字大書:每個國家社會黨黨員都必須熟習的書(里貝克把它譯為應該閱讀,弱化了它的本意)。這個書單中包括亨利·福特的《國際猶太勢力》、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之敵》這樣的一些精品。希特勒的愛書之癖也可以從他在慕尼黑小公寓內所拍的一張罕見的照片得到印證,照片中“希特勒著深色西裝在一個書架前擺了一個姿勢”——那是一件漂亮的帶月牙邊造型的家具——他雙臂交叉,一副傲然的主人的架勢”。 1945年3月,美軍士兵經過德國慕尼黑“市民啤酒館”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廳政變失敗后,被同情他的法庭處以叛國罪,但卻只被判入獄五年,而且可能從寬提前釋放。恰恰就在愚人節這一天,這條輕描淡寫的責罚被執行了。在蘭斯堡監獄,在獄卒們的悉心照料下,希特勒寫了他的第一本書《我的奮斗》。據里貝克的觀點,在尚存的希特勒獄中讀本里,有一本翻舊了的《德國人民的種族類型》,這本書在《我的奮斗》中留下了鮮明的思想印記。這本書的作者F. K.岡特以其狂熱的種族純潔論而被稱為“種族分子岡特”。盡管里貝克書中沒有提及,希特勒在蘭斯堡還是每周都得到慕尼黑大學一個政治學教授——“生存空間論”的鼓吹者卡爾·奧斯弗的指導。 里貝克挑選了慕尼黑出版商尤利斯·弗里德里希·勒曼作為實例,因為此人有著“令人懷疑的雙重身份,據說既是希特勒藏書唯一的最為慷慨的捐贈者,又是納粹生物種族主義論偽科學的知名設計者”。里貝克繼續寫道,“有了勒曼的這批書,我們就掌握了希特勒書庫的核心,也就掌握了構成希特勒的知識世界及其第三帝國思想基石的主要材料。” 但我們是否真的掌握了這些呢?1919年,希特勒被卡爾·梅爾上尉選中去參加慕尼黑大學的系列宣傳集會,向士兵們宣傳布爾什維克黨的危險。早在那一年的9月,在回答一個士兵寫信提出的“猶太人問題”時,希特勒放言說理性反閃米特主義的“最終目標必將是毫不動搖地把猶太人徹底清除掉”。正如歷史學家伊恩·克劭在其所著的希特勒傳中所說,這個回答暗示著:他從一戰結束時起,直到他在柏林地堡內的最后幾天,就一直頑固地堅持著國家主義和理性反閃米特主義。簡而言之,希特勒對書本的冥思暗忖,強化了而不是創造了他的這種惡毒的仇恨。 另外,里貝克也忽略了一座城市的重要性,在那里希特勒第一次接受了反閃米特主義。希特勒的維也納,借用奧地利學者布利基特·哈曼一本書的標題來說,是一口沸騰的大鍋,烹制著對猶太人的憎恨。希特勒對該城奉行反閃米特主義的市長卡爾·呂格贊賞有加,并沉浸于閱讀那些宣揚種族主義的報紙和宣傳小冊子。他也對德國的浪漫主義著了迷。以瓦格納的戲劇為形式,德國的浪漫主義滋長了他的一種幻想,認為自己担負著使這個老朽的德意志帝國起死回生的使命。 對里貝克而言,希特勒理論的本質,就是“一個雜貨鋪式的理論,從一堆廉價偏狹的平裝書和佶屈聱牙的硬裝書中縫縫補補拼湊而來,為其空洞淺薄、精于算計而又霸道唬人的謊言提供辯護理由”。但是希特勒的本質還遠不止里貝克說的這些。在沒有自己的獨創思想時,希特勒沒像嘉年華會上招攬顧客的小販那樣大喊大叫。相反,他利用那些彌漫于魏瑪共和國的理念,穩步在知識界和資產階級圈子里贏得了信任。希特勒的天才在于能夠把德國的文化國家主義和政治糅合到一起,從而使得他能在同時代的人當中發揮藝術性很強的迷惑力。正如托馬斯·曼恩在其1938年的一篇題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中無所畏懼而又犀利無比地指出的那樣,元首或許“讓人感到不快而且猥瑣可恥”,但是對這樣一個人的親密關系,曼恩不是僅憑主觀愿望就能使之消失的。 盡管如此,里貝克還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誘人的機會,使我們得以窺見希特勒那令人毛骨悚然而又狹隘細碎的自我提高計劃。成為一個書蟲未必就是變成一個大屠殺兇手的先決條件,但這顯然不會是一個障礙。斯大林也是一個勁頭十足的讀書人,并為其書庫里的兩萬冊藏書而夸耀不已。“如果你想了解你周圍的人,”斯大林說,“那你就得看他讀什么樣的書。”當里貝克開始探究希特勒的收藏時,他發現了普魯士將軍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一本著作,這本著作和法國一位素食主義者的烹調書緊挨著放在一塊兒,這本烹調書題贈給了“素食者希特勒先生”。
文 | 提摩西·里貝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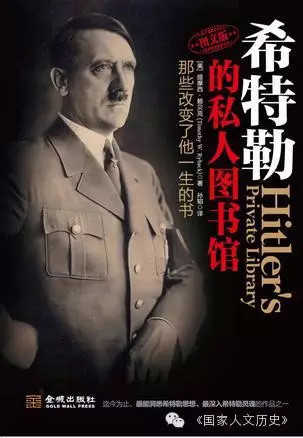


《國家人文歷史》 提摩西·里貝克 2015-08-23 08:54: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