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的世界——讀《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當我動手寫這篇書評的時候,“方韓大戰”仍萬馬戰猶酣。雙方都沒有聽從我的和解勸告,方舟子堅持質疑韓寒有代筆,而韓寒則向上海法院遞交了訴訟。我之所以勸和,從私心角度講,是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希望文學的事情由文學本身來解決,不希望看到80后文壇實力的被削弱;而從公心的角度講,則希望同時保護創作自由和批評自由,不愿意看到哪方因遭強力壓制而噤聲。方舟子的質疑固然犀利,韓寒的反擊固然猛烈,但由于雙方皆非文學研究者,所以他們都不知曉文學理論中有這樣一個概念:敘事者。一旦我們從“敘事者”的視角看待作品,許多爭論就是完全多余的了。
一般讀者都認為文學作品是“作者”寫的。但那個現實生活中的“作者”,跟讀者通過作品想象出來的“作者”,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僅在極少數情況下,二者基本重合。寫《阿Q正傳》的“巴人”,決不等于在教育部當官的那個“周樹人”;給我們講述“孔乙己”悲慘遭遇的那個魯鎮酒店的小伙計,更不是少年魯迅。因此文學理論家們發明了一個“敘事者”概念。這個敘事者,是作者通過作品所塑造出來的一個虛擬自我。例如我們讀古代白話小說,覺得那個敘事者好像是在茶館酒肆的一個說書人,隔三差五就喚咱們一聲“看官”,而真正的作者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臣。30年代的人,讀郁達夫的小說,感覺敘事者窮困潦倒,而生活中的郁達夫,嬌妻美宅,過著“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日子。事已至此,我不想用敘事者這個概念去介入方韓的官司,只想從這個視角看看韓寒2010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長篇《1988》,或許會增加一點我們對80后文學的理解。
這部小說的情節很簡單。第一人稱敘事者“我”,開著一輛1988年出廠的旅行車,到幾千里外的異地,去接一位朋友出獄。這輛車,就是那位朋友在報廢的基礎上給改造的。“我”夜宿小鎮,邂逅了一位妓女。接受了服務后得知,她已經懷了不知是哪位客人的孩子,并且想生下來,培養成一個理想的后代。因為被警察抓了嫖娼,“我”跟這個妓女產生了復雜的感情糾葛,于是就一路帶著她去找某個男人。“我”在路上不斷回憶往事,于是就插敘進來其他少年往事和感情線索。終于到達了異地,“我”去監獄接出來的,其實是朋友的骨灰。而妓女也沒有找到她的“孫老板”,接著二人在醫院里走散。故事的結尾,妓女生下孩子后托人送給了“我”,“我”就“帶著一個屬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
如果把這個故事當成“賽車手韓寒”的夫子自道,顯然是天真和外行的。書中的回憶有眼保健操里包含“為革命保護視力”的開頭語的情節,有被同學批判為“反革命”的情節,此類“閃回”顯然不是80后而是60后以前的人生記憶。但80后憑什么就不能借用甚至虛構60后的人生記憶呢?所以,我們不必追究作家韓寒的“創作程序”,值得研究的是敘事者韓寒與賽車手韓寒的靈魂交錯。我曾經說過,韓寒的小說具有一種“速度感”。這種速度感不是簡單的節奏快捷或者思維跳躍之類,而是韓寒的文字經常給人一種“在路上隔著車窗看人生”的感覺,這個感覺跟80后60后無關,這個感覺只屬于一個曾經喜歡長跑、后來喜歡狂飆的狂狷之士。不論我們覺得他有什么天才或缺陷,不論我們覺得他有什么洞見或偏激,不論我們覺得他天馬行空或鼠肚雞腸,他都是獨一無二、只可模仿不可復制的。
正因為不是在正常的速度中看世界,所以敘事者一方面“想和這個世界談談”,而另一方面他所呈現給讀者的世界是動蕩的,是可疑的,是不可久居的,是不斷向后掠過的,是沒爹沒媽的,是活得快死得也快的,是剛剛尋找到就發現已經成了骨灰的。80后文壇上,集中全力為讀者奉獻出這樣一個世界的,只有一個“敘事者韓寒”,不論這個韓寒在生活中是誰,哪怕他是一個韓國人,都值得他的那些粉絲向他致敬。因為他所奉獻的,是一個“韓寒的世界”。
2012年2月10日 (本文發表于《長篇小說選刊》2012年第2期)
本期博客思考題:
1.一個寫作團隊使用一個筆名,可以不可以?
2.為什么筆墨官司不宜用打官司的方式解決?
3.去掉了神圣光環的韓寒,還有沒有文學和文化價值?
孔慶東 2012-05-29 22:13:37
 |
相關閱讀 |
 |
推薦文章 |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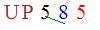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