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劉再復:三國水滸是人心的地獄
 |
>>> 春秋茶館 - 古典韻味,時事評論,每天清新的思考 >>> | 簡體 傳統 |
觀點各異,重在包容探討與辨析,此文可供參考。:-)
——答《瞭望周刊》記者楊天問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1.您在《雙典批判》中將《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稱為"中國人的地獄之門",而在我國民間,也早有"少不讀《水滸》,老不看《三國》"之說。對于這兩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著眼點各是什么?在您看來,"雙典"對于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獄是人心的地獄,"雙典"便是這種地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小說把中國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淵,使中國人原是非常純樸、非常平和的心靈發生變形、變態、變質,變得愈來愈可怕,此時,我必須大喊一聲:同胞們,請小心自我的地獄。中國正處于急速現代化的過程,此次現代化,不是槍炮推動的(即不是殖民過程),而是技術推動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發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為現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興。但是,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發展"總是要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包括三個負面的東西:(1)生態的破壞;(2)社會的變質;(3)人心的黑暗。這三種代價中屬于最嚴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壞是"人心的黑暗"。在此歷史語境下,我對"雙典"展開批判,正是期待減低付出的代價。
"雙典"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蔑視生命、蔑視婦女、蔑視孩子,嗜斗、嗜殺、嗜血,一切都可當作英雄的祭品等等,我不想再復述了,但今天面對你的問題,我要再次指出:"雙典"對中國人心有一種共同的巨大危害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水滸傳》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讓人覺得"目的"神圣,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這就是所謂"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鴛鴦樓,濫殺仇人之外的十幾個無辜(連馬夫、小丫環也不放過)有理,李逵按照吳用的指示把四歲的嬰兒(小衙內)砍成兩段也有理,為了逼迫盧俊義、朱同、秦明上山而欺騙、嫁禍于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國演義》也是如此,為了自己設定的目的(如劉備的維護正統和曹操的維護一統)便不惜使用各種權術、心術、詭術,不惜施行各種陰謀、陽謀、毒計。為了打下江山,臉皮像劉備那么厚、內心像曹操那么黑,均理所當然。中國人一代代地欣賞、崇尚武松、李逵、劉備等,到了當下,"厚黑學"竟成了中國一部分聰明人的生意經和升官發財的潛規則。面對這種現象,我在"批判"中強調"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導致崇高的、圣潔的目的。我認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換句話說,手段重于目的。這是我感悟到的一種人文真理。對不對,可以討論。不能簡單地說"造反有理",即不能認為只要是造反,那么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簡單地說"正統有理',即不能認為只要是維護道統,使用什么陰謀權術都是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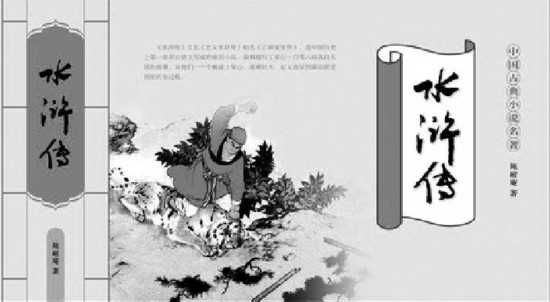
2.您說過,"寫作《雙典批判》,其實是在寫作招魂曲。中國文化的魂,是一個誠'字。"這個"誠"字具體內涵是什么?為何到了《三國演義》時代,"誠"字會喪失殆盡?
答:在美國落基山下,常聽李澤厚先生講中西文化的根本區別,其中有一點是說基督教講"信",因信稱義;而中國講"誠",至誠如神。《中庸》講"不誠無物",后世講"誠則靈",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基督的"信",派生出主、愛、贖罪、懺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范疇;中國的"誠"則派生出仁、禮、學、孝、悌、忠、恕、智、德、義、敬、哀、命等范疇,這些范疇可視為"誠"的文化內涵。而我們通常講的"誠"比較簡單,主要是指誠實、真誠,即對天、對地、對人、對事、對生、對死、對他人、對自己都要真誠、真實。這種"誠"是真,又是善,是中國原型的價值文化,也可以說是本真本然的價值理性。這種價值觀以情感為本體,不以功利為本體。如果說,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么,誠內心則是中國的魂。但是,到了《三國演義》,則一切都是為了現實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納入權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體系。為了奪得政權,戰勝對方,即實現功利的最大化,爭斗的各方全都掩蓋真相,全都帶假面具。誰"偽裝"得最好,誰的成功率就最高。這是三國邏輯。那個時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較量,實際上是詭術、權術、陰謀的較量。以生命個體而言,當時最有力量的是呂布,但他失敗得最慘,因為他的詭術、權術不如劉備、曹操等,他臨死時,還期望劉備能替他說話,還給他一點"誠",結果適得其反,劉備報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爭權奪利進入白熱化的時代里,絕對不可能有"誠"字的立足之所。三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又是"誠實"喪盡的時代。
3.您曾提及,魯迅先生最早發現了"雙典"與中國國民性的相通。可否談談"雙典"的這種國民性基礎最早可溯源何處?對于魯迅先生所述的"三國氣"與"水滸氣",您作何解?您認為,"雙典"的產生又有助于塑造新的國民性格,這種性格的具體表現是什么?"雙典"產生之后,其文化價值觀就一直在統治著中國,這種影響甚至延續至今,為何其會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響力?
答:魯迅所說的"三國氣"和"水滸氣",可理解為"三國氣質"與"水滸氣質",也就是中國人早已具備三國式與水滸式的國民氣質即國民性了。魯迅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因為有國民性的基礎,所以就喜歡"雙典"。說得明白透徹一些,便是:中國人早已成了三國中人與水滸中人,所以自然就樂于接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超階層、超階級的全民族共有的國民性也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國民性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是長期歷史積淀的結果,不是某時某地某處發生的事件,所以很難回答你的"溯源于何處"的問題。
魯迅指出中國人接受"雙典"有國民性基礎,這一點對我有啟發。我補充說明的是,"雙典"產生之后五百年來,它又加劇了中國國民性的壞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負面作用。使中國國民性中"瞞"的方面、"騙"的方面、"偽"的方面、"兇殘"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樣",從而進一步惡性發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權術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許多人文經典,但是,他們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影響,都不如"雙典"如此廣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統治中國人心的還是"雙典"。國民性是一種歷史的惰力,"雙典"產生后又強化了這種惰力,很難改造。魯迅一生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很偉大,但他的改造事業並沒有成功。他的《阿Q正傳》並沒有戰勝《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現在中國仍然到處是水滸中人與三國中人。也到處是阿Q。

4.您將中華文化劃分為原形文化和偽形文化,能否談談做這樣劃分的原因和其現實價值?您認為《山海經》是中華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國真正的原形文化,為什么?以《山海經》為參照,《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又是如何發生"偽形"的?
答: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的劃分,是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這兩個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變形變質,我借用來描述中華文化,並不是套用,而是中華文化也有原形與偽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變質為偽形文化的現象。每一種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大系統的質都不是單一的,列寧早就說過,每個民族都有兩種文化。用我們熟悉的語言表述,便是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精華與糟粕。但是,分清精華與糟粕是靜態分析,而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這兩個概念則包含著動態過程,這種劃分更能呈現文化歷史的真實,也更能幫助我們在評價文化時免于落入本質化即簡單化的陷阱。我把《山海經》界定為中華民族原形文化的經典,是因為《山海經》雖然是神話,但它卻呈現出中華民族最真實的原始精神,是中國最內在的歷史。中華民族心靈的本真本然是什么樣的?中國歷史的開端擁有什么樣的"基因"?《山海經》全都形象地呈現出來了。《山海經》這部"天書"見證了中國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經》"救人"、造福人類的建設性文化為參照系,我們就可以看出"雙典"中的英雄已完全變質,雙典文化已變成殺人的、破壞性的英雄文化。

5.您為什么說"五四"運動選錯了旗幟和靶子?這是否說明,"五四"主要著眼的是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運動,而您對"雙典"的批判等工作,則更多關注的是整體國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讀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運動很了不起,它包含著歷史主義的文化內涵,也包含著倫理主義的文化內涵。我的"雙典"批判,的確更多地關注倫理主義內涵,也就是你所說的整體國民精神人格。從歷史主義的角度著眼,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走向現代社會,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把孔夫子作為舊文化的總代表,這無可非議。他們把孔子作為打擊的靶子,是為了說明,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為了趕上時代的潮流,必須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這是對的。但是,如果從倫理主義的角度著眼,我則認為孔子並不代表中國道德的黑暗面,真正體現中國道德的負面與黑暗面的,應當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要說吃人,"雙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滸傳》中的暴力,《三國演義》中的偽裝與權術,都是反人性與反道德的。"五四"批判舊道德、偽道德,而偽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國中人。《三國演義》不僅有道德的偽形,而且還有智慧的偽形、美的偽形、歷史的偽形,樣樣都是科學與民主的大敵,樣樣都在腐蝕人的心靈。如果五四運動以"雙典"為主要批判對象,現在中國人的靈魂一定會健康得多。
6.在對《水滸傳》的批判中,您在確認"造反"的某種歷史合理性,同情造反者對"專制制度"或"專制權力"的反抗的同時,卻并不認同反抗者的"專制人格"。這種"專制人格"指什么?您為何對其不認同?
答:在我心目中,所謂專制,包括專制制度、專制人格、專制語言、專制氛圍等層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對無處不在的專制氛圍、專制人格、專制語言感受特別深。群眾專政,最可怕之處首先是造成專制氛圍,隨時都可能被點名,隨時都可能被"揪"出來,沒有任何安全感,那個時刻,我才明白,大民主原來是大專制,難怪伏爾泰要說,我寧可受寡人專制,也不愿意受眾人專制。還有專制語言,這就是我一再批判的語言暴力。人身攻擊,心靈中傷,人格踐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變成無稽造謠,無端污蔑,無恥誹謗,無限上綱,無所不用無極。那個時候方塊字全帶毒液,中國古今最受尊重的圣賢和中西方最有成就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無一不受到最惡毒的抹黑和打擊,連朱德、劉少奇、彭德懷、陳毅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也難幸免。除此之外,還讓我終生難忘的是到處都橫行著李逵式的"排頭砍去"的專制人格,這種人格是唯我獨革、唯我獨尊、唯我獨斷的人格。我在"雙典"批判中說李逵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近女色,二是嗜殺。因為不近女色,他就占領了道德制高點,就可為所欲為,嗜殺濫殺也是大英雄。中國的男人,多半都具有專制人格,心理上皆嗜殺好斗,唯我獨尊、獨斷,但又好色。文化大革命中打斗造反的紅衛兵,幾乎個個都具專制人格,他們未掌權時是"暴民",一旦掌了權便是"暴君",因為本來就是專制人格,一旦"重新洗牌"成功掌了權,自然還是喜歡由我獨斷獨裁的專制制度,于是,革命領袖轉瞬間變成了專制暴君,中國歷代王朝的更替全是此種循環套。所以我才特別強調,必須在文化上清除專制人格,否則,中國永遠走不出專制--造反--再專制的循環套。

7.您從社會性和政治性兩方面對于《水滸傳》的"造反有理"進行了批判,這樣的批判與您和李澤厚先生十幾年前提出的"告別革命"的論斷有何內在聯系?對于"告別革命"的命題,如今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答:《雙典批判》與《告別革命》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可說是"吾道一以貫之"。
中國文化傳統可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大傳統是孔、孟、老、莊等建構的(開端比這還早)尚和、尚文、尚"柔"的傳統。這一傳統合符人間情理,所以永遠不會滅亡。還有一個是小傳統,這是農民起義的造反傳統,這一傳統,極端尚武,爭奪的雙方均極為殘酷,這是真正你死我活的戰爭。造反的一方知道"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不能不拼死一戰,不能不"排頭砍去"。鎮壓革命的一方為了保住政權也決不留情,連力倡"仁義道德"的大儒曾國藩也"殺得一個不留"而被稱為"曾剃頭"。我和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便是告別小傳統,即告別《水滸傳》所謳歌的小傳統。破小傳統是為了立大傳統。我們相信,世上沒有什么爭端不可以用對話、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決。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流血暴力的方式並非歷史的必由之路。
8.您認為"從宋江梁山起義的年代直到現代,中國始終沒有第三空間。"您所說的"第三空間"是指什么?為何中國始終沒有"第三空間"?現在有什么可能途徑能夠建立"第三空間"?
答:我所講的"第三空間",原是哲學話語、文化話語,並非政治話語。如果把此概念運用到政治領域也可以,但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從哲學上說,二元對立講的是非此即彼,二律背反講的是亦此亦彼,"第三空間"講的則是"非此非彼"。我認為,文學藝術的原創性皆產生于"非此非彼"的第三種可能中。我的好友高行健,其小說、戲劇、繪畫的原創,全仰仗于非此非彼即超乎二的第三空間。
政治總是產生對立的兩級,如所謂左派與右派,"革命派"與"反動派",激進派與保守派。在兩極對峙中,政治中人當然要選擇一極作為自己的基本立場,但文學中人與文化中人,由于他們乃是以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為人生目的和事業目的,因此總是選擇超越黨派甚至超越政治的立場。這種立場可稱為中性立場,也可稱作價值中立的立場。持守這種立場的知識分子,其立足之地便是超越兩極對立的第三空間。有此空間,才有良知的自由即終極關懷的自由,失去這一空間便失去自由,但是中國歷來政治斗爭太嚴酷激烈,對立的雙方都要知識分子"非此即彼",不給他們獨立于第三空間的自由。《水滸傳》中的盧俊義,算是大紳士,它本來也想站立于第三空間,可是梁山英雄不讓他作此選擇,非逼他入其"團伙"不可。文化大革命,我想當"逍遙派",也是想退入第三空間,但無可逃遁,"革命"大勢不允許。現在情況已有所好轉,知識分子至少有沉默的自由、逍遙的自由以及不表態、不參與的自由。也就是說,第三空間還是可以由自己去開辟,去爭取。

9.能否談談"雙典"的婦女觀?在您看來,《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特別是婚外戀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可分別用"天堂"、"地獄"和"人間"形容,為什么如此詮釋?
答:"雙典"的婦女觀,是把婦女只當"物"不當"人"的野蠻婦女觀。我為此特制作了一張女人的物化圖表,請你留心一下。《三國演義》也殺女人吃女人,如獵戶劉安就殺妻子讓劉備吃,此舉還得到曹操的獎賞。但"三國"對婦女更多的是利用,而"水滸"的重心則是殺戮。"雙典"對婦女的態度是英雄主義和大男子主義及專制人格"三結合"的產物,非常黑暗,非常血腥又非常虛偽。
《紅樓夢》、《水滸傳》和《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簡單地說,《水滸傳》對婦女設置了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為兇殘的道德法庭,楊雄之妻潘巧云,武松之嫂潘金蓮等,都被這一法庭判處死刑酷刑,都被挖出五腑六臟。《水滸傳》對婦女只有道德法庭,沒有"審美法庭"。
與此相反,《紅樓夢》對于婦女只有"審美法庭",沒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則兩者皆無,它只如實地描寫社會百態與人生百態,既不做道德判斷,也無審美意識。所以,同樣是婚外戀者,《水滸傳》把潘金蓮判入地獄,《金瓶梅》則把潘金蓮放入人間,在人間中如此這般生活,七情八欲,皆屬常態,非善非惡,不必大驚小怪。而婚外戀者秦可卿生活在只有審美法庭的《紅樓夢》中,她卻贏得"兼美"的命名,屬于警幻仙子,又美又可愛。《紅樓夢》很偉大,它不僅把少女視為比元始天尊和釋迦牟尼更為重要的宇宙精華,而且把婚外戀女子秦可卿視為兼得釵、黛之美的天人女神。《紅樓夢》是真文學,呈現的是真人性。我們要尊重人與人性,高舉人的旗幟,只能傾心《紅樓夢》,批判《水滸傳》,肯定《金瓶梅》。
10.您為何認為《水滸傳》中僅魯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輝"?對于宋江,您又有著怎樣迥異時論的再評價?
答:前邊已說過,《水滸傳》中的主要英雄,均有嗜殺的特點,即動不動"殺人",唯獨魯智深是個例外。他的生命總方向,不是"殺人",而是"救人"。他出場后三拳打死了狀元橋下綽號鎮關西的鄭屠,這是我們能見到的唯一一次的"殺人",但此次打死人也是為了"救人"--為了救金翠蓮。而這之后,他到文殊院智真禪師處,剃度為僧,再也未殺過人。路過柳花莊,他痛打小霸王周通,也是為了救人--救劉太公的女兒。林沖刺配滄州時,他大鬧野豬林,更是為了救人--救林沖。當時他很有理由殺那兩個想把林沖置于死地的皀隸,但他只是救人,并不殺人。他處處與人為善,身上沒有匪氣,只有俠氣。它是《水滸傳》中的偉大俠客,不僅有人性,而且還有佛性,非常可愛。
如果說,魯智深是大武俠,那么,宋江則是大文俠。宋江既沒有武功,也沒有文功,為什么江湖豪杰們都服他,稱他為"及時雨",這就因為他身上既有儒氣又有俠氣,可謂亦儒亦俠。中國的"盜"與"俠"都"造反",但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盜是造反后一定要占有,而俠則不然,他路見不平,拔刀而起,造反勝利后則遠走高飛,不占有,不爭奪勝利之果。宋江恰恰有此特色。時人說他"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錯,但時人沒想到,他不反皇帝,正是他不想當皇帝,沒有占有皇位、占有天下的欲望。這正是大俠襟懷。哪個農民革命領袖不想當皇帝?他們通過革命想的是"重新洗牌",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在替天行道背后是人性貪婪的欲望,但宋江不是如此,他反貪官、反不平、反黑暗,但沒有奪帝位坐江山的欲望,因為他有此俠性,所以當了領袖以后,便提出一套和以往農民革命全然不同的"游戲規則",即被稱為"招安"的與政府又打又談判的妥協路線。我和時人的看法很不相同,認為應當充分肯定宋江這種路線與方式,不可簡單化地罵他為投降派,更不可像金圣嘆那樣,給他帶上種種黑帽子。
11.您將《三國演義》視為中國權術大全,您怎樣看待中國古代文化中所說的"道"和"術"之間的關系?為何在中國歷史上會數度出現"道崩潰,術勃興"的局面?為何說《三國演義》所以會變成權術大全,與諸葛亮智慧的變質關系極大?
答:中國古代文化中的"道"與"術"都是大范疇,要講清道與術的關系,可能需要專著或論文,我們在對談中只能簡單說說。我工作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金岳霖先生寫過《道論》,很難讀。我國最初提出道論的是老子。他講的道,是終極究竟,是宇宙本體。但是《道德經》除了講道之外,也講"術",司馬遷的《史記》甚至認為法家講術,全來源于"學黃老道德之術",(可參見《史記》中的"老莊申韓列傳"和"孟子荀卿列傳")。法家體系包括法、術、勢三派,商鞅言法,申不害言術,慎到言勢,韓非則集三派之大成。在韓非看來,法雖重要,但如果沒有術,君主便難以站在超然的地位以執法,所以他提出刑要重、賞要慎等政術,對于這些"術",我們不能簡單化地一律視為壞東西。我在《雙典批判》中所批判的權術、心術,實際上是政術的偽形。
用我們今天的現代語言來闡釋,"術"乃是技巧、策略、靈活性。這些"術"要正,必須有"道"作前提。道是根本,是原則,是靈魂,是制度。《三國演義》中的權術完全喪失前提、喪失原則,成了十足的詭術。打仗不能不講"詭術",但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詭詐之術,心靈就會崩潰。所謂"道崩潰",便是人類正常生活中的基本行為原則崩潰,心靈原則崩潰,道德底線崩潰。"三國"中的帝王將相,個個玩弄詭詐之術,有的玩儒術,有的玩道術,有的玩陰陽術,各種術,歸根結蒂,全是騙術。諸葛亮這個形象比較復雜,他有真誠的一面,真誠時,其智慧發揮得很動人,但他也有偽裝的一面,偽的時候,其智慧就發生變質。"術"可以表現為生存智慧、生存策略,也可以表現為生存計謀、生存面具,生存騙局。《三國演義》成為權術、心術的大全,包括諸葛亮的權術與心術。
12.您談到,中國的義,發展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其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逐步變形變質。那么,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什么?"雙典"中的"義"發生了怎樣的變形?這種變形的原因何在?這種變形在西方文化中是否也發生了?
答: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與"利"對立的一個大范疇。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到了孟子,說得更絕對,他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上)孟子的學說強調一個義字,他講義利之辯,讓我們明白,即使義中含有利,那也是利他而非利己。總之,對于個人,義便是超功利,不謀私利,唯其如此,才能以義去實踐天命,代替運命,光大生命。我在《雙典批判》中以伯牙和鐘子期的友情為例,說他們兩人的故事便是義的原形。伯牙和鐘子期的"知音"關系,只有情感,只有對音樂的酷愛,沒有其他功利之求。這種"義"很純很美。但是到了桃園三結義,義就發生變質了。義變成劉、關、張"共圖大業"即奪取天下的盟誓,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表述,義便是結盟結黨營私營利的組織原則,有如三個準備去搶銀行的小團伙,以義為團伙條規,對天發誓。所謂同年同月同日死等,都是安全的需要,功利的需要,因為這種組織原則有效,所以后來被青紅幫廣泛運用。伯牙、鐘子期不謀私利,特別是不謀政治經濟的大功利,非常純粹,自然也相互絕對信賴。劉、關、張及后來的青紅幫卻因功利大業而結合,關系不牢靠,只能用"義"來作"利"的保證。《三國演義》中的義,不僅功利性極強,而且排他性極強。團伙之內與團伙之外大不相同,內外之別乃天淵之別。《水滸傳》中的義也如此,"一〇八"之內與"一〇八"之外大不相同,內則稱兄弟,外則"排頭砍去",所以魯迅批評賽珍珠把《水滸傳》書名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妥當。"水滸"的"義"恰恰沒有愛的普遍性。"三國"中的義當然也是如此,偽形的"義"對社會的健康并沒有什么好處,它只能使社會變成一個一個的"團伙",即以團伙代替社會,使社會發生變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偽形的義乃是促使社會惡質化的毒劑。西方文化因為有基督教的大背景,愛與信都來自上帝,所以"義"的觀念不發達。韋伯的思想只能出現在西方,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韋伯只講責任倫理,不講意圖倫理,更不講兄弟倫理和團伙倫理。
13.您曾多次提及《金剛經》、《六祖壇經》、《道德經》、《南華經》、《山海經》和《紅樓夢》是您心中的"六經",為何有這樣的定義?這"六經"分別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旅居國外多年,對于中西文化的"體用"問題怎么看?
答:意大利當代的天才小說家卡爾維諾去世后出了一部文選,名字叫做《為什么讀經典》。其實,這是他在一九八一年的一篇演講題目。卡爾維諾給經典下了十種定義,我記得若干種。他說,經典是從未對讀者窮盡其義的作品,是每一次重讀都像首次閱讀時那樣新鮮,讓人有初識感覺的作品。它既是頭上戴著先前的詮釋所形成的光環、身后拖著它們在所經過的文化中所留下來的痕跡,又是剛剛向我們走來的新鮮的作品。特別讓我難忘的是,他說經典是代表整個宇宙的作品,是相當于古代護身符的作品,是不斷在其四周產生由評論所形成的塵云卻又總能將粒子甩掉的作品。我把《山海經》等六部作品界定為我的經典,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六部作品作為我須臾不可離開的護身符和永遠開掘不盡的精神礦山。這六經對我的影響,是對我生命整體的影響,也可以說它影響了我的整個生命狀態、生命質量,尤其是靈魂質量。它已進入我記憶的深層化作我的潛意識。因為經常讀此六經,我的生命感覺和二十年前已全然不同,連吃飯、睡覺、走路的感覺都不同。
旅居國外多年,此時我的心態是"世界公民"的心態,既愛中國文化,又愛世界文化。在我心目中,文化、學問、思想只有深淺之分、粗細之分、高下之分,并沒有森嚴的中西之分。我有中國的"我的六經",也有西方的"我的六經",我不知誰是體誰是用。我不講"中體西用",也不講"西體中用",只覺得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對我來說,都是"亦體亦用"。莎士比亞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曹雪芹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從荷馬但丁到托爾斯泰,從孔孟莊老到曹雪芹、魯迅,都是我的精神本體(體),也是我的實踐之師(用)。
14.1995年,您與李澤厚先生第一次提到"返回古典"的命題:從現代返回古典。能否談談當時提出這一命題的背景?這一命題的具體涵義又是什么?在您看來,應該返回什么樣的"古典"?怎么返回?在"返回古典"的具體落腳點和重心上,您和李澤厚先生的看法是否一致?在您看來,提出這樣的命題對于今天的中國有什么現實意義?對于這幾年國內盛行的"國學熱"您又有什么看法?
答:十六年前李澤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的命題,首先是針對二十世紀的機器統治和商品統治。過度的現代生產已使人變成機器的奴隸和廣告的奴隸。"返回古典"就是呼喚"人"從機器與商品統治中重新站立起來。西方文藝復興的"返回古典"(返回希臘)是為了走出宗教統治,讓"人"獲得解放,我們今天講返回古典也是為了人的解放,但歷史的針對性內容不同,我們針對的不是宗教,而是鋪天蓋地的機器與市場。除此之外,我們在理念上還針對正在風行的"后現代主義"時代癥。按照一些西方學人的看法,人類的文化方向應是從"現代"走向"后現代",所以必須高舉后現代主義旗幟,必須解構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形而上學體系,包括啟蒙理性,但我們發現"后現代主義"的致命傷:只有解構,沒有建構;只有破壞顛覆,沒有建設建樹。他們用理念代替審美,用"主義"代替藝術。在人文科學中,他們不顧歷史事實,只信如何講述。針對這種時代癥,我們要對他們說個"不"字:不一定要從現代走向后現代,而應當從現代返回古典,即回過頭來正視古典的偉大建樹,重新開掘古典的豐富資源,讓它滋養現代社會,養育現代人過于浮躁、過于急功近利的心靈。
我們講"返回古典",不是返回西方古典,而是返回中國古典。返回不是復古,而是從時代的需要(中國現代人的生存、溫飽、發展的需要)對中國古典重新開掘并進行現代性的提升。中國的"古典"是個巨大的人文體系,我認為這一體系包括兩大基本脈絡:一是重倫理、重教化、重秩序的脈絡;一是重自然、重自由、重個體的脈絡。前者以儒家為代表,后者以莊禪為代表。李澤厚先生認為儒道可以互補,儒法可以互用。同樣講返回古典,李澤厚先生側重講返回孔子,他推出中國十名最卓越的哲學家,排名第一的是孔子,第二才是莊子。十多年來,他潛心研究著述,提出"情本情"、"巫史傳統"、"一個世界"、"樂感文化"、"實用理性"、"歷史本體論"等重大命題,都與重新闡釋儒家學說相關。他的儒學研究包含著許多新的發現。我的返回古典則側重于返回"我的六經",也就是返回莊禪這一脈。無論是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講課,還是在臺灣中央大學、東海大學講座,我都講這一脈。在著述上,我則寫作"紅樓四書",在"四書"中我發現《紅樓夢》巨大的哲學內涵,覺悟到這是繼王陽明之后的一部偉大心學,但不同于王陽明,它是形象性心學。這一偉大心學展示了一個名為賈寶玉的"嬰兒宇宙",呈現了一顆人類文學史從未有過的最純粹的、兼有人性與神性的赤子心靈。我概說了《紅樓夢》五大哲學意蘊:大觀視角;心靈本體;中道智慧;靈魂悖論;澄明之境。上述這一切,都是"返回古典"的初步成果。《雙典批判》也是返回的結果。
你提出這樣的命題,對于今天的中國有什么現實意義?我答不了。我一再說,我只管"念佛",不管"行佛"。只管真誠講述,不求實用意義。
對于"國學熱"我不太熱心。原因是"國學"這個概念本身的內涵不太清楚,只能模糊把握。它是指經學,還是指儒學,還是指考據學?還是指整個中國古代傳統?不太清楚。"國學"最初出現時并不包括蒙學、疆學、滿學等,現在包括不包括?還有,用中國人的視角和語言研究西學包括研究馬克思,算不算國學?有人把季羨林先生也說成國學大師,明明是"外國學大師",怎么變成"中國學大師"了呢?還有,李澤厚的《論語今讀》,你可以納入國學,但他寫的康德批判即《批判哲學的批判》,算不算國學?
15.最近,您提出"創造中國的現代化自式"的新概念?這種現代化自式與現在廣泛熱議的"中國模式"是否是一個概念?為何您認為全世界只有中國有可能創造自式?這種"現代化自式"應該如何創造?
答:我在今年四月初回國參加母校廈門大學九十周年校慶,發表了一篇題為"創造中國的現代化自式"的講話,我講的"現代化自式"與現在廣泛熱議的"中國模式"不是同一個概念。"中國模式"是固定式,"現代化自式"是創造式。李澤厚先生讀了我的稿子就說,"中國模式"是"過去完成式",你講的"現代化自式"是"現在進行式",即現在和未來還需不斷探索、不斷試驗、不斷創造的一種大存在形式。
提出"創造中國的現代化自式"的中心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走自己的路,這一點,講"中國模式"的學者,可能也有這個意思。但我和他們的不同之處除了上邊講的這一點之外,還有一點不同。我認為,創造中國的現代化自式,離不開吸收"普世價值"。"創造自式"不是轉向他式,即不是轉向西式,但不能拒絕"他式"中所蘊含的"普世價值"。不過,我也要說,普世價值也不可能照搬,拿來之后還要從中國具體的歷史狀況進行創造性運用。在這里,"用"不是簡單的事。創造就在"用"字的大藝術之中。
我認定只有中國能夠創造出現代化自式,是因為中國具有以下三個條件:(1)中國擁有數千年積累而成的雄厚人文傳統。人類世界最雄厚人文傳統只有兩個,一個是歐洲人文傳統;一個是中國人文傳統。仰仗這一傳統,中國便有走自己的路的可能。(2)中國已創造出擁有強大國有化基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有此前提,中國進入世界經濟結構和建構,本土經濟結構必定帶有自身的特色,這又提供創造自式的另一種可能,(3)中國在二十世紀的變動與滄桑,經受了世上罕見的巨大苦難和生死體驗,經歷過封建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較量與實驗,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巨大的教訓,深知各種所有制的利弊。正是這種經驗使中國人更具創造自式的智慧。上述三個條件,日本、印度、巴西、加拿大、俄羅斯都不全具備,它們大體上只能走英美式的路。中國雖然具有創造自式的可能,但歷史給予的只有今后二、三十年的時間,錯過這個機會,那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謝謝你對我的兩次采訪。提了這么些有思想的問題,推動我思索。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美國

網載 2015-08-23 08:39:2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