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當我談信仰時,我談些什么∣《文學青年》任曉雯專號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關于任曉雯 任曉雯作品: 《當我談信仰時,我談些什么》 一、偶像 摩西十誡,第一條確認耶和華是唯一神;第二條指出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為何如此重要?因為第一條“別的神”,即指第二條的“偶像”。 提姆·凱樂對“偶像”定義道:當我們的心將某些事物“奉為神明,以它們為生活的中心,因為我們以為只要得到它們,它們就可以提供給我們人生的意義和保障、安全和滿足”,這類事物就成為了偶像。名聲、錢財、事業、愛情、政治、知識……都可能成為偶像。 提姆·凱樂甚至說,生命中美好的東西,尤其容易變成偶像。舉小說《魔戒》為例,黑暗的權能之戒,會敗壞任何使用它的人--包括那些尋求自由公義之人。托爾金專家TomShippey說它是“心靈擴大器”,將心中渴望放大到偶像化比例,從而使擁有高尚目的者,不擇卑鄙之手段。他們沉迷其中,被無限增強地奴役,最終跌倒于偶像化了的渴望之下。(參見《諸神的面具》) 雨果小說《悲慘世界》中的警官沙威,也是視佳物為偶像的典型例子。他將法律看作最高法則、萬物尺度、人生意義所在。但在冉阿讓救了他,他也放過冉阿讓之后,他發現了比法律更高之物:愛和寬恕。“他(沙威)有一個上級,吉斯凱先生,迄今為止他從沒想到過另外那個上級:上帝。這個新長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亂。”法律這個偶像崩塌了,“他(沙威)被感動了,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他覺得自己空虛、無用,脫節……毀了。他跳入陰冷的塞納河中。 提姆·凱樂說:我們的內心不去敬拜上帝,就會敬拜偶像,沒有中間狀態。人為什么有敬拜沖動?在我看來,人有探求生命意義的本能,也有面對死亡問題的恐懼,人需要有比肉體活著這個事實更高的盼望。當人無法認識神,或者認識神,卻又信心不足,會將盼望寄托在偶像之上。 摩西上西奈山四十晝夜,百姓要求亞倫為他們做神像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雖然此前不久,百姓曾目睹耶和華降臨,但在稍縱即逝的敬畏之后,他們又對不可見的神失去信心,希望信靠看得見的人與物,比如摩西(認為是摩西領他們出埃及),又比如神像(造金牛犢)。 相比這些“硬著頸項的百姓”,大先知摩西也沒好到哪里去。這位與耶和華面對面,如朋友般交談的摩西,在耶和華應允請求,同意與以色列人同在之后,繼續請求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神的應允也無法滿足摩西,他希望親眼見到神的榮耀,才能確定神的同在與大能。 我們有與生俱來的對神的渴望,卻困于經驗,囿于肉身沉重,惑于“眼見為實”,愿將確信托付于可見之物。不認識神的,難免把世界上的人與物作為偶像;認識神的,難免有將無限的神拉低到有限的感官范圍的狂妄。(求神跡的心理就是一例)因此加爾文對不可拜偶像的理解是:“這條誡命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禁止我們將無法測度的神局限于我們感官的范圍,或以任何形體代表他。第二部分禁止我們在宗教上敬拜任何形象。” 然而,人的歷史,就是不斷背棄神的誡命的歷史。一次次以他人為偶像--政治偶像引發政治浩劫,文化偶像扼殺文化豐富,宗教偶像引起紛爭、流血、人與神的阻隔。當下更有不少宣稱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事實上轉而以物為偶像--拜金、拜權力;或者以自我為偶像:我是絕對真理,我是至高無上,我沒有敬畏因而能夠為所欲為……難怪加爾文指出:人心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廠。 二、不可見的無限 人渴求“可見”,但因偶像的可見和有限,它們最終難以填補人心當中的終極空缺。托克維爾觀察美國時說:一種“奇特的郁悶縈繞著那些在豐富之中的居民”。美國人相信物質繁榮可以平息他們對快樂的渴望,但托克維爾認為,這種盼望是幻覺,“這世界上不完美的喜樂,永遠無法滿足人心。” 空虛的情圣、不快樂的富翁、內心煎熬的名人……叔本華說:“生命是一團欲望,欲望不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人生需要標桿,否則生命變成一團沒有方向的虛空;而當人以世上可見的人和物為標桿時,又必然通往生命的無意義,因為世界上的喜樂(欲望)是不完美的,我們無法籍此將人生從痛苦與無聊的搖擺之間解脫出來。人存在于世的終極價值,無法從肉身及可見物推導而得,它們只可能來自高于肉體的地方。 更何況,所有人都要面對死亡。“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知道什么與他有益呢?誰能告訴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傳6:12)“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夸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篇90:10)倘若沒有靈魂,沒有比肉體、比世上的人與物更高的東西,一切意義將隨著生命消失而灰飛煙滅,歸于虛空。那活著又是為了什么?我們豈是隨意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豈是白白承担諸多勞苦煩愁,然后白白死去? 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問,和面對死亡的虛無感,是硬幣之兩面:不能解決死亡的虛無,則難以理解生命的意義。因此,相比老話說的“不知生,焉知死”,我更愿相信:“不知死,焉知生。” 如果不將有限置入無限之中,有限本身就沒有意義。神將對永恒的渴望,放在人心里。讀書人想立身后名;藝術家想創傳世作;帝王造像、立碑、風干死亡的肉體……普通人也試圖使生命留下痕跡,所以拍照、錄像、寫日記。然后,在無限的時間面前,人的這些行為都是有限。估且不論碑是否倒,文字是否失傳,照片是否褪色,如果我們認為生命的意義,只存在與活著的肉體相關的一切,那么身后之物再長久,也與生命本身無關。 因此,叔本華所描述的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的人生,是一種絕望狀態。提姆·凱樂區分了傷心與絕望:“傷心是源于失去了某件好東西,其痛苦可以用其他的事物來撫平和安慰,因此如果你在事業上遭受到挫折,還可以在家中找到安慰而得以度過。但絕望則是無法被安慰的,因為它是源于失去了一件終極的東西。當你失去了終極的生命意義和盼望時,沒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幫助你度過,因此你的心靈就破碎了。” 在此意義上,神的超驗不可見性,實在是對人的恩典。耶和華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神必須超驗地存在,才能讓人持續保持仰望和敬畏。而人在仰望與敬畏那無限的、至高的不可見者之中,才能得到廣大與真正的自由,獲取向上與超拔的力量,使我們不至困頓于痛苦和無聊,受制于有限和罪性,沉迷于肉身沉重和人生虛無。正是因為憐憫人的軟弱與短視,神才不讓人見他的面。 三、看、聽、信 正因神是不可見的,人的信不能建立在看的基礎上。“眼見為實”的需求,最終只能導致拜偶像。耶穌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9:41)又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20:29)前者表明理性的狂妄,會遮蔽對神的認識;后者表明終極的信心,出自對不可見的無限仰望。 人是一種視覺造物,他的生活空間已為他能看見和把握的東西所界定。人通過“看”這種理性行為獲得知識。“‘看’在西方思想里占據著核心位置,因為他們的知識來源于‘看’。通過‘看’,人們形成了人生的方向感,得到了效用。”(汪丁丁) 然而,當我們談及“信”,意味著必須承認:人不把“看”當作他自身全部,他的世界也不由他所見之物來界定。在肉體視野之外,在人類理性之上,存在更高的秩序、更恒定的法則。“信”超越了“看”。這也是為什么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信心只用于未見之事。”(奧古斯丁) 在赫拉克利特看來,人所認知的,不過是局部的“意見”,但在各個局部意見之間的對話中,另有自行顯現的世界秩序,他將它稱作“logos”。柏拉圖則認為,人基于局部經驗的看法叫“意見”(doxa),對“意見”的超越,則是“知識”(epistem),知識是認知真理的過程,是“真理自行顯現”的過程。在古希臘人觀念中,人由“看”而得來的知識都是局部的,那個終極的logos、真理,是超越人的局部經驗的,來自作為整體的無限遠的至高者。 既然“看”作為一種經驗方式,是有局限性的,那么通往無限的“信”從何而來?圣經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羅10:17)即:信仰不是思考所得,而是來自聆聽。是聆聽、接受并回答的表現形式。信仰是接受不可見,不可想。但并不是說,信仰與理性相悖。信仰恰恰是理性的起點。任何理性都會回溯到某種不證自明的“我信”。信仰是意義的賦予過程,人只能在那種支持他的意義的框架下行動。不證自明的“我信”包括:我是否相信在人的有限的理性之外,存在恒定真理?我是否相信關于善的法則,是被普遍放置在人心之中的?等等。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區分“作為一種性質的善”和“作為一種關系的善”。前者因表現了善之共相而被稱為善,后者因成為有用之事而被稱為善。摩爾在此基礎上說:“善是簡單的、非自然的、不可定義的特定事物的質”。首先,善是簡單的(simple),其次,它是非自然的、不是自然界有的(non-natural),即:它是抽象的、看不見的;最后,它是不可定義的(indefinable)。綜合起來,即:善這個概念是不可被定義的、也是抽象不可見的,無法被論證的。這種無法被論證的簡單概念,就是我前面所說的“理性的起點”。任何理性都會回溯到某種不證自明的“我信”。這樣“理性的起點”,是被放置在人心之中的。 這是為什么,神禁止人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善惡的絕對標準在于神,不在于人。人自以為神,自行分別善惡,會將于己有用之事當作善。這種利己心就是墮落和罪性。這也是為什么,倘若不認為真理來自更高的絕對者,人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局限,容易自以為占有真理,自以為是真理化身。 四、懷疑 正因以上種種,在承認“我信”的同時,也要承認另一個事實:“我懷疑”。神賜名雅各“以色列”,以色列是“與神角力”之意。它暗示著:人的信仰之路從來都是一場艱辛的“與神角力”,充滿著懷疑、抗爭與背離。 比如“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也有不信的時刻。他不信神能賜予平安,為求保命而謊稱妻子撒萊是妹子;他不信神能賜予后裔,同意娶妾生子,導致家庭紛爭,乃至未來歷史中的民族紛爭。 比如以虔誠聞名的圣女小德蘭,死前幾個星期陷入絕望的懷疑:“一種最壞的無神主義誘惑在猛烈地攻擊著我。” 又比如特蕾莎修女也有秘密的信仰危機。《特蕾莎嬤嬤:成為我的光明》(特蕾莎書信匯總)一書披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前三個月,她在給精神密友邁克爾皮特的信中寫道:她心里畏懼于那個并不存在的基督。“耶穌將贈予你特別的愛……但是對于我,沉默和空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想看卻看不到,想聽也聽不來。張開了祈禱的唇舌,卻發不出聲音……我想你應為我祈禱,以使我能讓基督有一個慷慨的選擇。”大衛·畢摩寫道:“一些信件公開有悖于她(特蕾莎)的期望,盡管她要求銷毀一些信件,但是最終還是被她的修道院所保留下來。在40多封未曾公布于眾的信件里,特蕾莎抱怨煩躁、黑暗、孤獨和痛苦,將地獄的情況和她所經歷的做了比較,她說,這讓她懷疑天堂的存在,乃至上帝。特蕾莎強烈恐懼于內心世界和公眾舉止的不一致。” 因為見不到神,因為肉身沉重、內心軟弱,“信”對于人來說,并非全然的、一勞永逸的。信仰者只能在虛無、誘惑、疑問之路上,不斷完善自己的信。 然而,這樣的沉重與軟弱,何嘗不是出于神的秩序?在神的秩序里,有善,也有惡。有光,也有暗。人有信,也有疑。上帝全然掌控,又給人以自由意志。創世之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創1:4)神并不因為“光是好的”,就消滅暗,他允許暗的存在,并將光與暗分開,形成秩序。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別光;有惡的存在,才能認識善;因為有懷疑,才能更堅信;人作為如此渺小的受造物,能夠擁有自由意志,能夠在信與疑的張力之間,施展想象力和理性的能力,這何嘗不是神的大能與美意。 信仰者有懷疑,與此同時,無信仰者也并非封閉自足。唯物主義者難道不會疑慮:人類僅僅是一堆蛋白質組合嗎?在我們可見的、物質的世界之外,難道沒有別樣的存在?馬丁·布柏寫過一個故事:某位啟蒙運動追隨者,聽說伯弟柴夫有一位拉比,就去與之爭論。拉比對他說:“孩子,那些與你爭論的神學家白費口舌了。他們不能把神及其國度擺到你面前的桌子上,我也不能。但是,孩子,請你想想,那也許是真的!”這個“也許”擊敗了年輕的無神論者。 信仰不是可以被“擺到面前的桌子上”的東西,它不可見,也不能被演示。然而,人的肉身所能見、理性所能認知的領域,是不是一個絕對性領域?如果一個人還沒驕傲到自認為宇宙真理的話,他就得承認:這個領域只是人類存在乃至整個存在的一個層面,在這個層面里的事物不具有終極性質。在肉身之外、理性之上,永遠存在著那個“也許”的誘惑--那也許是真的呢!也許上帝存在呢! 由此,信仰者會受到無信仰的侵襲,無信仰者也會受到信仰的誘惑與侵襲。“在這種疑惑與信仰、誘惑與確定之間的不斷競爭中尋獲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命運歸宿的基本模式。也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疑惑使雙方不致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成為雙方交流的通衢。疑惑可使雙方避免沉溺于完全的自滿自足中;它使信仰者向疑惑者開放,也使疑惑者向信仰者開放:對一方來說,他分享無信仰者的命運;對另一方來說,信仰還是一種挑戰。”(約瑟夫·拉辛格) 有一首贊美詩,每次吟唱我都受感動。詩唱:“我真無法解釋,天天疑惑,天天相信。”在我看來,沒有懷疑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對于信仰者而言,勇于面對疑惑,才能在信仰之路上前行。“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需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10:12)人是軟弱、多疑、時時站立不穩的,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才可能加固信心。保羅說:“我更喜歡夸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后12:9)”所以,我愿天天疑惑,天天相信。持續禱告、仰望與敬畏。 寫于2013年3月22日 本作品由任曉雯授權《文學青年》發表,轉來請注明出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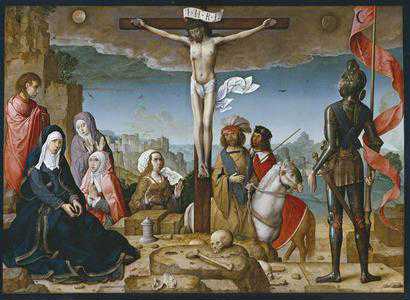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0:5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