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真實的“夜校”:睡眠中的大腦?
 |
>>> 創業先鋒 眾人拾柴火焰高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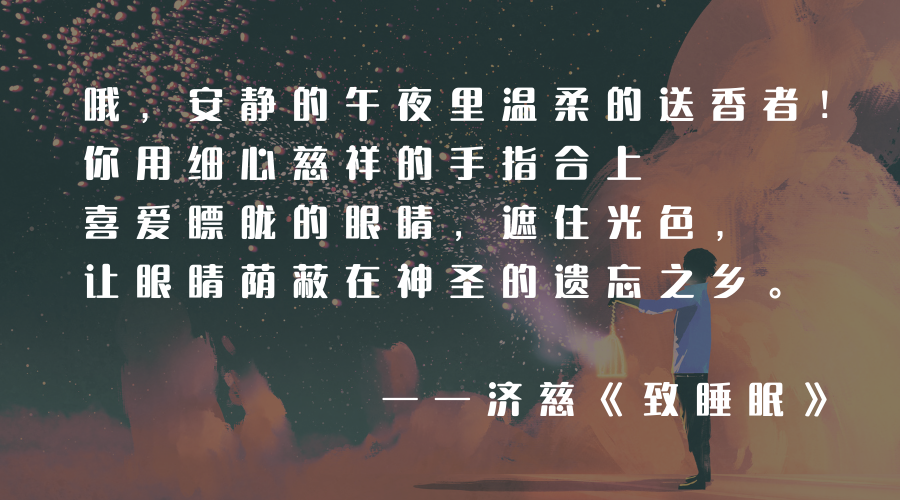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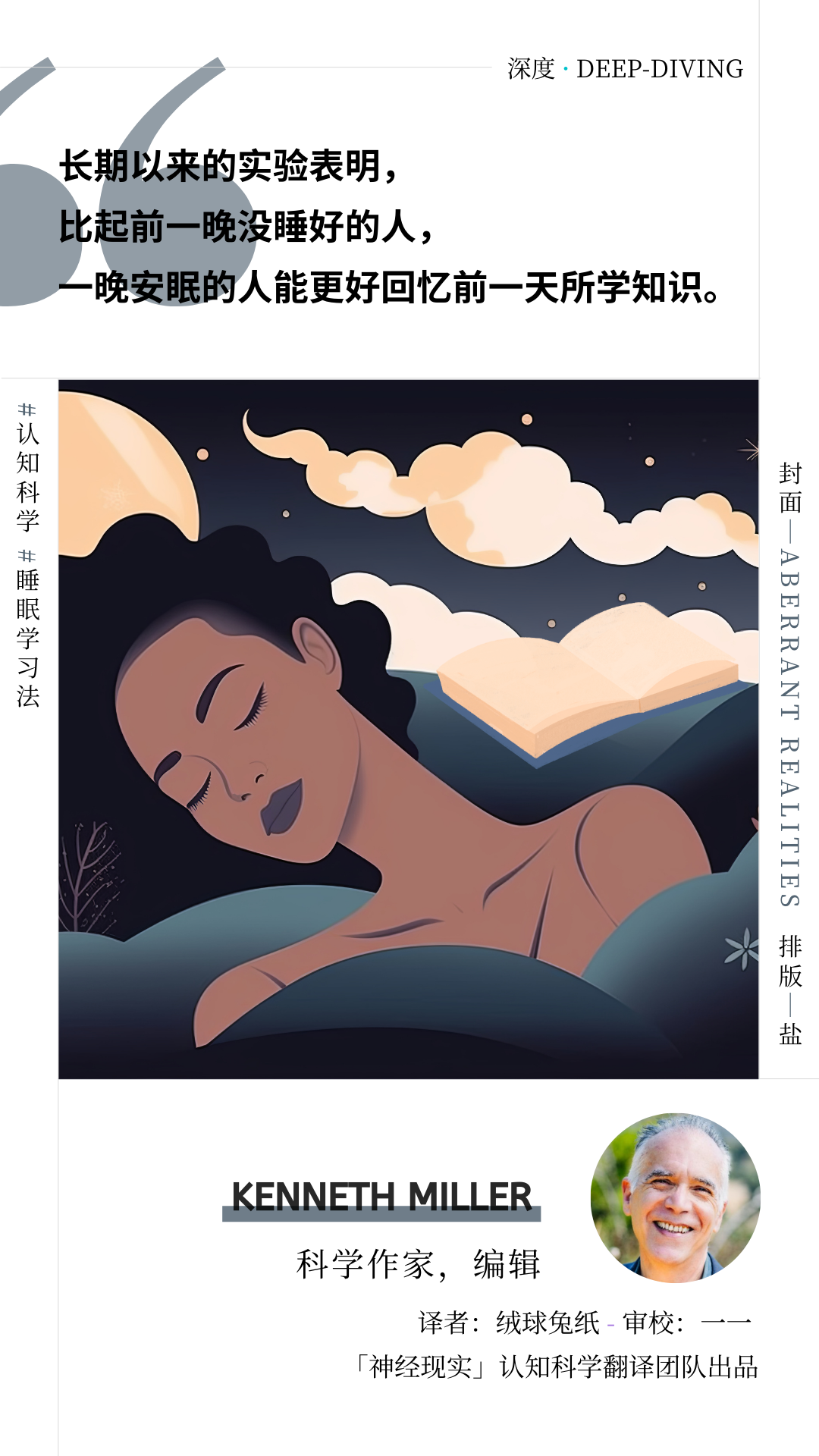


每次出國旅行,我都希望能掌握幾句當地語言,流利與否是另一回事。我是語言老師的兒子,小時候學過法語。20 來歲在墨西哥漫游時,我學會了西班牙語,但在那以后,我就忙碌起來。盡管終生渴望學意大利語,不過人到中年,我還是只會“Per favore”和“Grazie”。最近,米蘭附近的一個會議邀請我參加,這讓我又想冒險嘗試。但每天都被工作期限和家庭義務塞得滿滿的,我沒一丁點時間上夜校,或通過 APP 在家學。我猜,也許我能通過睡眠中聽錄音來掌握這門“美麗的語言”(la bella lingua)。
近一個世紀前,“睡眠學習法”的熱潮席卷了整個工業化社會,直到神經科學家確定該方法在生理上并不可實現,熱潮方才褪去。然而今天,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當年那些神經科學家們或許錯了。睡眠學習法似乎正走向復興,科學依據比其前身要堅實得多。通過對睡眠進行一些工程性的調整或修正,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大腦每晚的離線時間,為吸收信息爭取寶貴時間。經過許多夜晚,我們可以極大擴展知識和技能儲備,甚或治療頑固癮癖和心理創傷。但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該歡迎還是害怕這種前景?如果我們利用睡眠來自我提升,我們是否會失去某些自身的本質?
由來已久的睡眠學習法
人類可以在睡眠中學習的觀點至少可追溯到《圣經》時代,上帝讓雅各布在夢中看到天使爬上天國之梯,從而瞥見自身命運。但從這個概念中賺錢的第一人是阿洛伊斯·本杰明·薩利格(Alois Benjamin Saliger),一位生于捷克、居于紐約的商人兼發明家(據時人描述,他“高個子,身材瘦削,薄嘴唇,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和寬闊前額”),于 1932 年獲“心理電話”專利。這種留聲機裝有一個重復裝置和一個小喇叭,可以放在睡眠者的床邊,以耳語的音量重復播放口語錄音。和它一起銷售的還有一些唱片,唱片名包括《繁榮》《靈感》《正常體重》和《交合》。
薩利格在最后一張唱片中莊嚴吟誦:“我渴望一個理想的伴侶,我散發著愛的光芒,我擁有迷人且有魅力的個性。我有強烈的性吸引力。”如果這臺機器的功能正如廣告所言,那么用戶醒來時就會充滿無可阻擋的自信,準備大步流星地征服被其揀選的領地。
“心理電話”的運作前提是,人們在睡眠狀態下和催眠狀態下一樣易受暗示,阿爾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中就曾采用了這個未經證實的理論。小說里,錄音訊息用以訓練熟睡的兒童,讓他們形成一種缺乏人性、道德和情感的未來社會價值觀,赫胥黎將其稱為“睡眠教學法”(hypnopaedia)。書中,一位自豪的官員說,這種新方法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教化和社會化力量”。
盡管睡眠教學法從未在現實世界中用于大規模灌輸教育,但它逐漸被廣泛當成工具,用來傳授新技能或改變不良行為。科學研究似乎表明它是有效的。在一項研究中,一群熟睡的人聽到了一串中文詞匯及英文翻譯的錄音,第二天,他們在理解測試中的得分明顯高于對照組。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 20 名有咬指甲習慣的男孩,每晚播放 300 次短語“我的指甲嘗起來苦得要命”,播放了 54 晚。試驗結束時,據報道,40% 的男孩克服了他們的惡習。這種方法在蘇聯變得特別流行,據說整個村莊的人都在打盹時學外語。
這種觀念在上世紀 50 年代迎來反轉,那時候科學家們開始使用腦電圖(EEG)技術。有了這項技術,他們終于可以確定受試者是否真的睡著了,而不是昏昏欲睡或僅在閉眼休息。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威廉·埃蒙斯(William Emmons)和查爾斯·西蒙(Charles Simon)向一些男性反復播放 10 個單詞的列表,這些男性的腦電圖顯示當時他們腦中沒有α波(這是睡眠的可靠指標)。結果,他們在清醒后記憶測試中的表現,并不比隨機情況好。其他腦電圖監測試驗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科學共識很快達成:熟睡中的大腦無法接收外界信息*,睡眠教學法被歸為江湖醫術的范疇。
* 譯者注:最近發表于《自然-神經科學》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神經現實已作相關編譯,詳見意識帷幕的縫隙,或將改變睡眠的定義?
現在,鐘擺又開始擺動了。盡管還沒有切實有效的方法存在(除了網上騙子們的聲稱),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睡眠教學法原則上是可行的。如果能克服某些技術難題,它將真正開辟一個“美麗新世界”。
人們對睡眠學習法產生新的興趣,是因為對“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流口水時,我們的大腦在做什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長期以來的實驗表明,比起前一晚沒睡好的人,一晚安眠的人能更好地回憶起前一天所學的知識。但這是為什么呢?
睡眠中學習為何可能
有一種理論認為,大腦在以快速眼動(REM)為特征的夢中,演習前一個白天的新信息。然而,實驗室研究最終否定了這一觀點。到了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數據顯示了另一種觀點:記憶主要是在被稱為慢波睡眠(SWS)的深層無夢睡眠階段演習的。(因為大腦腦電活動在高峰和低谷之間從容地循環,所以稱為“慢波睡眠”。)
研究人員發現,在慢波睡眠階段,大鼠海馬中特化的“位置細胞”會重放白天學會跑的迷宮路線。其后的研究表明,人類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重現新記憶。海馬會作為記憶的臨時倉庫,直到這些記憶在大腦皮層(語言、感知覺和思維所在)形成生成較慢但更永久的連接。
隨著“熟睡中的大腦為消化白天學習的內容做了多少工作”逐漸變得清晰,“熟睡中學習”的概念也就似乎不那么牽強了。
1996 年,日本研究人員通過誘發心理學家所謂的條件反射——將兩種刺激聯系起來,使重復第二種刺激觸發通常與第一種刺激相關的反應——對睡眠學習法的基本形式進行了測試。他們對五名睡眠者的腿部進行了輕微電擊,同時播放了一種聲音信號;醒來后,被試單獨聽到這個聲音信號時,出現心跳加快。研究證明,熟睡中的被試至少下意識地回憶起了這一聲音信號。
2007 年,由德國呂貝克大學醫學心理學家詹·伯恩(Jan Born)領導的研究小組,利用嗅覺線索觸發了完全有意識的記憶(陳述性記憶)。他們首先在被試記憶電腦屏幕上的物體位置時,將玫瑰花的氣味送入受試者的鼻孔。然后,部分被試在慢波睡眠期間再次接觸到這種香味。當這部分被試醒來時,他們回憶物體位置的準確率,比睡眠時未接觸香味的對照組高出 15%。
在隨后的實驗中,芝加哥西北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肯·帕勒(Ken Paller)教被試在鍵盤上演奏一段簡短的旋律。然后,當被試小睡時,對他們中的一半重復播放這段旋律。醒來后,這一組被試彈奏該旋律的錯誤率低于安靜睡覺的那一組人。另一項研究與我的語言學探索直接相關:在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被試在白天學習荷蘭語單詞,晚上在慢波睡眠中重放這些單詞后證明,他們能夠更好地回憶和翻譯這些單詞。這些音樂和語言試驗表明,聽覺線索可以直接觸發特定任務的記憶演習——完全不需要條件關聯。
熟睡時也能學習新知識?
總之,這些研究近乎證明了睡眠學習法的概念。但有一點是缺失的:所有實驗涉及的技能或信息都是在清醒時首次學習的。為了證明睡眠教學法的作用,科學家必須向熟睡中的被試教授新知識。
2015 年 3 月,研究人員在《自然-神經科學》上報道他們已做到了。由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神經生物學家卡里姆·本切納內(Karim Benchenane)領導的研究小組,首先在小鼠大腦中植入電極,記錄它們在一米寬的圓形平臺上找路時,位置細胞的激活情況。研究人員為每只小鼠選擇一個位置細胞,然后等待它在睡眠中重新激活。在那時,他們用低壓電流刺激小鼠大腦的獎勵中樞,創造強烈的快感。當小鼠醒來時,它們會沖向與位置細胞相關的位置,在那里逗留,顯然是在期待另一個獎勵。科學家們制造了一種虛假記憶,改變了動物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行為方式并不是之前清醒時的經驗所導致的。
本切納內的研究采用正強化的方法對被試小鼠進行訓練。與此同時,以色列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們對人類尼古丁成癮者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在慢波睡眠期間使他們暴露在香煙和臭雞蛋(或臭魚)的氣味中。得益于這種厭惡性條件反射,參與者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減少了 30% 的吸煙量。
而在美國西北大學,神經學博士后凱瑟琳娜·豪納(Katherina Hauner)設計了一種在慢波睡眠過程中消除負面關聯的方法。首先,她向志愿者展示人臉圖像,同時給予不愉快的電擊;與此同時,她讓志愿者暴露在薄荷、檸檬或松樹的氣味中。被試很快就學會了將人臉與疼痛聯系起來。然后,在他們睡覺時,豪納讓他們單獨接觸這些氣味。起初,他們的反應是恐懼(通過皮膚上的微量汗液測量得出),但這種反應隨著氣味重復出現而減弱。當被試醒來時,他們看到那些面孔時的焦慮也隨之減輕。
不難看出,這種技術可以帶來多么大的改變。當我在芝加哥給帕勒打電話時,他說:“我們正處于試圖弄清‘沉睡的大腦能做什么’的最前沿。在短期內,我們可能會利用睡眠中已經發生的處理過程來改善學習。”升級后的“心理電話”可以設計為在慢波睡眠時提供提示,也許能幫助學生更快地掌握一門學科,但白天的學習仍然是必要的。該設備可與搭載經顱電刺激的頭帶配對使用,經顱電刺激在特定頻率下可加深慢波睡眠。“豪華套餐”中還可包括一臺香氛機,以增強整體效果。
睡眠學習法可用于治療,用對相同事件不太激烈的回憶取代創傷記憶。這可能需要藥物來撬開神經閘門,讓“超級心理電話”將內容直接輸送到海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科學家們最近發明了一種方法,可以在被試觀看視頻時記錄她的神經模式,將其轉化為計算機代碼,并生成原始圖像的模糊近似值。也許有一天,這個過程會被完善和逆向工程化,為初學者提供“神經可下載的”(neuro-downloadable)意大利語多媒體課程。
這個方法的潛力是顯而易見的,且不僅是對像我這樣過于繁忙的語言怪才而言。各個領域的學生都能以比現在快一倍的速度達到熟練程度,并學到雙倍的知識。任何人想要獲得新的工作技能、掌握一門樂器或探索錯綜復雜的粒子物理學,都能以近乎神奇的速度輕松實現。
那么,代價是什么呢?
但風險似乎也是顯而易見的。睡眠教學法可能會破壞睡眠中通常會出現的恢復功能——例如,修剪多余的神經連接,為即將到來的記憶騰出空間。經過一夜無意識考試后,第二天學習新知識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睡覺時學習也會減少大腦用于鞏固長期記憶的能量,也許會導致去年伊斯坦布爾之行的記憶被抹去。它可能會破壞神經膠質細胞夜間清理大腦代謝廢物的功能,增加學習者患神經退行性疾病(如阿爾茨海默病)的可能性。
睡眠期間,大腦會重新平衡免疫和內分泌系統,這就是為什么睡眠障礙與抑郁癥、肥胖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等疾病相關。擺弄大腦的控制過程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
此外,還必須考慮到不太明顯的代價。我已經上了年紀,還記得智能手機出現之前的生活,那會兒,在一天中的某些時間,甚至連續幾天失聯,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種失聯的寧靜狀態現已成為“失落的伊甸園”。如今,若我的編輯發來緊急詢問郵件,我沒有理由不在清醒時回復。但至少,睡眠時間仍是禁區。但在睡眠教學法盛行的未來,這種界限也可能消失。
想象一下,你老板要求你在熄燈后,將明早要報告的數據下載到大腦中。想象一下,你的同事們在墨菲斯*的懷抱里,討論他們追的電視劇。想象一下,你的臉書好友們會發布他們每晚學習普通話的最新情況。如果我們屈從于 24 小時可觸達、可通信和可生產的要求,我們將犧牲什么?
* 譯者注:墨菲斯(Morpheus),希臘神話里的夢神。
臣服于睡眠吧,就像臣服于愛情
睡眠心理學家魯賓·奈曼(Rubin Naiman)在其著作《治愈之夜》中講述了他小時候與母親玩的一個游戲。他母親會問:“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什么?”小魯賓會大聲說出自己的猜測(“玩具!卡通!雪糕!”),直到她說出正確答案:“夜晚。”奈曼的母親曾在納粹集中營度過了四年,在那段地獄般的生活中,她學會了珍惜黑暗中的時光,將其視為應許之地。“夜晚帶來睡眠,”奈曼寫道,“這是每日重要的安寧。相應的,睡眠又是通往夢的天然橋梁。而夢境則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神秘入口,通向一個更可塑的、更具同情心的現實。”
奈曼觀察到,這種敬畏在傳統社會中很常見,但在被過度照明的西方,它幾乎被拋棄了。我們大多數人認為,夜晚是一種不便,而睡眠只不過是為第二天充電的一種手段。我們盡可能少睡覺,當睡眠不能如期而至時,就吃藥讓自己昏昏欲睡。然后,我們用興奮劑來彌補真正休息時間的不足。奈曼論證,我們“以醒來為中心”的世界觀,正在損害我們的精神、身體和心理健康。他認為,我們能通過“恢復夜晚和夜間意識的神圣感”來收獲益處。
當我問奈曼對睡眠教學法的看法時,他把它比作用做愛來消耗卡路里,或邊上廁所邊吃東西。他告訴我,睡眠是消化數據的時間,而不是攝取數據的時間。睡眠也是我們放棄晝伏夜出的追求,徜徉在內心隱秘中的時刻。奈曼說:“我們談論墜入愛河和入睡,兩者都需要一種臣服。”睡眠的主要樂趣之一(就像愛情一樣),是它把我們從時間中拉出來,進入一個每刻都是獎勵的領域。
相比之下,睡眠學習法則是拒絕進入無意識的睡眠狀態。它代表了“喚醒中心主義”(wake-centrism)的終極目標:完全征服黑夜,把它變成一個完全可以利用的殖民地。在這樣的環境中,不戴耳機上床睡覺就像出門不帶手機一樣不可想象。在世界的某處,一個新時代的薩利格肯定正在暗中策劃從這樣的場景中獲利。
我特此掛上“請勿打擾”的標志。拜托了,阿洛伊斯,讓我睡覺吧!
作者:Kenneth Miller
翻譯:絨球兔紙 審校:一一
封面:Aberrant Realities 排版:鹽
原文:If we can learn while asleep, when will we ever switch off?
2023-11-10 17:03:4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