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胡德夫●侯德健●羅大佑的音樂與人生
 |
>>> 深入傳統文化及個人修身養性 >>> | 簡體 傳統 |
6月18日,有“臺灣首席文藝青年”之稱的馬世芳,在“看理想”(公眾號ikanlixiang)的視頻節目《聽說》就將在優酷土豆和大家見面。馬世芳是公認的臺灣流行音樂最忠實的觀察者與記錄者,在總長16集的《聽說》里,馬世芳娓娓道來一首首歌、一個個音樂人的前身后世,在喚醒不止一代人集體記憶的同時,也讓我們對時代的限制與變遷不勝唏噓。馬世芳的新作《耳朵借我》簡體版也將同步上市,這是馬世芳首部專講“中文世界”的音樂文集,某種程度上亦可視作《聽說》的來處。以下節選胡德夫、李雙澤、侯德健、羅大佑的音樂與人生故事,讓大家先睹為快。 胡德夫●侯德健●羅大佑的音樂與人生 文|馬世芳 ●●● 美麗之島 胡德夫、李雙澤《美麗島》 ▼ 二○一一年五月二日晚上,六十一歲的胡德夫——我們叫他Kimbo——在北京通州運河公園“草莓音樂節”登臺獻唱。舞臺底下黑壓壓一大片人頭,幾乎都是二十啷當的青年。他們定定站著,雙眼放光,一臉虔誠。這是“臺灣舞臺”的最后一段節目,同時會場兩邊大舞臺的壓軸表演也正火熱:一邊是“二手玫瑰”,另一邊是謝天笑,暴躁的音浪自遠方一左一右轟轟然輾過來。Kimbo沒有樂隊伴奏,他的武器只有一架鍵盤,和他的一把老嗓子。偶爾,年輕的口琴手小彭會躥上臺去吹幾段,聊作幫襯。 當Kimbo粗壯的手指滑過琴鍵,開口唱歌,所有背景噪音瞬時像海潮一樣退去。 我確實看過許多次Kimbo的演出。七○年代末我還是小學生,便曾在臺北“國際學舍”或者“國父紀念館”的演唱會上,看過一頭黑發的青年Kimbo彈平臺鋼琴唱《牛背上的小孩》。我也曾在世紀初的臺北“女巫店”看他唱歌,客人只有寥寥幾桌。二○○五年他終于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在臺北“紅樓”劇場辦發表會,那夜我也在座。三十年前的青春狂夢、二十年前的沖州撞府、十年前的憔悴落魄,盡成往事。臺下冠蓋云集,昔日戰友多少恩怨情仇,如今許多已是臺灣最有錢最有權的人。Kimbo開口唱歌,他們齊齊落淚。散場時那些翻臉多年、各事其主的頭臉人物真誠地緊握雙手,勾肩拍背,相約宵夜飲酒。仿佛起碼這一個晚上,借著Kimbo的歌,他們可以回到世界還沒那么復雜的時代。 經歷過那些場面,我以為能經驗的都經驗過了,我將好整以暇聽完這場演出。然而Kimbo唱起《美麗島》。歌到中途,我發現自己正嘩嘩地流眼淚。我赧然抹了把臉,偷偷張望左右前后,他媽的,每個人都在抹眼淚,連音控臺前的大哥也未幸免。 這大概是我不止第十遍聽Kimbo唱這首歌,我以為《美麗島》很難再讓我哭了。打從八○年代末——臺灣解除戒嚴、這首歌“開禁”的時代算起,大概有二十多年,我在任何演唱會聽任何人唱這首歌都會掉眼淚。天知道,李雙澤和梁景峰一九七七年寫下《美麗島》的時候,連一絲一毫悲壯的意思都沒有呀。這原該是一首明亮、開闊、歡悅的歌。是后來發生的事,為它披上了苦澀的色彩。 Kimbo在臺上說:“我最后來唱一首頌贊大地的歌,叫做《美麗島》。”底下一片歡呼鼓掌,我暗暗吃驚于彼岸青年人對Kimbo與臺灣樂史的熟悉,畢竟這首歌從未在此地公開發行。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唱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Kimbo豪氣地說:“歡迎到臺灣來!”全場歡聲雷動。 我記得七○年代末的“校園民歌”演唱會,最后安可曲總是合唱《美麗島》——那時這歌還沒變成“黨外雜志”的名字,大家不大把它跟政治聯想在一起。七八歲的我聽到“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總是忍不住咯咯笑。怎么會有人把香蕉和玉蘭花寫成歌詞呢? 《美麗島》的作曲人李雙澤,是一個愛唱歌、愛寫文章、愛畫畫、愛拍照、愛交女朋友的家伙。他大學沒念完,賃居淡水一棟叫“動物園”的房子,淡江師生和各路藝文人士經常在那兒熬夜聚談,儼然“沙龍”。他亦曾浪游世界,看遍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江湖風景。李雙澤最著名的事跡,是在一九七六年一場校園演唱會拎著一瓶可口可樂上臺,質問唱“洋歌”的青年:“全世界年輕人都在喝可口可樂、唱洋文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里?”傳說他后來一氣擲碎了那瓶可樂,但據當天在場者回憶,那恐怕是夸大的神話。無所謂,李雙澤的“嗆聲”,震撼力并不下于當眾打碎一只玻璃瓶。 既然點了火,他也以身作則,開始寫歌,并用簡陋器材錄下一些作品。一九七七年九月,李雙澤跳海救人,竟溺死在淡水,時年二十八歲,他甚至來不及自己錄下親自演唱的《美麗島》。告別式前一天,老友Kimbo和楊祖珺借用“稻草人”西餐廳的錄音器材,就著李雙澤的手稿彈唱這首歌,留下了《美麗島》的第一個錄音版本,在葬禮現場初次播放。這個版本后來屢經轉拷,地下流傳許多年,直到二○○八年才正式收錄到楊祖珺《關不住的歌聲》專輯。 我偶爾會想:設若早生二十年,我會變成李雙澤的哥們兒嗎?大概不會。李雙澤是一個倔強、熱血、滿心正義感的家伙,并且就跟許多那個歲數的青年一樣,深深相信自己看到的道路,才是最正確的道路。若是身在一九七六“可樂事件”現場,我想,我不會為他的唐突與無禮喝彩。 我在青年時代也認識同樣倔強、熱血、滿懷正義的同輩人,他們才氣確實遠不如李雙澤,我總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幽默感,他們深深相信自己可以改造世界,凡不這么相信的人則必須被改造。他們刻意不修邊幅,個個活成浪人模樣,仿佛這樣就可以擺脫他們多半不壞的出身,假裝自己屬于那個他們從未屬于過的階級。他們崇尚“草根”的土味兒,崇尚“素人”與“民間”這樣的詞匯,敵視精致、敵視文氣、敵視“為藝術而藝術”。他們認為在這危急的時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他們隨時要“啟蒙”你。而我始終覺得所謂自由,就是讓人能有“置身事外”的權利。一旦我們變得和我們反抗的對象一樣無趣、滿嘴教條、隨時隨地逼人表態,那革命還有什么意思?——不消說,我們看彼此都不是很順眼。 聽著李雙澤那些粗糙的老錄音,我不禁想起青年時代認識的那些人。若我與李雙澤生在同一時代,多半也會被他目為“覺悟性不夠”、“革命純度不足”的那種人吧?設若如此,我該感到羞愧嗎? ●●● 巨龍之眼 侯德健《龍的傳人》 ▼ 看胡德夫的前一天,我在北京“鳥巢”國家體育館看了整場“滾石三十年”演唱會。其中一個饒富深意的段落,是侯德健和李建復同臺唱《龍的傳人》——李建復是這首歌的原唱,至于侯德健,這首歌的詞曲作者,已經二十多年未曾在大陸公開演出了。那段表演不算特別純熟,恪于時間壓力,歌曲沒能唱全,老侯還唱錯了一段詞。但當李建復介紹侯德健出場,唱了兩句《歸去來兮》,仍讓我心震動: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 是多少年來的徘徊 啊,究竟蒼白了多少年 是多少年來的等待 啊,究竟顫抖了多少年 侯德健,還認識這個名字的兩岸青年恐怕不多了。然而只要回頭專心聽過,你應該也會同意,他實在是七○年代“民歌運動”孕育的那群青年創作人之中,才氣、底氣俱足的將才。他的創作很早就脫去了彼時“校園民歌”習見的文藝腔,語言干凈而坦率,并且擅長從“小我”經驗寫出“大我”情結。比方后來讓包美圣唱紅的《那一盆火》: 大年夜的歌聲在遠遠地唱,冷冷的北風緊緊地吹 我總是癡癡地看著那,輕輕的紙灰慢慢地飛 曾經是爺爺點著的火,曾經是爹爹交給了我 分不清究竟為什么,愛上這熊熊的一盆火 別問我唱的什么調,其實你心里全知道 敲敲胸中銹了的弦,輕輕地唱你的相思調 侯德健生于一九五六年,比李雙澤小七歲。他曾說:“政治本該是人的一部分,人不應該是政治的一部分。”——然而事與愿違,侯德健半生浪蕩顛簸,幾乎都和“政治的一部分”難分難解。他老是在錯誤時機做正確的事、在錯誤場合說正確的話,結果這個名字就這樣曲曲折折跌進了歷史板塊錯開的裂縫,被海峽兩岸以各自不同的理由遺忘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宣布將在次年元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是臺灣自一九七一年被趕出聯合國以來,連年對外關系挫敗的最后一擊。二十二歲的侯德健在這一天寫下《龍的傳人》——說真的,這首歌旋律簡單、歌詞粗糙,絕非侯德健最講究的作品。但是一首歌的命運,往往連創作者都無法逆料。侯德健做夢也想不到這首歌將如何改變他的生命,帶給他多少光榮和詛咒。 《龍的傳人》先以手抄曲譜的形式傳唱開來,繼而在一九八○年由李建復錄成唱片。將近三十年后,我初次聽到侯德健一九七九年親自彈唱的demo,才發現《龍的傳人》原本是一首哀怨而壓抑的民謠,與我們熟悉的悲壯情緒相去甚遠。當年是制作人李壽全和編曲家陳志遠,合力把這首歌“托”了起來:悠揚的法國號前奏、沉郁跌宕的混聲合唱、浩蕩的管弦樂團……當然還有李建復正氣凜然的清亮歌聲。他們讓《龍的傳人》徹底擺脫哀怨,變成了一首悲壯的史詩。 QQ音樂沒有侯德健版《龍的傳人》,此處為純音樂版。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里常神游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涌在夢里 這是一個在臺灣出生、成長的眷村子弟,對素未謀面的“故土中國”的執迷。我們想起楊弦唱過的余光中《鄉愁四韻》:“給我一瓢長江水呀長江水/那酒一樣的長江水”——長江黃河對彼時的臺灣青年,仍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符號。 此為羅大佑版,QQ音樂沒有楊弦版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長成以后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在“鳥巢”九萬人的會場,再度聽到這久違的熟悉的歌詞,仍不禁感到錯亂。歷經三十年歲月沖刷,物換星移,如此單薄天真的圖騰標簽,在我耳中益發顯得不合時宜。 而那天在“鳥巢”,他們沒能唱到關鍵的第三段: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里 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姑息的劍”是為了配合審查而改的詞。侯德健更早的版本有二:“洋人的劍”或者“奴才的劍”。“洋人”指列強逼壓,“奴才的劍”則把責任歸到了不爭氣的“自己人”,更耐人尋味一些。 整首歌直到這邊才轉入悲憤。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的恥辱,和臺美“斷交”、洋人“背棄”這片島嶼的現實前后映照。嚴格講,這段歌詞潦草而文氣不通,但正是這曖昧的仇憤,讓《龍的傳人》能夠跨越兩岸、在不同的時代凝聚起不同的群眾——它勾起了“同仇敵愾”和“恨鐵不成鋼”的心情,這在臺美“斷交”之后被孤立于國際社會的臺灣,以及邁入改革開放、重返世界舞臺的大陸,都能找到集體焦慮的連接點。于是它先被國民黨“綁架”成官媒炒作的“愛國歌曲”,直到侯德健一九八三年干犯禁忌“出走”大陸,《龍的傳人》在臺灣一度變成禁歌。在此同時,它開始在對岸傳唱,相同的詞曲,卻能映射出另一種光譜。 三十多年過去,臺灣是老早告別《龍的傳人》的意識形態了,而我深深覺得彼岸亦未必需要這條身姿曖昧、體腔空虛的巨龍。見到侯德健終于得以公開登臺演出,我衷心為他歡喜。然而老實說,同樣關于歷史和家園,我更愿意再唱一次《美麗島》,再聽一次《少年中國》。我還更愿意拿出蒙塵的老唱片,再放一次侯德健“出走”對岸之后寫的《歌詞一九八三》,那年老侯二十七歲: 回想起當年,沒問完的問題很不少 只是到如今,還需要答案的已經不多 關于鴉片戰爭以及八國聯軍, 關于一八四○以及一九九七 以及關于曾經太左而太右,或者關于太右而太左 以及關于曾經瞻前而不顧后, 或者關于顧后卻忘了前瞻 以及或者關于究竟哪一年,我們才能夠瞻前又顧后 或者以及關于究竟哪一天,我們才能夠不左也不右 ●●● 白色的恐懼,紅色的污 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 ▼ 甲午戰爭百余年來,臺灣不斷接受外來文化與新移民的刺激,遂也漸漸習慣了“混血”式的文化樣態。臺灣曾經戒嚴近四十年,然而針對文化內容的管制,較諸政治體制的壓抑,相對還是寬松一些,舶來文化商品繁多。到七○年代“尋根”風起,青年世代重新摸索“身份認同”,首先要面對的,也是這盤根錯節的“混血”情結。 一九七一年奚淞、黃永松、吳美云、姚孟嘉創辦《漢聲》雜志英文版,一九七七年改為中文版,深入探討古跡保護、民間藝術與庶民文化。一九七三年林懷民創辦“云門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提拔新銳作家,推行報道文學,引介素人畫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陳達。一九七五年歌手楊弦在中山堂開演唱會,出版專輯,替余光中的現代詩譜曲,點燃“民歌運動”。一九七六年李雙澤在淡江大學演唱會手持可口可樂,怒道“走遍世界,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都是洋文歌”,遂令“唱自己的歌”成為廣為流傳的精神口號。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深化、普及了“尋根意識”,同年“金韻獎”創辦,“青年創作歌謠”風潮徹底改變了華語樂壇的走向。 這些事件,都有一股純粹近乎天真的底氣。事起之初,都未必想象得到后面將引出多么不得了的效應,更未必有“運動”的自覺。在臺灣對外關系節節敗退的時代,青年有強烈的危機感,也有巨大的使命感。他們未嘗經驗過父母輩叨念的戰亂歲月,擁有比較好的物質條件和閑暇時間,得以探索興趣,甚至將興趣發展成專業。當局高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時代,青年人一方面深受舶來文化的“混血”影響,對西洋與東洋的青年文化深自向往,一方面又體會到臺灣仰“上國”鼻息之可悲,而產生出民族主義的意氣和“尋根”的焦慮。 要理解這樣的糾結,我們可以用一首歌來說說: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 羅大佑的父親是苗栗客家人,母親是臺南人,但他從小在臺北長大。一九八三年,羅大佑發行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A面第二首歌便是《亞細亞的孤兒》: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當年歌詞頁,《亞細亞的孤兒》有一行副標“致中南半島難民”——七○年代越戰結束,許多人從海路出逃,舢舨、漁船擱淺在南中國海的珊瑚礁,餓死渴死者眾,竟還有人相食的慘事。那樣的故事,成了當年國民黨政權對內最好使的“反共教材”。 然而,只要你知道“亞細亞的孤兒”一詞出處,便明白那“致難民”的副標是障眼法。《亞細亞的孤兒》是臺灣作家吳濁流一九四五年完稿的長篇小說:一個叫胡太明的臺灣青年,在家鄉受日本殖民者欺壓,日本留學歸來卻被鄉人排擠,赴大陸又被視為外人,終被逼瘋。羅大佑借用這個意象,開篇四行歌詞,竟仿佛已從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一路走到了國共內戰與島嶼長年的戒嚴。 羅大佑是在當醫師的父親書架上看到了《亞細亞的孤兒》,那一剎那,他腦中響起了副歌吟哦的旋律。羅大佑的父親曾在日治時代被派去南洋當軍醫,一千個臺灣兵只有三百人活著回來。后來國民黨敗退遷臺,政權危殆之際下重手鎮壓異己,開啟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父輩大半生承受不同政權的時代動蕩,“胡太明”的命運非但是不堪回首的集體記憶,也預告了后來苦澀的歷史。 假使不加遮飾,光憑“白色的恐懼”一句,在戒嚴時代,羅大佑很可能從此無法出唱片——那“致難民”的副標,表面迎合了執政者的“主旋律”,暗地卻為所有懂得“解碼”的人,偷渡了一則歷史的大敘述。 這首歌背后的曲折,反映七八十年代臺灣創作人的處境:嚴密的審查制度之下,創作人必須苦心設計“偷渡”路線,埋藏“暗號”,氣味相投的聽眾得設法從字里行間“嗅出”那密碼。當一首這樣的歌透過電波向四方播送,那“啟蒙”的暗號,便可能改變不只一小撮人的生命: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為何哭泣 這是早期羅大佑最好的歌詞,語言直白而不失詩的質地,一洗“民歌”習見的學生腔、文藝腔,正如“民歌”一洗早年流行歌詞的歌廳氣、江湖腔。然而羅大佑在開創中文歌詞新局的同時,亦曾陸續以余光中、鄭愁予、吳晟詩作譜曲,其實承繼了“民歌”時代“以詩入歌”的傳統。那一輩“知識青年”背景的歌人常以“文藝青年”自居,他們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也為這新起的“歌壇”鋪墊了起碼的“文化教養”。 重聽《亞細亞的孤兒》,我們知道:創作人在全新的時代,驟臨無窮的機會與風險,他們幾乎沒有前例可循,仍企圖以“大眾娛樂”為載體,“偷渡”理念,實現理想。禁忌松動,民智漸開,大家對任何新鮮的文化產品都充滿好奇,近乎饑渴,我們還來不及體會后來“信息過剩”引致的飽脹、厭煩與虛無。“流行歌曲”作為“創作門類”的潛能獲得社會共識,“唱片人”亦得以擁有“文化人”的自尊與氣魄。對躍躍欲試的創作者,那是最好的時代。這樣的作品一旦多起來,臺灣流行音樂遂能挾其跨界混搭之雜色,以庶民文化“火車頭”的姿態向整個漢語文化圈輻射,終于成為這片島嶼有史以來影響最深最巨的“文化輸出”。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禁忌不再,《亞細亞的孤兒》那行“致中南半島難民”的副標,也在后來的版本拿下了。但故事并未結束——二○○三年,羅大佑全套作品首度在大陸發行正版,《亞細亞的孤兒》卻從唱片和歌詞內頁消失,只剩一行標題。二十年,一首歌,兩句詞,多少曲折。

胡德夫頂著滿頭白發在草莓音樂節舞臺上邊彈邊唱
演奏中的胡德夫
蘇婭版《美麗島》。騰訊沒有收錄胡德夫版,很可惜。
英年早逝的《美麗島》作曲者李雙澤
胡德夫(前排右一)、李雙澤(后排右一)
李建復 - 歸去來兮 (1980)
侯德健(右)和李建復。“滾石三十年”演唱會上。
包美圣
侯德健
1988年春晚 侯德健《龍的傳人》。侯德健次年因政治原因無緣大陸舞臺二十一年。該視頻似乎無法加載到微信。讀者可在網頁版查看。
臺灣新民歌之父楊弦
老磁帶。侯德健作品集。
羅大佑
漢聲四君子,左起:姚孟嘉、奚淞、黃永松、吳美云
《未來主人公》封面
一九八三年出版《未來的主人翁》內頁,《亞細亞的孤兒》仍有“致中南半島難民”副標題。
羅大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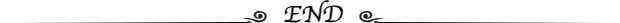
理想國 馬世芳 2015-08-23 08:54:3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