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惠此中國 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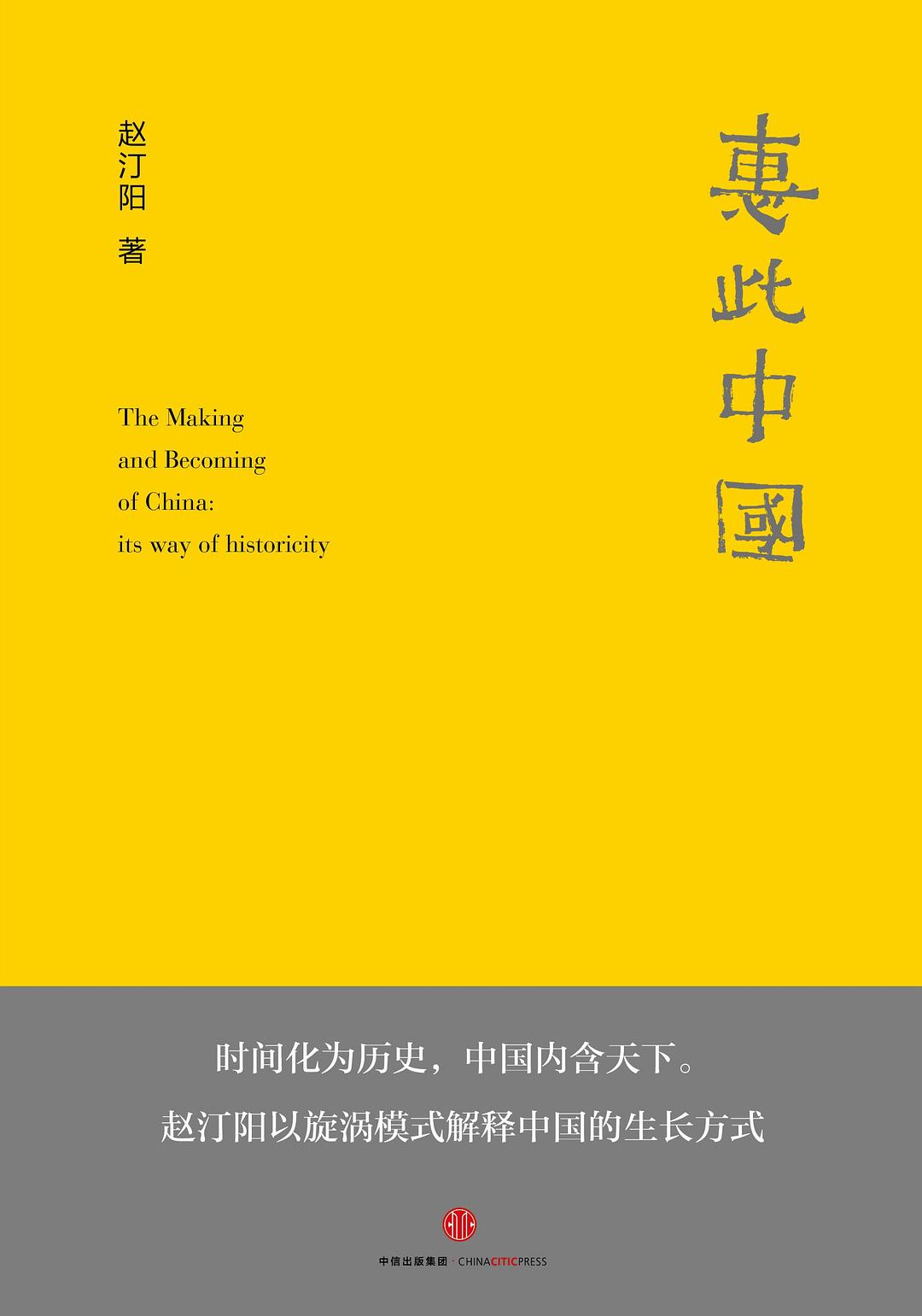
趙汀陽2016年新著,以旋渦模式解釋從商周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的生長方式和游戲規則,解釋為何古代中國并非擴張型帝國卻能不斷擴展。他認為其秘密在于,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擴張行為的紅利,而是來自外圍競爭勢力不斷向心卷入旋渦核心的禮物。
哲學家立足存在論和博弈論,征引大量歷史文獻和歷史研究成果,還原中國起源的“硬歷史”,步步緊追以中原為核心形成“中國旋渦”的四大動力根源:象形書寫文字、龐大成熟的思想系統、周朝創制的天下體系、政治神學的雪球效應。
在大國復興和新技術爆發的時代重新思考中國的起源和精神信仰,這是歷史的遺產,也應是我們對未來的饋贈——用中國思想、中國話語和現代邏輯重建中國之主體性,或曰“神性”。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城學者,國務院特貼專家, 博導。
歐洲國際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常委;
哈佛燕京學社“蒲塞杰出訪問學者”( Pusey Distinguished Fellow,2013);
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授課教授(中國先秦政治哲學,一個學期,2013)。
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哲學、政治哲學。
主要著作:《論可能生活》《天下體系》《壞世界研究》《天下的當代性》。
前言
引言 述史以祭祖
第一章 旋渦模式
第二章 內含天下的中國
第三章 逐鹿游戲與中原的誘惑
第四章 方法與命運
從歷史形態上說,中國是一個分與合的動態過程,盡管分合不斷循環,但作為大一統的“合”始終是其存在的本意或日內在目的。大一統不僅是政治權力的追求,也是萬民和平生息的經濟需要。只要能夠保證萬民安居樂業,大國的資源總量、經濟的多樣性和互補性、人口數量就是巨大的優勢,這是大一統政治實權背后的經濟實利。根據《周易》的存在論原則,“生生”乃一切存在的根本目的,利于萬物萬民“生生”的政治生態就是合理的存在狀態。大一統的信念固然有其吸引力,但終究還需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客觀動力和運作模式,方能化為實在。所以,僅有大一統的信念恐怕仍然不足以解釋中國存在的連續性和凝聚性,其中必定存在某種勢不可擋的客觀動力,這正是需要分析的問題。引自 第一章 旋渦模式
大集團總是存在嚴重的搭便車問題而往往導致集體行動的流產;因此,作為大集團的成功國家必定至少滿足兩個能夠超越搭便車困境的特殊條件:(1)能夠形成普遍共享利益,可能類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選擇性激勵的制度,類似于法家推崇的賞罰分明制度。根據歷史及傳說,在中原興起的核心王朝大都兼備圣王的德治傳統和公正賞罰制度,大概符合奧爾森條件。不過,奧爾森的理論或可解釋成為逐鹿勝利者的必要條件,卻仍然無法用于解釋中原之所以成為逐鹿空間的必然性和持續性:為什么中原會成為人們欲罷不能的逐鹿之地?引自 第一章 旋渦模式
陳進國:內含天下的中國與外延中國的天下——評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
提要: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旨在回答“何以中國”的最核心問題:一是什么是形成中國連續性或歷史性的內在動力結構,二是什么是中國在歷史中被不斷復制的生存基因。但趙氏提出的問鼎中原的旋渦模式也存在著邏輯無法自洽的困境,無法根本性地解釋博弈論中的“公共地悲劇”問題,其對變在中國的解釋也無法有效回應中國連續性文明中關于道統與政統的張力。我們在關注“內含天下的中國”之際,還應重視“外延中國的天下”。“外延中國的天下”,也是地理中國、文化中國、信仰中國得以持續生長,并具有持續歷史性的一種存在方式。
關鍵詞: 惠此中國旋渦模式 遷流模式 公共地悲劇 外延中國
一 前言
毋庸置疑,在當代中國,趙汀陽是最具有原創力的一位著名哲學家。盡管趙氏早年研究的是西方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但他一直致力于“讓哲學講中國話”,以期推動中國漢字世界的范疇的社會科學化,成為國際學術界共同的哲學話語和思考邏輯。繼《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之后,趙氏又推出了《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三本大作其實具有一貫的思想聯系性,有效地呈現了趙氏之述說中國聲音的雄心。而他的政治哲學理論——“天下體系”業已聲震天下,成為重思世界之未來可能性的一塊關鍵的思想磨刀石。作為一位開放的民族主義者和包容的世界主義者,趙汀陽的理論體系充滿著巨大的思想張力,因此也引發了不同的爭議。本文擬對趙汀陽的問題意識、分析路徑,理論的張力及其發展潛力之可能略作討論。
二 中國何以可能的存在論追問
《惠此中國》試圖對中國的歷史性給了一個哲學解釋。作者的問題意識始終扣緊兩個根本性的焦點:一是什么是形成中國連續性或歷史性的內在動力結構,二是什么是中國在歷史中被不斷復制的生存基因。趙汀陽嘗試從存在論的方法去重思中國——我們如果要為中國的歷史性找到歷史解釋的出口,就必須回到哲學上的“存在論的約束”才有可能。存在的本意是“繼續存在”和為了永在。任何一個存在體都必然追求超越歷史性的永在性,才具有歷史存在的意義。而存在論的約束又具體表現為人類行為以理性選擇為主導。任何一種文明的持續的生存能力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種難以解構而自足的“存在的秩序”。而中國之自足的存在秩序,就在于現實的中國同時是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一個歷史。三位一體的中國具有一個足以識別中國為中國的文明起點,具備一些基本精神原則而形成一個走向“大一統模式”的完形之勢。構成中國的精神世界不僅是各方力量共同博弈的精神資源,而且具有開放的共享性。因此,趙汀陽推導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基點——中國是一個內含天下結構的中國。中國成為一個配天的神性概念,謂之“神州”。中國是一個不斷生長甚至無邊生長的概念,即一個不斷趨近天下尺度的中國概念。如果我們站在“民族國家”或者“帝國”之類的概念,來曲解內含天下的中國,就是一種概念的錯位。
近年來,就如何解釋中國,國際漢學界特別是海外史學界,掀起了一種“解構中國”的思潮,其中一個潛在的理論預設就是中國并非一個“大一統”的文明體,而是一個帝國。中國同樣并非具有統一的根基性認同的中國,而是一個近代被建構的“想象的共同體”。有的漢學家甚至將歷史中國的持續生長視為一種“內殖民化”的過程,將中國邊疆的管治視為是一種強勢的漢化的強權。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何以可能”的持續“問題化”和“他者化”,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反思的根本問題。事實上,歷史中國并不僅僅只是表現為一系列所謂的真實史料。任何歷史學家在重塑過去時,總是立足于自我的歷史觀去進行自以為是的研判,當政者更是從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出發進行歷史的剪裁和裁判。
柯文指出,解讀義和團運動至少有“歷史三調”——事件、經歷、神話。“三調”是人們了解歷史的意義、探尋并最終認識歷史真相的不同途徑,也是人們根據不同的原則塑造歷史的不同途徑。“作為事件的義和團代表的是對過去的一種特殊的解讀,而作為神話的義和團代表的是以過去為載體而對現在進行的一種特殊的解讀。兩種路徑都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建立了一種互動關系,在此過程中,現在的人們經常按照自己不斷變化的多樣化的見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重新塑造著過去”。[①]關于中國的“神話化”的話語構建一直持續的存在,并且呈現了多樣化的表現形態。
今天,關于“何以中國”問題的各類“否定性神話”,更是成為一種常態性的主流的歷史話語,甚至是“學術正確”的新史學。所謂的新元史、新清史,都夾雜著太多的“新”的中國想象。這些論述不論是出于學術的真誠還是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都構成當下“一個中國”的現實挑戰,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約定俗成的“中國”論述,更需要中國學者從理論上進行邏輯自洽式的回答,以免陷入一系列的思想陷阱。我們既需要從中國看世界,更需要從世界(包括周邊)看中國。因此,趙汀陽對于中國何以可能的存在論反思,促使我們認真反思自身的歷史認同、身份認同、國族認同,具有相當深刻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自身對中國之持續“存在的秩序”,都難以形成一種在思想邏輯上自洽的解釋,又何以自稱“中國人”,更遑論中國文明?因此,趙汀陽之問,也是針對中國的本體論之問。趙汀陽的道路自信,是中國的生長方式已經鑄成一種長存的方法論。有方法就有青山。
三 問鼎中原的旋渦模式與公共地悲劇
與純粹的哲學思辨不同的是,趙汀陽在提出“何以中國”之存在論理由的發問之后,卻主動回歸到中國之歷史性的結構化解釋。他有效地借鑒了一種重要的思想工具,即經濟學博弈論的理解方式,以輔證和強化他的中國生長模式的哲學解釋。
博弈論的理論預設就是“理性人”,我們只能假定參與博弈的雙方或多方都是理性的存在體,才有進行合作或不合作博弈游戲的現實可能性。而任何一個博弈游戲要追求一個或多個的“納什均衡”,則必須是雙方或多方本著理性的精神原則,來共享一種共有的、有限的并形成彼此共識的資源。唯有如此,博弈游戲才能成為一個“存在的秩序”,并存在多樣性的均衡解決方案。趙汀陽借此提出了歷史中國得以生成的“旋渦模式”。
具體說來,歷史中國有一個政治博弈聚點,即以中原為核心的“天下逐鹿”或“問鼎中原”游戲。而維持這個連續博弈游戲的動力結構,是一個有著強大向心力的旋渦模式:眾多相關者抗不住旋渦的利益誘惑而相續“主動”地加入游戲成為中國的競爭者,博弈旋渦的規模也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一個由開放性的中國渦所定義的廣域中國,創造了中國以及中國的旋渦式的生長方式。而中原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號召力和普遍共享性,在于中原具有四大精神資源可資持續借用:一是以漢字為載體的精神世界發展了早期中國在信息和知識系統的大規模的傳播能力;二以四書五經為載體的思想系統具備了組織大規模社會和創造制度的能力;三是周朝創制的天下體系包含著“配天”“無外”等合法性和兼容性的原則,可以成為普遍接受的政治神學資源;四是“天命傳承”的政治神學的雪球效應。精神資源和政治神學意義的不斷積累,進一步增強了旋渦的向心力效應。
趙汀陽提出“逐鹿中原”或“問鼎中原”的旋渦模式,用來宏觀地解釋歷史中國的持續向心力效應,顯然符合他從“存在論的約束”出發的邏輯自洽原則。然而,如果我們順著趙氏所謂的博弈游戲說開來,“逐鹿中原”其實是一個中國版本的“公共地博弈”,或者通俗地說是“公海捕魚”或“牧地放牧”博弈的問題。博弈學家一直在反復討論如何避免“公共地悲劇”(公共資源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因為它涉及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與公共利益(Common good)對資源分配有所沖突的社會陷阱(Social trap),最早起源于1833年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針對人口壓力與資源利用沖突的比喻。1968年時,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期刊《科學》又將該概念加以延伸,喻示著有限的資源注定因自由取用和不受限制的要求而被過度的剝削,從而最后造成資源的枯絕。個體或利益集團的理性行為最后卻造成了集體的災難性的、非理性的后果。這樣的悲劇情況之所以會發生,源自于個體或利益集團都企求擴大自身可使用的資源,然而資源耗損的代價卻轉嫁所有可使用資源的人們,導致最后可使用資源的群體數目可能遠大于奪取資源的數目。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就從制度設計上分析了如何有效地解決公共地悲劇的博弈論模型。其中維利坦式的借助中央集權的方式、以及純私有化的方式都無法真正解決公共地悲劇,囚徒困境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埃莉諾提出,要解決公共地悲劇的集體行動問題,就必須解決三大問題:一是新制度的供給問題,二是可信承諾的問題,三是相互監督的問題。而諸如清晰界定邊界、占用和供應規則與當地條件保持一致、集體選擇的安排、監督、分級制裁、沖突解決機制、對組織的最低限度的認可、分權制企業等“設計原則”是保證長期有效的公共地資源自主組織、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構件。[②]
埃莉諾等關于解決公共地資源悲劇的制度設計,當然不能直接轉用來解釋歷史中國的“逐鹿中原”博弈游戲,卻足以讓我們反思“逐鹿中原”聚點模式和旋渦效應的解釋合理性及其局限的問題。趙汀陽可能要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逐鹿中原的旋渦效應,盡管客觀上造成了歷史中國的不斷生長,但是否仍然墜入了資源爭奪的歷史性悲劇,因此對于中原的精神資源的破壞也是空前絕后的?歷史中國因逐鹿中原而造成的頻繁的王朝更替,是否就是一種因制度設計失敗而反復造成的公共地悲劇?既然逐鹿中原不免陷入一種公共資源悲劇,那么所謂中原的精神世界又何以維系和共享呢?那么,黃炎培與毛澤東對談所及的“歷史周期律”之拷問,本質上就是政治中國的制度設計之問。某種意義上說,持續性的逐鹿中原的旋渦效應,或許是歷史中國的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的失靈?畢竟,歷朝歷代的不同的政治集團都是站在爭取獲得最大的政治利益(逐鹿/問鼎)的理性立場,來爭搶中原的地緣政治資源或思想資源的。而不斷地改朝換代,或連綿的戰爭沖突,或文化性的族群沖突,或“夷狄入主中原”等等大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根本上也是中原之精神資源爭奪的持續性悲劇。
因此,如果實際的博弈效果是一種公共地悲劇的話,那么逐鹿中原游戲就不是持續的向心力效應,而很可能是長期負面的共享效應。諸如歷史中國的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造成的人口大遷移,唐末黃巢對廣州、長安、陳州的屠殺,蒙元時期對金國境內廣域的中原地帶(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及成都(1279年)的屠殺,明末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滿清入關后的揚州十屠,乃至現代日本入侵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很難說形成了精神資源和政治神學意義的大累積,也很難說逐鹿中原的旋渦向心力正是導致“合”的動力因素。我們現在的普通話或國語,甚至很多也是蒙元或滿清“胡化”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各勢力逐鹿中原的精神資源,并沒有所謂的信任、互惠、尊重等理性選擇的“社會資本”規范,相反各個逐鹿的勢力方都被持續和反復地鎖進一個互不合作的“囚徒困境”,自然很難想象旋渦效應會使“合”成為必然之勢。而囚徒困境博弈是一種對所有對局人都擁有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博弈。不管其他人選擇什么策略,對局人只要選擇“背叛”的支配策略,他的境況就會變得更好。因此均衡的后果其實是“帕累托”較差的悖論。逐鹿或問鼎中原的博弈游戲,就是一個典型的“背叛、背叛”的結局,從而必然出現集體非理性的悲劇后果,形成你死我活式的輪回的改朝換代的血腥格局。當然,三國、魏晉南北朝或兩宋,也形成暫短的形近“合作,合作”的均衡格局。而問鼎中原的聚點模式,其實基本實行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因此,趙汀陽的“旋渦模式”很敏銳地給我們指出中國形成過程中的“問鼎中原”的基本存在樣式,但并未能實質性地解決他所謂的“中國何以可能”的共享精神資源問題,更無法解釋“內含天下結構”的中國在逐鹿中原游戲中何以無法解決囚徒困境和不合作的贏者通吃,反復陷入制度設計失靈的問題。當然,趙汀陽也明確作了自我的設限,即旋渦是個古代中國故事,現代中國早已進入另一種格式的現代博弈。
四 作為“變在”中國的人類學解釋
除了借用博弈論的思想資源外,趙汀陽《惠此中國》也充分活用了中國豐富多彩的考古學資源,以解釋中國旋渦的形成與天下秩序的發明的關聯性,解釋中國文明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問題,或者說中國精神的整體性問題。對于中國,是什么樣的歷史秩序使中國歷史成為萬民的共同歷史?趙汀陽引介了張光直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許宏關于二里頭文化“最早的中國”等等的詮釋,對中國的神學概念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進而將中國的旋渦模式同時解釋為一種精神世界的誘惑和共享,足以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政治魔力。
在論證中國是一個“內含天下結構的國家”時,他反復強調了大一統的中國一直保存著天下的觀念遺產,包括“天下無外”的兼容能力和“天命無私”的概念。而中國作為一個“配天”的神性概念,是與中國的連續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的文明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也因此成為一個神性的存在,成為一個信仰。但趙汀陽反對借儒家的精神傳統來解釋中國的精神世界。孔子所哀嘆的“禮崩樂壞”的格局,更說明禮樂無法構成中國整體精神的根基。他認為中國思想是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并舉,“自然之道”和“天下”就是中國的神性概念,“天下-國-家-國-天下”的雙向循環復制,進一步構成了中國概念的內在神性,使其具有政治神學的意義。內含天下結構的中國不僅是一個復制了天地秩序的自然神學概念,而且是一個復制了天下秩序的政治神學概念。趙汀陽將中國視為配天的神性概念的說辭,并不等于將中國視為一個以超越性――某種絕對的外在性――為基礎的國家,因此,中國的神性概念,自然也是一神教眼中的“異教”。
作為“神性”概念的中國的形成方式,自然是一個“化”字。趙汀陽認為,中國的善化能力與“天下無外”“禮不往教”的原則相關。唯有“天下無外”的原則能夠合理解釋開放的文化基因互化,這也是天下基因在中國概念里的持續功能之一,而中原文化正是互化的主要資源。中原傳統的天命觀和大一統概念正是異族最有利的政治神學敘事。而誰主導互化,關涉誰代表中國正統的敏感問題。因此,中國的概念始終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與共同建構的結果,是一種基因重組的再創造,進入游戲旋渦的地區和族群都是中國的共同創造者。而漢字精神世界最終成為了逐鹿勢力的共同選擇的聚點。
趙汀陽最后又回到他的存在方法論,將中國視為是一個“變在”(becoming)文明,以此反思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的命運。中國正是以變而在,以變而化,以變化的方法論去生存,同時以變化的方法論去建構精神世界。中國精神世界的元規則是方法而不是教義。從變在的方法論去思索中國精神世界的原點,就必須注重“事”而不是“物”。“事”不是一個實體的概念,而是一個關系的范疇。事發于行,因行求道。禮教法度就是有規可循之道(規范,人道),而萬事動態變化之道,乃是形而上之道(天道)。天然是自然而然,是以有變化這樣給定的存在狀態。而人道問題則立足于“生生”,既有扎根也有生長。人道之“事”既然是歷史(古)與未來(今)的結合,使得人的生活世界只有“作”(創造未來)與“述”(書寫歷史)。古與今都是根據“作”而定義的歷史時態。因此,中國“以變而在”的方法基于中國的存在論、方法論和歷史觀三位一體,即道、作、述三者的一貫性,亦即變化、變通、通變的三位一體。而基于變成存在論的歷史觀建立的是一種無限開放而同時無限積累的通變歷史性。“變通”的中國歷史正在是“通變”之中國歷史觀中達到對自身的自覺意識。
趙汀陽關于中國以變而在的存在方法論的證明,與前述論述中國的“旋渦模式”比較而言,顯得相當拗口而難懂,所謂“因作而在”“因述而在”,換一個更加明確的表述,就是讓時間成為歷史。時間只有演化為連續性的歷史,本身才有存在的意義。如果說旋渦模式是一種偏于歷史性的理解,中國作為變在的存在方法論的敘述,則是試圖進一步去解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本體論根基,以及作為我們如何有效去再思中國的認識論基礎。在傳統中國哲學中,討論變化一直有“不易”“簡易”“變易”之三易說,很形象地表述了趙汀陽開篇所謂的存在的本意就是繼續存在,存在的意義是追求永在(tobe is to be for good)。然而,趙汀陽繞口令式的“述”“作”之“事”的敘述,在我看來可以用一個更簡潔的語詞——“成”(becoming)字來統述。所謂“成己成物成事成人”,都在指向所謂的“變在”“通變”“變通”。而作為神性概念的中國之“成”,即作為自然的天道與作為教化的人道的合與化。
按我的理解,趙汀陽所謂的“神性”,并非指一種純粹的超越性的存在,而是指一種帶有泛神論特征的“精神性”,兼容自然與教化之道。按趙汀陽的神性范疇,來自孟子的說法:“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謂神。”因此,中國文明的神性,既然又來自無私的天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那么就是所謂的“道統”,道不變,天亦不變,沒有道統的支撐,爭搶問鼎中原的“正統”也就無所依歸。而要構建正統,其立足的主體的思想之一是“神道設教”,由觀天道而觀天下,由觀天下而化天下。《易。觀》稱:“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孔穎達疏曰:“圣人法則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神道設教是溝通天道與人道的中介,是有形之顯現,既要符合天道之固然(無形之理),又要引導人道之“當然”,以神道來顯現天道的根本目的。而人文化成(禮儀制度)又是以道化俗的途徑。[③]就宗教性的意義而言,“神道設教”是圣人根據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之,從而達到有序的人文教化。天下服“教”的過程,不僅僅是指傳布渠道上的“以道化俗”的“存神過化”教育,還是人格養成上的“位育”,從而實現了“安所遂生”的生命教育。
因此,冒昧地說,趙汀陽僅僅以“變在”來理解中國的存在方式,又使得我們無以追尋所謂構成問鼎中原的旋渦游戲的聚點或奇點。某種意義上說,中原只是一個現實的或想象的地理概念或歷史概念,并不足以構成作為中國之精神信仰引力的聚點或奇點。而中國的神性或者精神性原點,即天道與人道合一的道統原則,才是中國之成為中國的精神聚點。離開了“吾道一以貫之”的道統原則,則何以中國?何以旋渦?何以變在?何以化成?
最后,我們當然還要冒昧地追問,趙汀陽關于中國的變在的存在方法論,亦可能蘊含著一種詮釋學的困境。即與政治中國或歷史中國同質性最強的周邊地區或國家,諸如日本、朝鮮、越南,同樣在歷史上選擇以漢字作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為何卻成為“化外為地”,而不是“無外”?而且這些“小中華”卻自明清以來漸行漸遠?同樣的,明治時期的日本鼓吹“華夷變態”,以為日本乃中國的中心,進而衍生所謂“東亞共榮圈”,并欲圖依照蒙元和滿清,將侵華同樣視為是一種“問鼎中原”的模式。而納入歷史中國和政治中國的中國邊疆,構成其精神世界的依然并非主體的漢字,而是滿、蒙、維吾爾、藏語系。因此,這種政治神學敘事,是否構成旋渦模式的異數呢?我們進而要拷問的是,中國的生長方式真的已經鑄成一種長存的方法論嗎?中國的故事雖然還在繼續,是否也有故事生長的極限?如果中國真是一個可以不斷置換木板的“變在”的“忒修斯之船”,那舊中國與新中國,是否就是兩個中國?中國連續性文明的道統又將何在呢?
五 遷流模式:外延中國的天下?
在敘述完趙汀陽《惠此中國》的主體內容之后,筆者想再接著趙先生的話語邏輯略再進行一點近世中國生長之樣式的歷史性描述。既然“中國是一個內含天下結構的國家,以天下之名而行一國之實。”“天下逐鹿游戲持續不斷地旋渦效應創造了中國,而這個旋渦游戲的開放性――歸功于天下觀念――決定了中國是一個不斷生長的概念。”“作為生長方法而存在的中國具有‘以變而在’的無限性,是以中國能夠像一個‘世界’那樣存在,具有‘世界性’容納能力,能以‘不是而是’的方式生長。” [④]而“現代中國早已進入另一種格式的現代博弈”,那么這種博弈究竟又是什么博弈呢?沒有旋渦效應的公共地博弈,是否仍然會陷入一種博弈的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東南、華南地區的漢人在不斷地移居過程中,廣泛地流傳一首《遷流詩(認祖詩)》:“駿馬登程往異方,任從隨處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鄉。蒼天永庇誠吾愿(蒼天有眼常垂佑),俾我兒孫總熾昌。”[⑤]《隋書.食貨志》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謂之僑人。”在前民族-國家時代,以漢人為主的中國人所遷流和僑居地的范圍,就是整個的地理中國、文化中國所得以“外延”的“天下”,近世的地理中國、文化中國更伴隨著遷流的僑人、僑士得以持續的、墨汁式的生長,從而擴散形成一個以“中國”為名的“文明體”,并有效地構成了中國連續性文明的歷史性。換一句話說,中國人所遷流的僑居地,不只是歷史上天朝體系所管轄的“內含天下的中國”,也涵蓋著近世朝貢貿易體系所輻射的“外延中國的天下”。中國人在歷史中國的域外地區的落地生根,往往是伴隨著原鄉文明傳統包括信仰文化基因的整體遷流。在化異鄉為故鄉的過程中,中國人(僑人、僑士)既實現了“再造原鄉”的飲水思源、認祖歸宗(如血緣宗族和地緣廟宇的異地興建)的文明認同,也完成了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拓殖開化進程。
筆者所謂的“外延中國的天下”,是指伴隨歷史中國的僑人和僑士的人口遷流異鄉,將原(故)鄉的文化、文明傳統一同遷流出去,并在異鄉完成“土著化”和“在地化”的歷史進程。“外延中國的天下”,也是地理中國、文化中國、信仰中國[⑥]得以持續生長,并具有持續歷史性的一種存在方式。如果說政治意義上大一統的“內含天下的中國”是一個“問鼎中原”或“逐鹿中原”的旋渦游戲,那么文化、信仰或拓殖意義上的“外延中國的天下”就是一個“再造中原”的遷流模式。遷流不僅僅是中國人口的遷流,也是中國文化、文明特別是宗教神明信仰、思想觀念體系的遷流,特別是原鄉神明譜系透過僑人(士)的主動的“分靈”和“割香”(存神),而成功地完成了于異鄉異境的在地化(過化),并通過持續不斷的“謁祖進香”“祖山朝圣”,來有效地構建與原鄉、原境的歷史勾連和精神紐帶。因此,遷流模式所形成的僑人(士)的文化中國,也是一個“信仰中國”。文化中國的版圖,也是信仰中國的版圖。僑人所構建的神明信仰譜系,也是一個跨境、跨國的天下信仰譜系。而因僑人(士)的持續的人口遷流模式所開拓歷史主權的土地,在近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中,既有內化為政治中國版圖的“吾境”,也有離散為政治中國之外的“異境”。因此,近世的臺灣、南洋等地區“僑人(士)”所慣性稱呼的“唐山”的歷史意象,不僅僅是一種原鄉中國的文化符號,也是一種中國認同的集體記憶。[⑦]
就此而論,我們分析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的生長,可能還要關注到中國固有的宗教譜系如民間宗教、民間信仰、儒教、道教等等存在的形態,如何作為中國的“綱常”的一部分,如何“化異鄉為故鄉”的“信仰遷流模式”,沒有包括作為中國本土信仰的遷流,也就不存在作為神性概念的中國,和作為精神信仰的中國。從“內含天下的中國”(生成的旋渦模式)和“外延中國的天下”(傳布的遷流模式)的雙重視野來看,近世的中國宗教譜系在地理中國、文化中國之不同地方的生長和存續,又總是伴隨著信仰的陌生人之不斷“遷流”異鄉的歷史進程。僑人、僑士在僑居地進行“開荒引(闡)道”“開荒播種”(道門之說法),隨時隨地構建立起道(教)門的綱常(信仰體系、神道設教),將外境“過化”為吾境,將他鄉“存神”為故鄉,從而形成了一個不斷生長的中國信仰世界。中國宗教譜系在傳布上的遷流模式,也是“存神過化”“開荒播種”的模式。
如果我們以近代的道門或教門等濟度宗教的視野去看,中國宗教譜系在價值觀上具有“早熟而不成熟”的“夾生飯”特征,民族主義和天下主義往往雜糅共生,復歸傳統性與追求現代性,往往相互鏈接、構成矛盾統一體。[⑧]那些早期尚未走出國門的濟度宗教,因為有外來的宗教和反正統的思想的擠壓,而顯得充滿著生存性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如“天時緊急”“救劫”等等說辭),并總是試圖強調自身宗教傳承的“正統性”(道降庶民),以期拯救和存續文化傳統,不免濡染著文化民族主義的復古憂思。因此,濟度宗教其實也是早期的殖民主義和資本全球化變相刺激下的原生性的精神產品。然而,“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⑨],“天下(王者)無外”原則又暗含著“道統無外”“過化無外”的深意。這種根深蒂固的“天下主義”同樣扎根于濟度宗教的思想資源當中,并構成了“斯文同骨肉”的情感認知和道化世界、普度群黎的價值取向。伴隨著華南的華人移民潮以及民族-國家的新政治意識形態的擠壓,內生的“文明化”使命感(萬法歸一、道化世界)和烏托邦情結(蓮花邦、彌勒世界)也催生了濟度宗教大膽地跨出國門,在異鄉的處境中向西方宗教及資本主義學習,因而濟度宗教的“道化”(存神過化)過程又充滿著公開性、開放性和現代性,并以跨境性的宗教結社網絡來參與全球性的文明對話,盡管這種文化回應并不成功,或者尚在拓荒播種的路上(如先天道、道院暨紅卍字會、一貫道)。特別是各種靈媒力量的身體感知,有效地鏈接人與神的直接交流,并借助神啟方式和箭垛式權威,將各種新觀念、新思想也帶進濟度團體進行混合和消融,從而形成了強烈的濟世主義情懷。而通過不斷地吸納了外來文化并加以進行信仰拼盤的濟度宗教,自然也帶著“異端”的精神氣質,并充滿著某些陌生宗教的危險性。然而,這些濟度宗教的傳播,同樣也是在推動文化中國、信仰中國的生長。
因此,趙汀陽提出的“中國何以可能”的問題,時時提醒著我們既要“以中國為中心”,又要“從中國看周邊”和“從周邊看中國”,反思“交錯的中國史”,再思“批評的中國學”。中國問題的拷問,同樣會促使我們克服線性歷史觀,走出傳統的“神話化”的“歷史”陷阱,重新書寫“何以中國”的實態相。當我們跨出中國大陸,以港澳臺地區、以“東亞”“東南亞”作為具有關聯性的文化中國、信仰中國版圖,并且彼此進行“互觀”,我們就會驀然發現,中國及其周邊地區在精神資源上同樣是“互為背景與資源”[⑩]的,并且具有持續性的交流傳統。文化關聯性的斷裂往往發生在中國內部而不是周邊地區。
因此,重思中國的精神世界,也是重思歷史中國,重思中國文明。
[①]參見[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序言”“結論”,林繼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第1-6、289-250頁。
[②]參見[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余遜達、陳旭東譯,上海三聯書店。
[③]盧國龍:《“神道設教”中的人文精神》,載《原道》總第4輯,學林出版社,1997。
[④]參見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中信出版集團,2016,第135-154頁、第205-206頁。
[⑤]福建、廣東一帶的劉氏、黃氏族譜,普遍都有《遷流詩》,語詞略有不同。
[⑥]“信仰中國”是徐以驊提出的概念。“信仰中國”包含了三個緊密相連的“信仰板塊”:中國大陸與港、澳、臺;中國傳統宗教信仰與各種東西方宗教的海外華人信眾群體;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外國信眾群體。第一個“信仰板塊”正好涵蓋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版圖,而第二、三個“信仰板塊”則反映了“信仰中國”的海外版圖,是中國“信仰國境線”的海外延伸。參見徐以驊、鄒磊《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1期。
[⑦]關于“外延中國的天下”和濟度宗教的遷流模式的反思,也得益于趙汀陽“天下體系”的啟發和王琛發關于“中華信仰版圖”的思考。
[⑧]葛兆光指出,晚清民初中國知識思想界相當復雜,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或者傳統性與近代性相互糾纏、相互鏈接。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傳統性的固守,民族主義則經由世界主義來表達。參見氏著《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2011,第192-195頁。
[⑨](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十七《漢紀》十九引荀悅。
[⑩]“互為背景與資源”是借用葛兆光語,參見氏著《互為背景與資源——以近代中日韓佛教史為例》,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文章來源:《江漢論壇》2017年第6期
2023-06-16 14:02:1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