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新的“野火”,從哪里開始,浪漫的理想主義,今何在?
 |
>>> 春秋茶館 - 古典韻味,時事評論,每天清新的思考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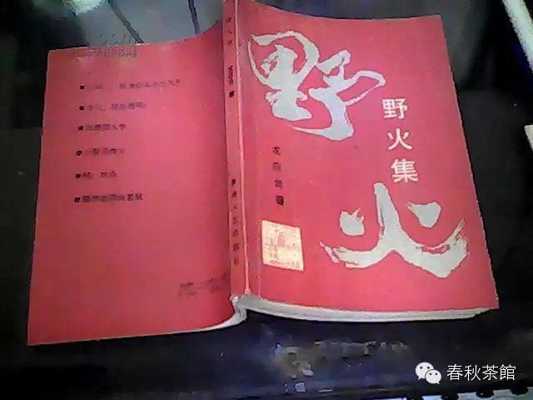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詞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家伙所下的定義,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辟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環保運動的……臺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么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么?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里,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臺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后,臺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斗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里,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里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里,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里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松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圣誕節,不管是掛著什么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臺和燈光的后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于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里,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里,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么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里的流動攤販、洼地里的違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道,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于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么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后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伙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里,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么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里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后幸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煙而被坦克車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么理解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連?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連?)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〇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義,結論是,“很長時間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斗,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斗。”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于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并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尸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于權力,是否猶如尸體之于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斗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斗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于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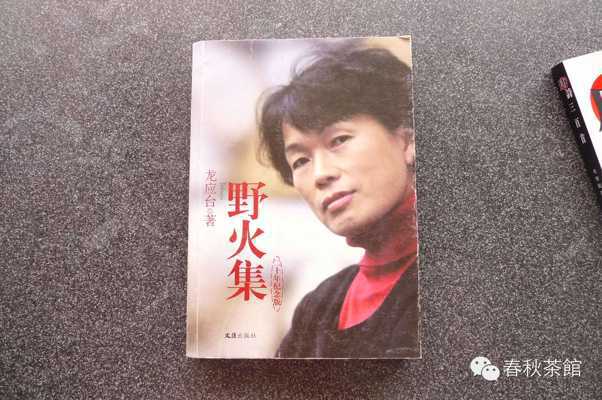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沖破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么,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臺灣的現實里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么辦?)
讀到這里,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么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斗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后,電視由虛假和童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么?人們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里,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后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這么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里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游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閑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里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后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于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于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里抽身而出,獲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里,“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精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鑒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么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里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于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里只有一種面孔呢?對于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詞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家伙所下的定義,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辟的見解,將你推翻。)

龍應臺 2015-05-14 21:37:2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