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看不見的收藏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看不見的收藏 ——德國通貨膨脹時期中的一段插曲 列車過了德累斯頓兩站,一位上了年紀的先生登上了我們這小節車廂,他彬彬有禮地打了招呼,向我頷首致意,再次富有表情地望了我一眼,像是遇見一位故人。乍一看我想不起來,可當他面帶微笑剛一說出他的名字時,我馬上就想起來了:他是柏林最有聲望的藝術古玩商人之一,和平時期我經常在他那里瀏覽和購買舊書以及作家手稿。我們先是隨便地聊了一會兒,突然間他徑直說道: “我得告訴您,我這是從哪來的。作為一個藝術商人,這是我三十七年來遇見的一樁奇怪之極的插曲。您大概知道,自從貨幣的價值像空氣一樣地不值錢,現在我們這一行的行情是什么樣子:一批暴發戶驟然間都對哥特式的圣母像、古版書以及古老的銅版雕刻畫和古畫感興趣了。根本就無法滿足他們的奢望,您甚至不得不防范他們把你的整個家底搜凈刮光呢。他們恨不能把衣袖上的紐扣和寫字臺上的桌燈都買了去。于是收進新的貨物就越來越困難了——請您原諒,我突然把這些東西說成是貨物,往常這可是令我們感到多少有些敬畏的呢——可是這群壞家伙就是習慣于把一本杰出的威尼斯古版書看做一大堆美元,把一張古爾希諾(意大利畫家喬萬尼· 弗蘭西斯科· 巴比埃利· 達· 秦托(1590—1666)的綽號。)的素描當成幾張一百法郎鈔票的化身。這股突然涌來的搶購浪潮,其勢頭銳不可當。于是隔夜之間我就被搜刮得一干二凈。我真想把店門一關了事。在我們這樣一家老字號里——這還是我父親從我祖父手里接過來的——竟然只有一些可憐巴巴的劣等貨色,過去,在北方這都是些連走街串巷的小販也不愿放到車上的東西,我為此羞愧至極。 “在這種狼狽的境地里,我想出了個主意,去翻閱我們的老賬本,搜索一下我們的老顧客,或許可能從他們手中重新買回幾件復制品,這樣一本陳舊的顧客名單一直都是某種類型的墳墓,特別是在眼下這年代,它對我的用處根本不大。我們早先的那些買主大多數不是早就把他們的收藏送進了拍賣行,就是已不在人世了,對極個別的人也不能抱什么希望。突然間翻出我們的一個老顧客的一整捆來信,我一下子就想起他來,因為從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以來,他就再也沒有寫信向我們訂過貨和詢問過情況了。這些信件大約都是六十年代(指19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這絕不是夸張!他從我祖父和父親手里買過東西,可我記不起來,在我經營的三十七年中他進過我們的商店。一切都表明,他一定是一個古怪的、老式的、滑稽可笑的人。這樣的德國人已經變得罕見了,只有在偏遠的小鎮里還有個把這樣的人一直活到我們的時代。他寫的字都是一種書法藝術,寫得十分工整,錢數總額都用尺和紅筆畫上直道,而在數字下面都是再畫上一道,以免出錯。這一點以及他所用的簡陋的信封和很不起眼的信紙都說明了這個無可救藥的外省人的瑣細和吝嗇。落款處除了簽上他的名字之外,他還經常帶上一大串繁瑣的頭銜:退休的林務官,農業學家,退休上尉,一級鐵十字獎章獲得者。這個七十年代的老兵,要是還活著的話,那至少年過八十了。但是,這個滑稽可笑的節儉人,作為一個古老的繪畫藝術的收藏家卻表現出一種非凡的聰穎、杰出的知識和出色的鑒賞力。我慢慢地整理他大約六十年之內的訂單——最早的一批訂貨還只是幾枚銀幣的事情——這時我發現,這個卑微的外省人在當時人們用一個塔勒(德國舊時的一種銀幣。)可以買一大堆精美的德國木刻畫的年代里,不聲不響地搜集到一批銅版雕刻畫,這筆收藏與那些暴發戶借以炫耀自己的東西相比,毫不遜色。在半個世紀里,光是他在我們這里僅用極少馬克和芬尼成交的,今天的價值就會令人咋舌,除此,可以想象得出,他定也從拍賣行和其他商人手中弄到不少名貴的東西呢。從一九一四年起我們再也沒有從他那里收到過訂單了,但我對藝術商界里的事情十分熟悉,這樣一批收藏如果進行拍賣或者私下里出售那是瞞不過我的。因此,這個古怪的人現在一定還活著,要不這批收藏就在他的繼承人手里。 “這件事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我在第二天,即昨天晚上立刻動身,直奔薩克森的一座十分破舊的小鎮。當我從簡陋的車站穿越城鎮的那條主要街道時,我簡直不能相信,在這些平庸的、市民氣的簡陋房屋里,其中某間陋室竟住著一個擁有倫勃朗的最杰出的繪畫、丟勒和蒙臺納的木刻人像的人。使我驚訝的是我在郵局詢問這里是否住有叫這個名字的林務官和農業學家時,得知這位老先生確實還健在,于是我就在上午前去拜訪,應當承認,我的心當時跳個不停呢。 “我沒費什么力氣就找到了他的住處。他住在那種租費低廉的、土里土氣的樓房里,這種建筑物都是在六十年代草率匆忙修建起來的,他住在三樓,二樓住著一位老實的裁縫,在三樓的左邊掛著一位郵政局長的牌子,閃閃發光;而在右邊掛著一個小型的琺瑯牌子,上面有林務官和農業學家的字樣。我膽怯地拉動了門鈴,隨即出來了一個年邁的白發女人,她頭戴一頂整潔的黑色小帽。我把我的名片遞給了她,問是否可以同林務官先生面談。她感到驚訝,先是懷有某種疑惑似的打量我,隨即看了看我的名片。在這遠離世界的小鎮里,在這老式的房子里,出現了一個從外地來的客人,這可是一件大事。但是她和氣地請我稍候,拿著名片,走進房間,我聽到她輕輕地說話,隨即突然響起了一個男人的洪亮的聲音:‘啊,R先生,柏林來的,一家大古玩店的老板……請進來,請進來……我太高興了!’那個老婦人快步重新走了出來,把我讓進屋內。 “我脫掉大衣,進了房間。在簡樸的房間正中,筆直地站著一個健壯的老人,濃髭密髯,身上穿著一件半軍用的便服,親切地向我伸出雙手。但他站在那里的這種奇怪的、僵直的姿態與他那外表上不容置疑的高興非凡和喜出望外的歡迎姿態毫無共同之處。他一步也不朝我走來,我感到一絲愕然,只得走到他跟前,以便和他握手。可當我正要握他的手時,我發現他的那雙手仍一動不動保持著水平姿勢,不是來握我的手,而是在那兒等我去握。隨即我全明白了,這個人是個盲人。 “早從孩提時代起,在一個盲人面前,我總是覺得不舒服;我明知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可同時又知道,他不能像我看到他那樣看到我,這總免不了使我感到某種羞赧和窘迫。當我現在看到白色濃眉下的一雙業已死亡了的、僵直的、空無所視的眼睛時,我不得不克制我的愕然。但是這個盲人卻不讓我有更多時間發怔,我剛一握住他的手,他就使勁地搖動起來,急促地、高興得粗聲粗氣地再度表示歡迎。‘稀客啊,’他滿臉堆笑地對我說,‘這真是奇跡呀,柏林的一位大老板竟然光臨寒舍……可一當某個生意人上路,那就要當心啊……在我們這里,人們常說:要是吉卜賽人來了,那就要緊鎖房門,看好錢包……是的,我想得出您為什么來找我……眼下,在我們這個可憐的、走下坡路的德國,生意不好做啊。沒有買主了,于是大老板們就又想起了他們的舊主顧,尋找他們走失了的羔羊……但在我這里,恐怕您交不上運氣啦,我們這些窮苦人,靠養老金過活的老人,飯桌上有塊面包,就夠高興的了。你們現在要的令人發瘋的價格,我們再也付不起了……我們這樣的人永遠也沒有份了。’ “我立即解釋說,他誤解了我的來意。我來這兒不是向他出售什么,我只是偶爾來到這一帶,有了機會,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來拜訪我們的一位多年的老主顧和德國最大的收藏家之一,我剛一說完‘最大的收藏家之一’這句話,這老人的臉上便起了一種奇怪的變化。雖說他還是筆直地、僵硬地站在房子中央,可是現在他的態度突然顯出歡快明亮和洋洋得意的神情。他把身子轉向估計是他妻子的方向,說道:‘你聽聽。’聲音里充滿了快樂,沒有一絲那種在軍隊里養成的粗魯語氣,而是和氣地甚至是溫柔地對我說:‘您這真是太好、太好了……您確是不虛此行啊。您可以看到您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的東西,即使是在你們豪華的柏林……有幾幅畫,在阿爾帕梯納(阿爾柏梯納:維也納著名的藝術陳列館。),在該死的巴黎都找不出比它們更美的了……真的,收藏了六十年,什么樣的東西能沒有啊,這可不是在馬路上隨便看得到的。露易絲,把柜子的鑰匙給我!’ “這時候卻發生了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個一直站在他身邊、面帶微笑客氣地靜聽我們談話的老婦人,突然向我懇求地舉起雙手,與此同時猛烈地搖頭表示不同意,這個暗示一開頭我沒有理解。這時她走到丈夫跟前,把兩只手放到他的雙肩上。‘海瓦特,’她提醒說,‘你還根本沒問這位先生現在是不是有時間來看你的收藏呢,現在已經中午了。而飯后你得體息一個鐘頭,這是醫生明確囑咐了的。飯后你讓這位先生看你的東西,然后我們一同喝杯咖啡,不是更好嗎?那時安娜瑪麗也在這兒了,她對這些東西很熟悉,可以幫你的忙!’ “這番話她剛一說完,就立即再次背著什么也察覺不到的老人重復那種迫切乞求的手勢。我現在懂得了她的意思。我知道,她希望我現在拒絕觀看他的收藏,我很快找到一個遁詞,說中午有一個約會。如果能夠欣賞他的收藏,我當然感到高興和光榮,但是在三點鐘之前幾乎不可能了,在此之后我十分愿意。 “他像一個孩子被人奪去了心愛的玩具那樣惱火起來,老人轉過身來。‘當然,’他嘟囔說,‘柏林的先生們從來都沒有時間的,可這次您一定得花點時間的,這可不是三五幅畫,這是整整二十七本畫冊,每本是一個大師的作品,而且沒有一本里是有空頁的。那就說好三點;可要準時,否則我們是看不完的。’ “他又空無所視地把手伸給我。‘您注意,您會高興——或者惱火。而您越是惱火,我就越是高興。我們收藏家一向就是這樣:一切都弄來給自己,而沒有我們給別人的!’他再次有力地搖動我的手。 “老婦人陪我出門。整個時間里我已覺察到她悶悶不樂、畏葸不安和不知所措的表情。剛一走出門口,她完全壓低了聲音、結結巴巴地對我說:‘在您來我們這里之前,是否請您允許……請您允許……我的女兒安娜瑪麗去領您前來?……這更好些……更妥當些……您大概是在旅館用飯吧?’ “‘當然,我為此感到非常高興,樂于從命。’我說。“真的,就在一個小時之后,我在市集廣場旁邊旅館的小飯堂里剛吃完中飯,就走進來一個老氣的姑娘,她衣著簡樸,用目光在搜尋。我向她走去,介紹我自己,說明我已準備停當,可以立即動身去欣賞她父親的收藏。可她突然臉紅了起來,像她母親一樣慌亂窘迫,她問我在去之前可否同我談幾句話。我立刻看出來她很為難。每當她要開口說話時,總是十分差赧,面泛紅暈,不安地用手撫弄衣服。最后她總算開始說了,結結巴巴,并且老是一再地慌亂無措: “‘母親叫我到您這兒來……她把一切都講給我聽了……我們對您有一個請求……在您去我父親那兒之前,我們是想告訴您,我父親當然想把他的收藏拿給您看……可是這批收藏……這批收藏……不再是完整無缺的了……其中少了一些……不幸的是,甚至可以說少了很多……’ “她不得不又停下來喘口氣,隨即突然望著我,匆忙地說下去: “‘我必須完全坦率地對您講……您清楚眼下的時代,您會了解這一切的……戰爭爆發后父親的雙目就完全失明了。早在這之前他的眼睛就經常犯病,而由于激動終于完全失明——戰爭開始那年,他雖然已七十六歲了,可還是要到法國去打仗,當軍隊沒有像一八七○年那樣長驅直入,他就可怕地激動起來,于是他的視力就急劇減退,要沒有這場變故,他一直還完全是健壯的,在這之前不久他還能整小時走動,甚至外出打獵,這是他最喜愛的一種運動。可現在他不能出外散步,他剩下的唯一樂趣就是這批收藏,每天他都得看上一遍……說實在的,他根本不是在看,他根本也看不見了,但他每天下午把畫冊都拿出來,為的是至少可以用手去摸摸它們,一張接著一張,總是按著固定的次序,這是數十年來他熟記好了的……今天沒有什么再引起他的興致了,我總是給他念報紙上的拍賣價格,他聽到價格越高,就越是高興……可是……可這太可怕了,我父親對物價、對時代是一竅不通啊……他不知道我們失去了一切,他不知道他一個月的養老金只夠兩天的生活用……此外還得加上我妹妹和她的四個孩子,她的丈夫戰死了……可我父親對我們經濟上的困難一無所知。開頭我們節儉地過,省吃儉用,可這無濟于事。于是我們開始賣東西——我們當時不動他心愛的收藏——賣我們有的零星首飾,可是,我的上帝,六十年來我父親把他省下來的每個芬尼都用在買畫上了,我們能有什么值錢的東西呢。山窮水盡,我們不知該怎么辦……于是,于是母親和我賣了一張畫。父親要知道的話,是不會允許的,他不知道境況多么壞,他想象不出在黑市里買一口吃的是多么困難,他也不知道我們被打敗了,阿爾薩斯和洛林被割讓出去了,我們不再給他念報紙上這一類的事情,免得他激動起來。 “‘我們賣了一幅非常珍貴的畫,那是倫勃朗的一張銅版蝕刻畫。買主給了我們好幾千馬克,我們希望用這筆錢能過上一年。可是您知道,這錢也太不值錢了……我們把余款存放在銀行里,可是兩個月后就變得一文不值了。這樣我們只得又賣一張,接著再賣一張,而買主匯來的錢老是很遲,等錢到手又不值錢了。隨后我們去拍賣行,可在那兒他們也欺騙我們,出的價格是上百萬……可是等這幾百萬馬克到我們手就又變成一堆廢紙。慢慢地就這樣把他那批收藏中的最珍貴的賣得一張不剩,用來維持起碼的、最可憐不過的生活,而我父親對此一無所知。 “‘因此,當您今天前來,我母親十分驚慌……要是他給您打開他的畫冊,那一切就隱瞞不住了……我們把復制品或類似的畫塞到畫冊里的舊框里去代替我們賣出的畫,這樣,他撫摸的時候就不會發覺。當他撫摸和數這些畫(每一張的次序他記得非常清楚)的時候,那種喜悅勁和他過去眼睛能看得見的時候一樣。在這座小城鎮里,父親認為,沒有一個人配看他的寶貝……他懷有一種狂熱愛著每一張畫,我相信,要是他知道了他手里的這批畫都早已無影無蹤的話,那他會心碎的。這么多年來,您是第一個他要把他的畫冊給您看的人。為此我請求您……’ “突然這個女人舉起雙手,眼睛含著淚水,閃閃發光。 “‘……我們懇求您……您不要使他不幸……您不要使我們不幸……您不要毀掉他這最后的幻想,請您幫助我們,使他相信他要對您講述的這些畫都還在……要是他猜出了都是假的,那他肯定會死去的。或許我們這樣對待他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人總得活下去……人的生命,我妹妹的四個孤兒,這總比畫要重要啊……直到今天我們確也沒有剝奪掉他的快樂;每天下午有三個鐘點他翻閱他的畫冊,同每張畫說話,像同一個活人一樣。而今天……今天也許是他最幸福的日子,多年以來,他一直等待這么一天,好向一個行家展示他這些心愛之物;我請求您……用舉起的雙手懇求您,不要毀掉他的幸福!’ “她說的這一切是那樣感人,我的復述根本無法表達出萬一。我的上帝,作為一個生意人,我看到過許多人被無恥地掠奪得一干二凈,被通貨膨脹弄得傾家蕩產,他們寶貴的家私為了換口奶油面包而被騙去。但是這兒,命運創造了另外一番奇特的情景,它使我極為感動。不言而喻,我答應她一定保守秘密,并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們一道前往。在半路上我又憤慨地得知,別人用區區小數的錢欺騙了這兩個窮苦的、無知的女人,這更堅定了我去幫助她們的決心。我們上了樓,還沒等我們拉門鈴,我就聽見從房間里面傳出來老人高興的叫喊聲:‘進來!進來!’盲人的靈敏聽覺使他在我剛一上樓時就聽到了我們的腳步聲。 “‘海瓦特今天等著您看他的寶貝,急得連覺都沒睡著。’老婦人微笑著說。她女兒的一個眼色就使她安下心來,知道已經取得了我的同意。在桌面上早就擺滿了畫冊,這位雙目失明的老人剛一握到我的手,來不及說其他的歡迎詞兒,就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扶手椅上。 “‘好了,現在我們馬上開始——有好多東西要看呢,從柏林來的先生們沒有時間哪。第一本畫冊是丟勒大師的,您可以看得出來,是相當完整的,一張比一張好,喏,這您自己能判斷出來的,您看這一張!’他翻開畫冊的第一張,‘這是《大馬》。’ “于是他十分謹慎地,就像是接觸一件易碎的物件似的,用指尖小心翼翼地從畫冊的紙框里取下一張上面什么也沒有的、發黃的紙張,興高采烈地把這張廢紙頭擺在自己的面前。他看著它,有好幾分鐘,實際上他什么也看不見,但他興奮地用手把這張白紙舉到眼前,臉上奇妙地呈現出一個明目人那樣的聚精會神的表情。在他那雙瞳仁業已僵死的眼睛里霎時間閃出一種明鏡般的光亮,一種智慧的光華。這是由于紙張的反射還是內心光輝的映照? “‘喏,您什么時候看到過這樣一張極為漂亮的畫呢?’他驕傲地說,‘每一個細部都多么清晰,多么細膩——我把這一張同德累斯頓的那一張作過比較,比起來那一張顯得呆板,毫無生氣。這兒還有收藏家的一些落款!’說著他把這張紙翻了過來,用指甲準確地指著這張白紙背面的一個地方,這使我不由自主地看過去,看那兒是否真的有什么標記。‘這是拿格勒收藏的圖章,這兒是雪米和艾斯達依勒的圖章;他們,這些著名的收藏家絕不會想到,他們的畫有一天竟落到了這間陋室里。’ “當這個一無所知的盲人那樣贊賞一張廢紙時,我脊背上不禁感到一陣發冷;看到他用指甲尖一絲不茍地指著那些只存在于他幻想中而實際上看不到的收藏者的標志,真使人難過。我覺得嗓子眼發堵,不知回答什么好;但當我不知所措地向兩個女人望去時,看到了那個顫抖的、激動的老婦人乞求地舉起雙手,于是我鎮定下來,開始扮演我的角色。 “‘真是罕見!’我終于訥訥說道,‘一張美極了的畫。’他的臉立刻由于驕矜而泛出光澤。‘這遠不算什么,’他得意地說,‘您得先看看那張《憂郁》或者《基督受難》,一張著色的珍品,這樣的質量再找不出第二份來,您看看吧。’他的手指又輕輕地在一張他想象中的畫上比畫著。‘多么鮮艷,色調多么細膩,多么溫暖。柏林的古玩商和博物館的專家們都會目瞪口呆的。’ “這種狂喜入迷的、喋喋不休的贊賞足足有兩個鐘頭。不,我無法向您描述,看到這一二百張白紙或粗劣的復制品是多么令人難過,但這些白紙和復制品在這個悲慘的、一無所知的盲人的記憶里卻是那么真實,他能絲毫不爽地順著次序贊美著、描繪著每一個細部,十分精確;這看不見的收藏,雖說早已失散得一干二凈,可對于這個盲人,對于這個令人感動的、受騙的老人,卻依然是完整無缺啊,他幻覺中的激情是那樣強烈,幾乎使我都開始相信他的幻覺是真實的了。只是有一次他幾乎從這種夜游式的狀態中被驚醒過來:在他夸獎倫勃朗的《阿齊奧帕》(這一定是一幅珍貴無比的樣本)印得多么精致時,同時就用他那神經質的有視覺的手指,順著印路在描畫著,可他那敏感的觸覺神經在這張白紙上卻感受不到那種紋路。剎那間他的額頭籠罩上一層黑影,聲音慌亂起來。‘這真的……真的是《阿齊奧帕》?’他嘀咕起來,顯得有些困惑。于是我靈機一動,馬上從他手里把這張紙拿了過來,并興致勃勃地對這幅我也熟悉的銅板蝕刻畫中每一個細節加以描述。盲目老人業已變得困惑的面孔又恢復了常態。我越是贊賞,這個身材魁梧然而老態龍鐘的盲人便越是心花怒放,一種寬厚的慈祥,一種憨直的喜悅。‘這才真是一個行家,’他歡叫起來,得意地把身子轉向家人,‘終于有一個懂行的人了,你們也會知道,我的畫是多么寶貴了。你們總是懷疑我,責備我把錢都花在我的收藏上,是啊,六十年來,我不喝啤酒,什么酒也不喝,不吸煙,不外出旅行,不上劇場,不買書,我節衣縮食,省吃儉用,就是為了這些畫。你們會看到的,等我離開人世時,那你們就會有錢,比這個城鎮的任何人都有錢,和德累斯頓最有錢的人一樣富有,那時你們就會對我的這股傻勁再次感到高興呢。但是只要我還活著,哪一幅畫也不許離開我的家。得先把我抬去埋掉,才能動我的收藏。’ “他的手溫柔地撫摸著早已空空如也的畫冊,像撫摸一個活物似的。這使我感到驚悸,但同時也深受感動,在戰爭的年代里我還從沒有在一個德國人的臉上看到這樣完美、這樣純真的幸福表情,站在他身邊的是他的妻女,她們與德國大師的那幅蝕刻畫上的女性形象那樣神奇地相似,她們來到這兒是為了瞻仰她們的救世主的墳墓,站在被挖掘一空的墓穴之前,她們面帶一種驚駭至極的表情,而同時又懷有一種虔誠的、奇妙的狂喜。像那幅畫上的女人在聽耶穌基督的上天預言那樣,這兩個上了年紀的、面容憔悴的、窮苦的小資產階級女人被老人的孩子般的喜悅所感染,半是歡笑,半是淚水,這種景象我從未經歷過,它是那樣動人。但是老人覺得我的贊賞仍嫌不夠似的,他一直不斷地翻動畫冊,如饑似渴地吞飲下我的每一句話。當這些騙人的畫冊終于被推到一旁,他不情愿地把桌子騰出來供喝咖啡用時,這對我來說如釋重負。但我的這種輕松之感,卻是針對他那極度興奮、極為狂亂的快樂的,針對這像是年輕了三十歲的老人的自豪而言的,這使我感到內疚。他講了許許多多他搜集這些畫的趣聞;他拒絕他人的幫忙,不斷地站起身來,一再地抽出一幅又一幅的畫來,宛如喝醉了酒那樣不能自主。最后,當我告訴他我得告辭時,他驀地一怔,像一個固執的孩子那樣滿心不悅,氣得直跺腳。這不行,我還一半都沒看完呢。兩個女人極力使這執拗的老人理解,他不應該再挽留我了,要不我就要誤火車了。 “經過無望的挽留,他最后聽從了勸告;在告別的時候,他的聲音變得完全溫和了。他抓住我的雙手,面帶一個盲人所能表現出來的全部感情,用手指愛撫地一直摸到手腕,像是要更多地了解我,或者是要給予我遠非言辭所能表達出的、更多的愛。‘您的訪問使我高興極了,高興極了,’他開始激動地說,這激動出自他內心深處,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您對我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我終于,終于,終于能同一個行家一道欣賞我這些心愛的畫冊。您會看到,您到一個老瞎子這兒來,并沒有白來一趟。這兒,在我的妻子面前,她可以作證,我答應,在我的遺囑上再加上一個條款,把我的這批收藏委托給您這家老字號負責拍賣。您應該有這份榮譽,支配這批不被人知曉的寶貝,’說到這里他把手輕輕地放在已被洗劫一空的畫冊上面,‘直到它們流散在世上的那一天為止。但您要答應我,印一份精美的目錄:這將是我的墓碑,我不需要其他更好的了。’ “我向他的妻子和女兒望去,她倆聚靠在一起,戰栗不時從一個人傳向另一個人,仿佛她倆成為一體,協調一致地在抖動。可我有著一種莊重的情感,因為這個令人感動的、一無所知的盲人把他那看不見的、早已無影無蹤的收藏當做一批珍貴的財富委托給我支配。我激動地應允了他,可是這允諾是永遠不會兌現的。在他那對業已死亡的瞳仁中重又泛出光輝。我覺察到,他有著一種出自心底的渴望,要和我親近;我感到他的手指是那么溫柔、那么親切地緊握住我的手指,滿懷著感激和莊嚴的情感。“兩個女人陪我向門口走去。她倆不敢講話,因為怕他靈敏的聽覺會聽到每一個字;她們望著我,兩眼飽含熱淚,目光里充滿了感激之情。我迷迷瞪瞪地摸著下了樓梯。我真應該感到羞愧,看起來我像一個天使降臨到一個窮人之家,由于我參與了一場虔誠的騙局并進行了善意的欺騙,從而使一個盲人復明了一個小時,我實際上卻是一個卑劣的商販,來到這里是想從別人手中搞去一兩張珍貴的作品。但我從這里帶走的遠比這要珍貴得多:在這個陰郁的、沒有歡樂的時代里,我又一次活生生地感受到了純真的熱情,一種照透靈魂、完全傾注于藝術的狂熱,而這種狂熱我們的人早就沒有了。我懷有一種敬畏的感情——我不能說出別的什么來——盡管我還一直有著一種我說不出為什么的羞愧之情。 “我已走到了街上,上面的窗戶咯吱地響動起來,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真的,老人用盲無所見的眼睛在望著估計是我走去的方向,他連這個機會都不放過。他把身子從窗戶里探出很遠,兩個女人不得不費心地扶住他。他揮動手帕,用孩子似的歡快聲音喊道:‘一路平安!’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景象:窗口上面白發老人的一張快樂的面孔,高高地漂浮在馬路上愁容滿面、熙來攘往、行色匆忙的眾生之上,乘著一朵幻覺的白云冉冉上升,離開了我們這個令人厭惡的世界。我不由得憶起了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我想那是歌德說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高中甫 譯 選自新陸文庫·德語卷·《茨威格中短篇小說經典》[奧地利]茨威格 著 高中甫 等譯 本書選錄了茨威格中短篇小說十一篇,這些不同風格的作品代表了茨威格不同時期的藝術成就。茨威格以細膩的筆調展現了人物復雜幽暗的內心世界,凸顯了情欲力量和無意識驅動力對人物的影響。《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寫了一個女人自十三歲就對一個登徒子一往情深、癡心不改;《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寫了一個出身名門的富有孀婦,竟對一個年輕賭徒神魂顛倒,以身相許,竟至預備與他私奔;《情感的迷惘》則寫了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由于受同性戀情欲的牽引,出沒于骯臟下流的齷齪場所,欲罷不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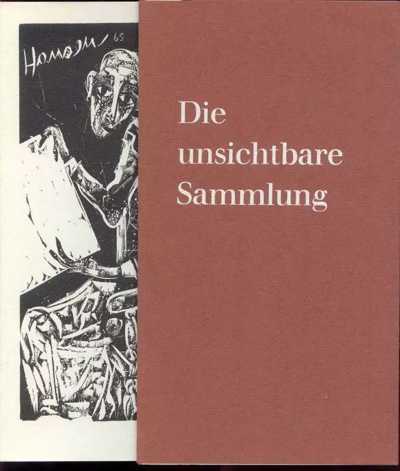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0: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