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你是否也患上了"耶路撒冷綜合征"? 薦書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耶路撒冷三千年》 [英]西蒙•蒙蒂菲奧里/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11 耶路撒冷曾被視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沖突的戰略要沖,是讓世人魂牽夢繞的去處,是惑人的陰謀與虛構的網絡傳說和二十四小時新聞發生的地方。西蒙•蒙蒂菲奧里依年代順序,以三大宗教圍繞“圣城”的角逐,以幾大家族的興衰更迭為主線,生動講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以客觀、中立的角度,透過士兵與先知、詩人與國王、農民與音樂家的生活,以及創造耶路撒冷的家族來呈現這座城市的三千年瑰麗歷史,還原真實的耶路撒冷…… 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生于1965年,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歷史。他是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研究員,耶路撒冷舊城外第一座猶太住宅區的建造者摩西•蒙蒂菲奧里爵士的曾孫,紀錄片《耶路撒冷:一座圣城的誕生》主持人。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五 種語言,暢銷多個國家,曾獲得英國科斯塔傳記獎、美國《洛杉磯時報》傳記圖書獎、法國政治傳記大獎,以及奧地利克萊斯基政治文學獎等眾多大獎。 死亡是我們的永恒伴侶。長久以來,朝圣者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圍,以為末日來臨時的復活作準備而前往耶路撒冷,他們還在繼續前來。這座城市被墓地包圍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軀體備受尊崇——抹大拉的瑪利亞干癟發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臘正教修會會長的房間里供奉著。許多圣跡,甚至許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墳墓周圍。這座死人之城的陰森不僅源自戀尸癖,而且還與招魂術有關: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們只是在那里等待復活。對這里無休止的爭奪——屠殺、蓄意破壞、戰爭、恐怖主義、圍攻和災難將耶路撒冷變成了戰場——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話說,是“宗教的屠宰場”;用福樓拜的話說,是一個“停尸房”。梅爾維爾稱這個城市是一個被“死亡大軍”包圍的“頭蓋骨”;而愛德華·賽義德記得自己的父親討厭耶路撒冷,因為它“使他想起死亡”。 這個天與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發展起來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展示的靈光。帝國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個軍閥的活力和運氣。從大衛王開始,某些個人的決定使得耶路撒冷成為“耶路撒冷”。 誰也沒有想到大衛的小小城堡,一個弱小王國的首都竟然會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對耶路撒冷的毀滅造就了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場災難促使猶太人記錄并贊頌錫安的榮耀。通常來說,這樣的大災難會導致一個民族的消亡,然而猶太人生機勃勃,對自己的上帝忠貞不渝,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在《圣經》中將自己的歷史記載了下來,這些都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聲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經》取代了猶太國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說的那樣,成為“猶太人隨身攜帶的祖國,隨身攜帶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沒有任何城市擁有自己的圣書,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經》一樣如此主導一座城市的命運。 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猶太人作為特選子民的“例外論”,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選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選的土地,后來這種例外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繼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從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到20世紀70年代宗教領域不斷增長的對猶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癡迷,以及西方世界對它的世俗對應物猶太復國主義的狂熱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劇故事改變了人們對以色列的認知,對于這些人來說,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執迷戀,還有這種普遍的歸屬感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說是把雙刃劍。今天,這種情況反映在對耶路撒冷更加強烈、更富感情的審視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沖突上,其中的緊張程度與情感糾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可比擬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來的那么簡單。歷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變化與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連續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著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這里的人們不符合各大宗教傳說和后來的民族主義敘述的狹隘分類。這是我盡可能地以家族發展為線索追尋歷史的原因——大衛家族、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瑪亞家族、鮑德溫和薩拉丁家族,直到侯賽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蒙蒂菲奧里家族——這種做法有悖于正統史學所注重的突發事件描述和狹隘敘事,但卻可以展示有機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僅有相對的兩方,還有許多相互連結、相互重疊的文化和不同層次的忠誠——它是一個由阿拉伯正統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爾迪猶太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哈雷迪猶太人、世俗猶太人、亞美尼亞東正教徒、格魯吉亞人、塞爾維亞人、俄國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亞人、拉丁人等等組成的多姿多彩、千變萬化的萬花筒。某個個體經常忠誠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個土層的沙石都能找到對應人群。 事實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時盛時衰,絕非靜止不動,而是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就像一種不斷改變形狀、大小,甚至顏色,但始終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膚淺的表現——耶路撒冷作為媒體所說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時新聞秀場”——是相對晚近的。有幾個世紀耶路撒冷似乎喪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數情況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啟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獻熱情。 每當耶路撒冷要被遺忘、變得無關緊要時,那些虔誠崇拜《圣經》、潛心鉆研《圣經》的遙遠地方的人們——不管是在麥加、莫斯科還是在馬薩諸塞——都會將他們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認識外部思維模式的窗戶,但這座城市卻是一面雙面鏡,她既能展示其內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絕對信仰的時代、正義帝國構建的時代、福音啟示的時代,還是世俗民族主義的時代,耶路撒冷都是時代的象征與角逐的對象。然而,就像馬戲團的鏡子一樣,它反射的內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時甚至是怪異的。 耶路撒冷有辦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訪問者遭受失望與折磨。塵世之城與天國之城的差別是如此令人難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進入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綜合征”,即一種由期望、失望和幻覺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綜合征也有政治性誘因:耶路撒冷藐視理智、現實政治和戰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擁有貪婪情欲和無可匹敵情感的王國,理性在這里顯得蒼白無力。 即使在這場爭奪統治權和真理的斗爭中,對其他人而言,勝利也只是增強了這座城市的神圣性。壓迫者越貪婪,競爭越激烈,就越發能激起本能的反應。在這里,結果往往會超出預期。 沒有其他地方能夠喚起這樣的獨占欲。而這種嫉妒心頗具諷刺性,因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跡以及與此相關的解讀,都是借來的或偷來的,它們原本屬于之前的宗教。這座城市的過去通常是虛構的。實際上,每一塊石頭都曾屹立在另一種宗教久被遺忘的神廟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個帝國的凱旋門上。伴隨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來的是在強占其他宗教的傳統、故事和遺址的同時,抹去這些宗教存在的痕跡。耶路撒冷經歷了許多破壞,但征服者通常不會摧毀之前就有的東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為它添磚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衛城、錫安山和圣墓大教堂這樣重要的遺址沒有出現明顯的歷史分層,它們更像復寫紙和刺繡作品,里面的絲線是如此縱橫交織以至于現在已不可能將它們抽絲剝繭。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競爭導致一些圣跡先后對三大宗教都變得格外神圣;國王裁決它們的歸屬,人們為它們而犧牲——而今它們幾乎被遺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熱的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現在很少見到穆斯林或猶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為基督徒的場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遠不如神話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問我真相的歷史,”著名的巴勒斯坦歷史學家納茲米·朱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說,“若拿走虛構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無所有了。”在這里,歷史的影響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學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力量,考古學家有時和士兵一樣擁有巨大能量,他們被征募過來為現在的目的而盜用過去。一個以客觀、科學為目標的學科可以被用來粉飾宗教民族偏見,為帝國野心提供辯護。19世紀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國主義者都曾犯下征用歷史事件,賦予它們矛盾的意義和事實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歷史既是真相的歷史,也是傳說的歷史。但其中有歷史事實,而這本書致力于講述這些歷史事實,不論對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難以接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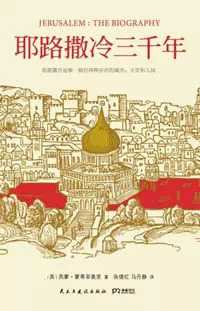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3:06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