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當清華民謠風靡全國的時候,北大民謠在干什么?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換個形式的Sayings: 今天推薦的是一篇講北大民謠的文章。里頭提到的《未名湖是個海洋》和一群民謠歌手,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前輩,有的是如今的投資偶像。不久前,北大舉辦了“草坪音樂節”,這些人一下子都冒了出來。但就像文章里說的那樣,老人們都頭發稀疏了,可愛溫柔又有些小憂傷的年輕人散發著誘人的粉香。 時代變了。 清華走出的李健正在重度流行。這是他應得的流行,而且讓人欣慰的是,這是他許多許多年之后才開始的流行,他不是突然冒出的新人,此前,他已經在我這么大的人耳朵里響了很多年,不咸不淡的,名氣不大不小。他突然以我不熟悉的面目出現,不讓人討厭,只是讓知道此前那個年代的人感嘆。 人也都變了。 自沒有紅遍全國時開始,李健和那些清華民謠的歌手就和北大歌手有著特別明顯的不同。很難描述這種不同,一種是克制的清楚的,一種是由著性子混沌的;一種唱歌時想著別人,一種卻更多想著自己。 沒有辦法做褒貶。我是像后一種人那樣過完北大生活的,現在卻更像前一種人。并不是說哪種好,哪種壞,只是我覺得,清華歌手們提前結束了青春應該有的樣子,但當他們走出青春期之后,他們不需要面對北大學生那種轉型的痛苦和迷茫,也不會面對一些北大學生(包括歌手)“再也沒有走出青春期”的困惑。 這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2011級本科生方凱成的作品,刊發在微信公眾號“北大青年”上,有刪節。 正文: 我還記得六年前在上海的一件小書房里,第一次聽到了《未名湖是個海洋》,我激動地幾近流淚。多年后在北大旁邊的一家小飯館里,我導師夾著大白菜聽我說完這個故事后,淡淡地說了一句:“許秋漢是我的室友,當時在寢室寫這歌跟我商量來著”,我終于確信在上海那間小書房的眼淚和這首歌的意思沒有半毛錢關系。 “這真是一塊圣地,今天我來到這里……湖水淚水汗水血水在閃爍,告訴我這里沒有游戲”,當時只被我當作了絕佳的高考勵志歌曲,如果這也算理想主義的話,確實證明北大民謠無論如何解讀,都緊緊和理想主義聯系在一起。 六年后,快要畢業的我站在一體的草坪上,再次聽到了作為整場草坪音樂會末章的《未名湖是個海洋》。那些頭發有些稀疏的老人們帶走了民謠的劍氣,可愛溫柔又有些小憂傷的年輕人散發著誘人的粉香。 當清華民謠流行全國的時候,北大民謠在做什么 幾乎所有中國流行音樂史寫到“校園民謠”這一章的時候,都把1994年大地唱片公司推出的《校園民謠1》作為起點,這張專輯收錄了1983-1993的校園音樂。《同桌的你》、《流浪歌手的情人》、《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都是高曉松寫的歌,直到1996年高曉松作品集《青春無悔》問世,清華從一開始就似乎成為這場民謠運動歷史的書寫者。除了高曉松之外,宋柯、李健、水木年華等一批清華人在中國樂壇大放異彩,才高八斗的高曉松以“詩與遠方”不斷構建并書寫著這段歷史。“北大是個文科學校,女生太多,男生都沒有練琴寫歌的動力”,高曉松常常善意地為北大民謠開脫,也把北大民謠從中國民謠史里請了出去。 (《校園民謠》) 我們剛上學的時候,以各種方式黑清華是一個必學的技能。但是快畢業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清華人團結友愛、勤勞踏實的干事作風,確實大大超過北大。而且,正是清華人會做事,才在改革開放的商業大潮里,把“校園民謠”推得如此火熱。可是,如果說校園民謠史的起點,我們可能還需要往前看看,至少要看看一個叫徐小平的北大團委老師當年在宿舍泡方便面時,是怎樣的落寞。 1988年,以北大學生創作為主的專輯《寂寞的星期天》出版,但這首專輯里的歌似乎除了徐小平自己的《星期天》以外,并沒有流傳下來別的歌。即便是《星期天》,和《同桌的你》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了。如果“校園民謠”從94年開始算,至今21年,而北大民謠則已近30年了。 當我們重新來看這段歷史的時候,不得不借用現有的以《校園民謠1》為起點的敘述結構,把“校園民謠”放到更大的歷史框架下來觀察。李鷹在寫《校園民謠志》的時候說:“《校園民謠1》的成功在于它清新樸素的獨特風格,以及它那打動所有人的真情實感。之前大陸本土創作從信天游開始,到1991年的搖滾風,流行過的音樂都是激昂甚至暴烈的。可校園民謠與之前的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甚至有點兒低吟淺唱,給人以娓娓道來之感”,李皖在他的《多少次散場,忘了記了憂傷:六十年三地歌》中,把1994-2009中的一個主題定為“民謠,民謠”,在“校園民謠”興起前,以李春波為代表的“城市民謠”已經興起。 高曉松回憶說當時沒有什么娛樂,就是在草地上彈吉他想著追姑娘。但是,即便是高曉松都沒有準確地告訴我們那個年代的校園。他唱:“當歲月和美麗已成了風塵中的嘆息,你感傷的眼里,有舊時淚滴。在相信愛的年紀,沒能唱給你的歌曲,讓我一生中常常追憶”。然而,并不是只有在校園里才有“相信愛的年紀”,正如《校園民謠1》磁帶的封面上寫的;“每一首歌都來自一個動人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發生在你生活的四周”,清華民謠寫在校園,卻仍很社會。 95年《沒有圍墻的校園》幾乎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早搜集北大民謠的專輯了,隨后是2005年發行的《未名湖是個海洋》。北大民謠并不出名,或許因為它太校園,太北大。如果說民謠的重要特點是敘事,那北大民謠的敘事幾乎到了一種令人發指的地步。徐小平用他沙啞的嗓音和濃重的口音唱出的《星期天》,給我們敘述了一個無聊透頂的空虛生活:“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靜靜悄悄是校園,是校園/北京同學都回家去團圓/呼兒嘿喲,留下俺這外地人受呀么受孤單”。 如果這段歌詞還只是北大民謠的暖場,那么北大民謠的狐貍尾巴馬上就要在最后一段露出來了:“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轟轟烈烈是校園,是校園/校長書記來宿舍,問寒問暖/呼兒嘿喲/叫俺樹立無產階級人呀么人生觀”。“書記”、“校長”、“無產階級人生觀”——當這些詞語出來的時候,我們大概能聞到80年代末的北大校園的氣氛了,北大青年的熱血很大一部分是關于國家和政治的。1993年的校慶,北大圖書館東門大草坪上據說匯集了北大青年和大量來自當時海淀區的一個聚集著流浪詩人、藝術家、畫家、音樂家的村子的人。在未名湖邊狂歌,或許紀念,當然這種自發性的大型活動是校方最担心的。 91級社會學系許秋漢在那之后寫了《未名湖是個海洋》:“這真是一塊圣地/夢中我來到這里/湖水淚水汗水血水在閃爍/告訴我這里沒有游戲/未名湖是個海洋/詩人都藏在水底/靈魂們都是一條魚也會從水面躍起”。這幾乎會讓所有人想起北大中文系謝冕教授著名的《永遠的校園》:“這真是一塊圣地。數十年來這里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于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許秋漢接下來馬上就寫道:“讓那些自由的青草滋潤生長/讓那泓靜靜的湖水永遠明亮/讓螢火蟲在漆黑的夜里放把火/讓我在燭光下唱歌”。 這未免也太北大了一些,如果《未名湖是個海洋》仍舊籠罩著對北大“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懷念,那90年代的校園彌漫著的失望、迷茫、彷徨則在許秋漢的另一首叫《長鋏》的民謠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無可牽掛/十年寒窗付東流,壯志未酬歸故鄉/天下,興亡事。在我,胸中藏/嘆望世上滿目蒼涼,碌碌奔波空悲傷/長鋏,歸來乎?士可殺,不可辱/從今后對酒當歌,樂得逍遙回故鄉。”這是北大民謠版的“青春散場”,他們總覺得自己的青春和國家命運是緊密相連的。自己的青春散場,關系著國家的興亡。這種奇怪的調調,想必也是出不了校園的。 82級經濟學系的代世洪的《陜北1998》前半段像是信天游:“山里的花兒開/遠遠的你走來/是你的身影依舊/牽了我的手兒走/割不斷這許多愁”,后半段則有著崔健的搖滾味:“問過了高山我問大海/年輕的幻想和未來/天長地久在等待/等那滿山的鮮花開/問過了高山我問大海/總是說人生要忍耐”。這屬于“校園民謠”時代之前的歷史卻殘留在1998,那種原始生長力似乎根源在北大的土地上,在白衣飄飄的年代,它仍舊剛強。 北大民謠也不是不寫愛情,83級英語系許曉峰寫的《紅毛衣》寫了一個奇怪的愛情故事:“那個女孩告訴我/你應該/應該學會彈吉他/你應該/應該學會說外語/這樣我會更喜歡你/早上ABC ,晚上dore mi/站在鏡子前,找不到我自己”。難道愛情不應該是承受歲月無情下的容顏,仍然一生有你,在你身邊嗎?可是北大民謠寫的這個愛情故事,卻不是“你”而是“我”。我依然愛著你,為你改變,可是當我站在鏡子前的時候,那個強烈的“自我”卻仍舊在嘲諷著我的委曲求全,哪怕是偉大的愛情,都不能勝過獨立自我的良心。 北大人不但強調“自我”感,還相互提醒。 03級光華碩士夏威寫的《致老朋友》大可以和《睡在我上鋪的兄弟》一起來看,煙、酒,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可是清華的憂傷在于回不去的往昔、墻上的字跡,看著老友說現在有很多朋友,暗自嘆息信寫得越來越客氣。但是在《致老朋友》里卻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氣質:“嗨!再喝了這杯酒/今夜我和你不醉不休/該來的終歸會要來/該去的不必再為它挽留/漫長的旅途還是要慢慢走/嗨!我的老朋友/珍惜你和我相聚的時候/無論你過的忙碌或從容/無論你變的貧窮或富有/只是不要讓日子掩埋了你的所有”。北大人有時候太過“自我”,幾乎把獨立之思想看得最珍貴,因而對自己的老朋友最好的要求,不是一起回去“看看我們的宿舍我們的過去”,而是要求他在人生道路上不要忘了當年在校園里的獨立之精神。 很多人批評北大人不抱團太自私,這是對的。如果按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學說,“獨立”是一個中道的最好的德性,那北大人總是為了保有它而往“自私”偏一點點。93年沈慶拉著大伙干專輯的時候,清華民謠很快就團結起來干出了一番對中國音樂史影響深遠的事業,北大民謠還在校園里哼哼唧唧地憂國憂民。 從新青年到大齡女青年 90年代的滾滾紅塵終究是涌進了校園,但這種變化也是“校園民謠”的一部分。北大民謠不但有80歲月,而且忠實地記錄下了自己的變化歷程。李曉(95級經院)在《什么時候》里用略帶懶散的聲音唱著:“大學生活的那幾年/大家忙著各自打算/你忙TOEFL,GRE/我忙我的喝酒聊天”。當一個共同的關于對國家的夢想開始動搖的同時,各種各樣生活的可能開始展現,“各自打算”這四個字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直至今天都未能改變。 李曉繼續唱,或者說向這個時代的新青年們問道:“什么時候我們已不再簡單,一天到晚總想著掙錢?/什么時候未名湖的湖畔,來往著一個個的旅游團/什么時候南墻建了又拆,校園附近變成了商圈/什么時候小南門外的飯館,已經變成了四環”。清華民謠已經奮不顧身投入到商業運作的大潮里,勇敢地走出圍墻時,北大民謠還在遲疑著。直至2005年才開始出專輯,2015年才開始辦草坪音樂會(仍舊對商業邏輯半推半就著)。 不管怎樣,早期北大民謠里那些沙啞的嗓音,帶著口音的咬字,甚至是簡陋的錄制效果都已經不見了。進入00后,北大民謠里的聲音開始變得更加干凈、夾著氣聲,淡淡的憂傷,小小的俏皮,漫出了柔弱的香粉氣。 湯韻(99級國關)的《真感情》里的那個聲音,對于高中時的我來說,就像知青們在被窩里收聽敵臺忽然聽見了鄧麗君的聲音一樣。那樣的柔軟、干凈、天真、純潔,在自己小世界里有著很多不解疑惑,睜著眼睛抿著嘴有一些小憂愁。這首歌給了我無數關于北大愛情的幻想:“認識你似乎已有數不清個日子/還覺得自己是個孩子/ 弱水三千是否一樣的涼/誰都只能取一瓢來嘗/真的感情是否總是像戰場/還是簡單/到只有一點感傷。”我曾經被這首歌深深地打動過,但和被《長鋏》打動完全不一樣。我可以完全放下那種對宏大命題的哀傷與悲愴,只是安靜地閉上眼睛,享受一個細膩可人的聲音在耳邊絮語,那種甜蜜與美好是不可匹敵的。 恰恰是北大民謠的這一系愈走愈強。畢竟這個不再談理想和政治的時代,對北大的幻想,就是“文藝”。終于,北大民謠以“文藝”的名義,晚清華民謠20年走出了校園。 邵夷貝(02級新聞)的《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湯韻聲音中的那些顫抖和羞澀是90年代北大民謠走出校門的最后一點扭捏,那邵夷貝收放自如,有些壞壞的俏皮則帶著撲向社會的濃濃欲望了。當邵夷貝把“可是嫁人這一個問題,又不是她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最后的“de”唱成“da”,愛上她的青年應該已經繳械了,再聽到“她問她爸爸,她問她媽媽”那種童音一般的強調,另一些意志堅強的青年也應該繳械了。 如果說邵夷貝半瞇眼的似笑非笑帶著壞壞的俏皮,那程璧(09級外國語學院碩士)的大眼睛和清純的打扮,可以算得上真正的森林系文藝了。文藝不能沒有思想,如果不俏皮那一定要感傷,程璧空靈的聲音配上《一切》的詞,會勾起青年們心中莫名的感傷,似乎未經世事就已滄桑:“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云/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一切歡樂都沒有微笑/一切苦難都沒有淚痕一切語言都是重復/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于曉雯(10級環境科學)的《我愛你,北京的天》,是2015年草坪音樂節發行的最新北大音樂專輯的最后一曲,算是當代史了。我在草坪音樂節第一次聽于曉雯現場唱的時候嚇了一大跳,當初她給我們排練一二九合唱的時候可能是擺出了學姐的威嚴,還沒那么萌。但當于曉雯在歌詞里夾雜著“咳咳”、“嗯嗯”等語氣詞,營造出一種初中生選中隊長演講特有的緊張時,北大民謠新時期的主旋律又出現了——“霧霾天,讀書天,只有上自習最安全”——這是每一個北大人的小生活,磕磕絆絆,時而抱怨時而又要跟生活撒嬌。 在這一系的女聲之外,北大音樂圈最有影響力的是04法學徐鳴澗。《永遠》、《微光》、《青春大概》等可能是現在除了《未名湖是個海洋》之外,流傳最廣的一些歌了。《青春大概》是我高中時常聽的一首歌:“哭過笑過戀過恨過/仿佛是一夢蹉跎/迷惑失落猶豫寂寞/誰都是凡人一個/在遺忘中不舍/醉心交錯/青春大概如你所說/在花落時結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這樣過”。這些青春的感傷和情愫顯得比高曉松那個年代更不“敘事”了,更文更細膩了。 現場照片來自法學院2011級本科生楊肯,其他圖片資源來自網絡 世相 倡導有物質基礎的精神生活 文章兼顧見識與審美 也許長,但必定值得耐心閱讀 覆蓋千萬文藝生活家的自媒體組織“文藝連萌”發起者 微信:thefair 微博:@世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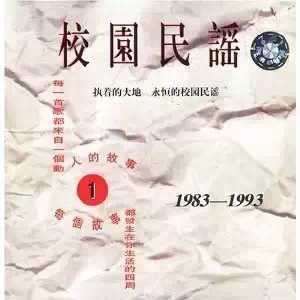

(草坪音樂節現場的徐小平)
(許秋漢和他的朋友們)
(許曉峰在草坪音樂節現場)
(邵夷貝)
(程璧)
(于曉雯在草坪音樂節現場)
世相 2015-08-23 08:50:5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