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卡夫卡:任何不是文學的東西都令我厭倦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卡夫卡的小說并不是關于宗教,玄學或者道德問題的論文——他們都是文學作品。卡夫卡不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或神學家對我們說話,他只是一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回復一封年輕讀者關于卡夫卡問題的信中曾這樣寫道。沒錯,卡夫卡,他是書寫了現代人的困境,但我們卻不必將他封神。 然而對許多卡夫卡評論家來說,欣賞卡夫卡,首先卻是把他放在作家這個身份之外。讓·斯塔羅賓斯基說,卡夫卡知道如何給予一部文學作品以宗教意義。曼克斯·布羅德說,我們應該把他的一生和作品放在神明類里,而不是文學類里。皮埃爾·克勞索斯基說,他不僅要創造一組作品,而且還要傳遞一個信息。 但是卡夫卡自己卻是這樣說的:“我的情形難以忍受,因為它與我唯一的愿望和唯一的使命——文學——相沖突。”“任何不是文學的東西令我厭倦。”“任何與文學不相干的事情,我都討厭。”“倘若我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運用自己的才能和潛力,那只能在文學范疇。” 卡夫卡不顧一切地想成為作家。每當他認為他的愿望受到阻攔時,他都會深陷絕望當中。當他被派去負責他父親的工廠,他覺得他在兩個星期里將無法寫作的時候,他恨不得了結自己的性命。他《日記》里最長的一段寫了他每天如何掙扎,如何不得不上班做事、不得不應付別人以及不得不對付自己,以便能夠在他的《日記》里寫幾個字。或許,最能代表卡夫卡獨特性的作品,是他的短篇。而他,則只是個在繁冗生活中掙扎的書寫者。 一道圣旨 有這么一個傳說:皇帝向你這位單獨的可憐的臣仆,在皇天的陽光下逃避到最遠的陰影下的卑微之輩,他在彌留之際恰恰向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讓使者跪在床前,悄聲向他交代了旨意;皇帝如此重視他的圣旨,以致還讓使者在他耳根復述一遍。他點了點頭,以示所述無誤,他當著為他送終的滿朝文武大臣們——所有礙事的墻壁均已拆除,帝國的巨頭們佇立在那搖搖晃晃的、又高又寬的玉墀之上,圍成一圈——皇帝當著所有這些人派出了使者。 使者立即出發。他是一個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會兒伸出這只胳膊,一會兒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開弓地在人群中開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標志著皇天的太陽,他就如入無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這樣眾多,他們的家屋無止無休。如果是空曠的原野,他便會迅步如飛,那么不久你便會聽到他響亮的敲門聲。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他的力氣白費一場。他仍一直奮力地穿越內宮的殿堂,他永遠也通不過去。即便他通過去了,那也無濟于事,下臺階他還得經過奮斗。如果成功,仍無濟于事,還有許多庭院必須走遍。 過了這些庭院還有第二圈宮闕,接著又是石階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層宮殿,如此重重復重重,幾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沖出了最外邊的大門——但這是決計不會發生的事情——面臨的首先是帝都,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積如山。沒有人在這里拼命擠了,即使有,則他所攜帶的也是一個死人的諭旨——但當夜幕降臨時,你正坐在窗邊遐想呢。 愛的險境 我愛一個姑娘,她也愛我,但我不得不離開她。 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況是這樣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裝的人圍著,他們的矛尖是向外的。無論何時,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會撞在矛尖上,受了傷,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這姑娘對此沒有罪責嗎? 我相信是沒有的,或不如說,我知道她是沒有的。前面這個比喻并不完全,我也是被全副武裝的人圍著的,而他們的矛尖是向內的,也就是說是對著我的。當我想要沖到姑娘那里去時,我首先會撞在我的武士們的矛尖上,在這兒就已是寸步難行。也許我永遠到不了姑娘身邊的武士那兒,即使我能夠到達,將已是渾身鮮血,失去了知覺。 那姑娘始終是一個人待在那里嗎? 不,另一個人到了她的身邊,輕而易舉,毫無阻撓。由于艱苦的努力而筋疲力盡,我竟然那么無所謂地看著他們,就好像我是他們倆進行第一次接吻時兩張臉靠拢而穿過的空氣。 衣服 我經常看到有許多配有褶邊和飾物的服裝,穿在勻稱的身材上,顯得很是漂亮。然后我想,這樣精致的衣服保持了不多久,要起皺紋,要招塵土,不再平整,服飾變的粗糙,而且去不掉。然而并沒有人為此發愁,并且也不以此為可笑。每天早上照樣穿著同樣昂貴的衣服到晚上才脫掉。 然而,我看見過一些姑娘,她們真是漂亮,肌理骨肉都是很美的,皮膚結實,細發豐滿,可成天裹在帶頭罩的衣服里亮相,她們露出的臉總是手掌大,在她們的鏡子里反射出來。 有時候,她們從晚會上很晚回來,在鏡子里她們的衣服顯得破舊、膨脹,幾乎不能再穿了,然而就是穿著這身衣服被晚會上所有的人都看見了。 室內滂沱 他用上牙緊緊地咬住下唇,目注前方,一動不動。 “你這樣是毫無意義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可也并不槽糕;再說,即使破了產——這仍然是無稽之談——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輕又健康,學過經濟學,人很能干,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親。所以我要求你振作起來,告訴我,你為什么大白天把我叫來,又為什么這個樣子坐著?” 接著出現了小小的間歇,這時我坐在窗臺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終于開口了:“好吧,我這就都告訴你。你所說的全都沒錯,可是你想想:從昨天開始雨一直下個不停,大概是從下午五點開始的吧,”他看了看表,“昨天開始下雨,而今天都四點了,還一直在下。這本來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時街上下雨,屋子里不下。這回好像全顛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干的,對不對?好吧。可這里的水位不斷地上漲著。它愛漲就漲吧。這很糟糕,但我能夠忍受。只要想開一點,這事還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過連同我的椅子漂得高一點,整個狀況并沒有多大改變,所有東西都在漂,只下過我漂得更高一點。可是雨點在我頭上的敲打使我無法忍受。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這件小事是我無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說,這我也許甚至也能夠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僅僅是我的束手無策。我實在是無計可施了,我戴上一頂帽子,我撐開一把雨傘,我把一塊木板頂在頭上,全都是白費力氣,不是這場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傘下,木板下又下起了一場新的雨,雨點的敲擊力絲毫不減。” 其實,作為一個“有著特別的力量和個性”的藝術家,卡夫卡一生中與繪畫也結下了不解之緣,只不過被他文字的光芒所掩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卡夫卡本人并沒有太珍視這些畫作,他隨意地將它們送人,甚至扔進廢紙簍。1921年底,卡夫卡在給他的朋友、遺作管理者馬克斯•布羅德的“遺囑”中寫道:“我留下的所有繪畫作品等,都要毀掉。” 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作畫。我想看,想把我看到的東西畫下來。我試著以一種完全特別的方式限定我所看到的東西。 ——卡夫卡 卡夫卡《柵欄中的男人》 卡夫卡《用手腳走路的人》 卡夫卡《三個奔跑的人》 《日本雜耍藝人》 《女人頭和馬腿》 《請愿者和高貴的施主》 文字部分摘自《卡夫卡短篇小說經典》(葉廷芳 譯)、莫里斯·布朗肖《從卡夫卡到卡夫卡》;圖片選自網絡;鳳凰讀書綜合。
弗蘭茨·卡夫卡(1883.7.3-192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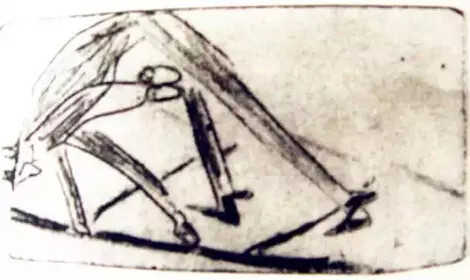


卡夫卡《低頭坐著的男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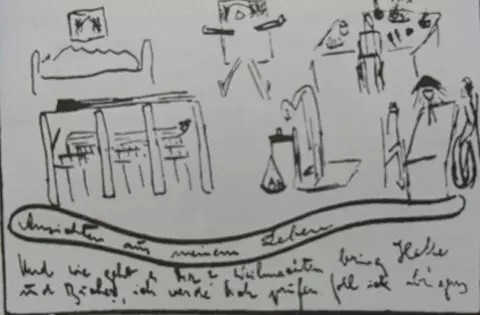
《我的生活》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3:5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