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天國之秋
 |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 簡體 傳統 |
撰文:裴士鋒(Stephen R. Platt) 翻譯:黃中憲 校譯:譚伯牛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第一部 帝國的黃昏 一、傳教士助理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個潮濕和疾病肆虐的地方。有人說島上“到處開挖土地釋出瘴氣”,島上居民終日害怕瘴氣纏身。山與海灣之間坐落著小小的英國人聚落,但翠綠與湛藍的山海風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陰暗。香港的主要街道,街名散發著思鄉情緒(皇后大道、威靈頓街、荷里活道),貨棧、兵營、商行緊挨著矗立其間。離開這些建筑,走上從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壯麗的景致,但走不久即離開白人聚落,觸目所見是散落于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間的華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國人靠著鴉片戰爭拿到這座島嶼當戰利品之后,這一農村景致一直沒變。有些較有錢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蓋了豪宅,宅邸中呈階梯狀布局的花園將山下的港灣和城區盡收眼底。但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離開香港的保護圈太遠,宅中居民于是生病,然后死亡。這些陰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熱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靜悄悄地坐落在山間,人去樓空,像是空洞的眼神在冷冷審視著山下的移民。 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 他是瑞典籍的年輕傳教士,薄薄的絡腮胡襯出他秀氣、幾乎女孩子氣的五官。他天生有著迷人的嗓音,年輕時在斯德哥爾摩曾與“瑞典夜鶯”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臺合唱。但林德繼續走歌唱之路,風靡歐美歌劇院,令肖邦與安徒生之類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時,韓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折。他雄渾有力的男高音,在講道壇上找到注定的發揮舞臺,一八四七年離開故鄉瑞典,坐船來到地球另一端,瘧疾橫行的香港,心里只想著要以另一種方式讓中國人臣服。 韓山文本來大有可能默默無聞度過一生,因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傳教士圈子以外沒人看在眼里。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闖中國鄉間的歐洲人之一。他離開較安全的香港,到中國商港廣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處的一個村子傳教(但后來基于健康考量,他還是回到香港)。他也是第一個學會客家話的歐洲人。客家人是吉卜賽似的少數族群,在華南人數頗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鄉下人帶了一個客人來找他,他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視。那是個矮小圓臉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著一段精彩的人生經歷要說。 韓山文憶起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說這個客家人最讓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了解上帝和耶穌,盡管他來自離香港傳教士狹小的活動范圍很遠的地方。韓山文帶著好奇,聽洪仁玕講述使他踏上香港的眾多機緣,聽得一頭霧水。他說到異夢和戰斗,說到由信徒組成的軍隊和禮拜會,說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廷差役追捕,易名到處躲藏,至少他是這么說。他曾遭綁架,然后逃脫,曾在森林里住了四天,在山洞里住了六天。但這一切聽來太光怪陸離,韓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說這些遭遇的用意,于是請洪仁玕寫下來,洪仁玕照做,然后沒說什么就離去——韓山文原以為他會留下來受洗。韓山文把洪仁玕寫下自身遭遇的那疊紙放進書桌抽屜,將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此后將近一年,他沒把這些紙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成血海,韓山文才意會到洪仁玕粗略交代的那些怪事,意義超乎他想象。 韓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一樣,完全是透過零星含糊的傳聞,得知中國境內情勢日益動蕩。從中國的政府公文,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加劇的混亂有什么模式,看不出存在什么原則或勢力集結之處。中國鄉間的地方暴亂和小股盜匪橫行,始終是帝國當局的困擾,談不上是新鮮事或值得一顧,盡管在鴉片戰爭后這幾年,這類事的確變多了。深入中國內陸的本國旅人和秘密(傳教)的天主教神甫傳言:有個更大的運動團體出現,那個團體由名叫“天德”的人領導。但許多傳聞說那人已經死在官兵手里,或說根本沒那個人。在沒有明確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對這類事情不大關心,只担心土匪使茶葉和絲的生產停擺。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場龐大內戰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門前。上海位于長江出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約三百公里。五十萬名自稱太平天國的叛軍,從華中搭乘大批征來的船,浩浩蕩蕩涌向南京,所過之處,城市變成空城,政府防御工事變成廢物。情勢非常清楚,這不只是土匪作亂。上海人心惶惶,與南京的直接通信斷絕,情況混沌不明(美國輪船“蘇士貴限拿”號〔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個清楚,結果擱淺在路上)。謠傳叛亂分子接下來會進軍上海攻打洋人,上海縣城里的本國居民把門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鄉間避難。洋人倉促著手防御,臨時找來一批志愿者組成防守隊守城墻,并備好幾艘船,打算情勢不妙就上船離開——兩艘英國汽輪和一艘雙桅橫帆戰船,還有供法國人與美國人搭乘的汽輪各一艘。 但太平軍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軍并未進軍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軍把矛頭朝北,指向滿清都城北京,以南京為作戰基地,掘壕固守,準備打一場漫長且慘烈的戰役。他們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遠,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國船排除萬難抵達南京,但帶回來的南京動態消息卻相互矛盾。最明確的看法出自英國全權代表之口,他宣稱太平天國擁有由“迷信與胡說八道”構成的意識形態。那些去過的人對叛軍的出身一無所悉。 盡管欠缺明確的訊息,有關中國內戰的第一手陳述還是從上海和香港往外傳,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歐洲剛在五年前經歷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變,中國的動亂似乎與之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悲慘的中國人民,遭滿人主子欺壓,如今終于挺身要求改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那是“與最近歐洲所遭遇者類似的社會變動或動亂”,說“亞、歐同時發生類似的騷亂,史上絕無僅有”。由此可見,地球另一端的帝國如今和西方的經濟及政治制度有了聯結。 一八五三年担任《紐約每日論壇報》(New-York Daily Tribune)倫敦通訊記者,正埋頭理清他對資本主義之看法的馬克思,也認為中國這場叛亂表明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稱它是英國在最近的鴉片戰爭中強迫中國開港通商的最終結果。照馬克思的說法,中國正發生的事,不僅是叛亂或數場暴動的合流,而且是“一場令人贊嘆的革命”,那革命表明與工業世界的息息相關。他甚至主張,正是在中國,可以看到西方的未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歐洲人民的下一場起義,他們下一個為了共和自由與廉潔政府的運動,其成敗或許更可能取決于目前在天朝上國——與歐洲完全相反的國度——發生的事,而較不可能取決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 誠如他所說明的,中國這場動亂肇因于鴉片貿易;十年前英國用戰船強行打開中國的市場,從中削弱了中國人對其統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與外面世界的接觸將摧毀舊秩序,因為“腐爛必然隨之發生,就像任何細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與室外空氣接觸,就必會腐爛一樣”。但受清朝腐爛影響者,不會只有中國自己。在他看來,整個太平革命是英國所造成,而英國海外作為的影響,如今將回傳到國內;他寫道:“不確定的是那場革命最終會如何反作用在英格蘭身上,并透過英格蘭反作用在歐洲身上。” 馬克思預測,中國市場落入太平革命團體之手,將削弱英國的棉花與羊毛出口。在動亂的中國,商人將只接受用金銀條塊換取他們的商品,從而使英國的貴金屬存量愈來愈少。更糟糕的是,這場革命將切斷英國的茶葉進口來源,大部分英國人所嗜飲的茶葉,在英格蘭的價格將暴漲,同時,西歐境內的農作物歉收看來很可能使糧價飆漲,從而進一步降低對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國經濟所倚賴的整個制造業。最后,馬克思斷言:“或許可以篤定地說,這場中國革命會將火星拋到現今工業體系已然(火藥)過載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引爆,然后在往國外擴散之后,緊接著歐陸會爆發政治革命。” 如果說馬克思一心想讓《紐約每日論壇報》的讀者相信,這場中國內戰是與歐洲境內的運動類似的階級斗爭和經濟革命運動,那么美國南方奴隸港新奧爾良的《每日瑣聞報》(Daily Picayune)的主編則從他們自身的世界觀出發,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這件事。誠如這些主編所認為,這是場種族戰爭,中國是劇變中的奴隸國。他們解釋道,太平軍發跡于廣西和廣東這兩個南部省份,兩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國原始種族”。相對地,北方的滿人是“中國的統治種族”,自兩百年前入主中國之后,“中國一直被其主子當成受征服國家來統治”。他們解釋道,這兩個種族從未混合,然后,與他們的美國南方觀點,也就是以奴隸為基礎的和諧社會觀相一致的,該報表示,在中國,“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數百萬人,以足堪表率的溫柔敦厚,接受他們主子的統治”。這個主奴和平共處的滿漢國,唯一威脅其穩定的是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華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亂與美國黑奴的暴動,有了令人神傷的相似之處。 倫敦《泰晤士報》(Times)最有先見之明,立即抓住問題核心,探討英國是否該派海軍投入這場中國內戰,以及如果這么做,該站在哪一邊。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傳到倫敦后不久,《泰晤士報》某篇社論指出,太平天國似乎所向披靡,“據各種可計算的概率,他們會推翻中國政府”。《泰晤士報》還轉載了上海某報的一篇報道,問道“換人當家做主”是不是大部分中國人所想要,并表示太平天國雖然在華北不大受喜愛,卻代表了一股漢人所樂見的改變力量,“認為不該再忍受官員橫征暴斂和壓迫的心態,似乎在全國各地都愈來愈濃”。到了夏末,《泰晤士報》直截了當宣告,中國這場叛亂“就各方面來看,都是世人所見過最大的革命”。 但叛軍本身卻是個謎。《泰晤士報》的讀者會輕易斷言,太平天國得到漢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強的支持——準備推翻滿人,開啟新政。但該報主編也就英國的無知發出告誡之意。“關于叛亂的源起或目標,我們沒有具體的訊息,”他們寫道,“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政府可能在內戰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們憂心英國不夠了解叛軍的本質或意識形態,而無法決定該不該予以支持或鼓勵:“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無法斷定我們的利益或職責該落在哪一邊——這場叛亂有正當理由或無正當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會促成我們與中國人的關系往好或往壞的方向改變,或是否會促成改變。”但事實表明,其中最迫切的問題——叛亂的根源、太平天國是什么樣的組織、他們的信念為何——答案將在香港尋得。答案就潦草寫在幾張紙上,而那些紙就塞在韓山文書桌的抽屜里。 同年秋天,洪仁玕再度找上韓山文。這時人在廣州郊外村落傳教站的韓山文知道他是什么人:太平天國創建人的族弟和終生奮斗伙伴,這時與太平天國斷了聯系,因緣際會流落香港。洪仁玕是唯一對興起于中國內陸的這股勢力有第一手了解且又與外國人有接觸的人——而這時,在世人終于注意到且遠遠注視下,這股勢力有可能從帝國內部摧毀統治王朝。韓山文與洪仁玕結為密友,一個是三十四歲的傳教士,一個是三十一歲的難民。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終于在韓山文主持下受洗入教,然后隨韓山文回香港。韓山文細心教導洪仁玕認識路德宗教義,打算把他培養成外國傳教士的助手,最終則希望他把他們的基督教派帶到南京的太平天國(但后來洪仁玕表示,那幾個月是他在教外國人,而非外國人教他)。隨著兩人一起工作,韓山文靠他蹩腳的客家話,終于掌握洪仁玕所寫東西里暗示的詳情,終于完全弄清楚他的身世和來歷。 照洪仁玕所述,比他大九歲的族兄洪秀全始終聰穎過人。他們分別住在距省城廣州約五十公里的相鄰的兩個村子里,天氣好時從村子里可看到廣州城東北方的白云山。村民大部分是他們洪氏的親戚,這個氏族曾非常顯赫,宋朝時許多洪氏族人當過高官和皇帝輔佐,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這時他們只是貧窮農民。但他們有一所小書塾,洪秀全七歲時在那里開始讀儒家典籍。他一入學表現就很優異,幾年內熟背四書五經和科舉考試必讀的其他典籍,少年時也已博覽中國文史書籍。由于聰穎過人,族人深信他不需人教,自己就能看懂古籍。他們期盼他光宗耀祖,讓沒落已久的家族重振聲威,他的幾個老師無酬教導,冀望他通過考試當官, 屆時自己得到回報。為獲得更專業的教導,他到離村子更遠的學校上學,由家人集資供他讀書,盡管十六歲時他已當起老師養活自己,領有微薄薪水,薪水主要是米、豬油、鹽、燈油。 要取得當官資格,就得通過以儒家典籍為內容的科舉考試,而洪秀全、洪仁玕兩人都胸懷此志。但科考很難,一次鄉試沒上,通常表示要再等幾年才有機會再考。鄉試時考生得在省城貢院里陰暗潮濕的號舍待上三天,證明自己真的將儒家思想融會貫通于心。洪仁玕本人考試成績一直不理想,但洪秀全于一八二七年第一次赴廣州參加鄉試時,他第一天的成績名列前茅。但隨著考試繼續進行,他的名次下滑,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已跌出榜外。再過了九年,也就是一八三六年,他才又有資格參加鄉試,這一次他又落榜。洪仁玕也從未能上榜,但背負整個大家族光耀門楣希望的是洪秀全。為何最終身心崩潰而病倒的是他,原因或許在此。 洪秀全于一八三七年,也就是第三次應試落榜后不久,首次做了異夢。由于不堪煎熬,身體虛弱,他靠人抬才得以回家。回家后他即無力倒在床上,請家人過來訣別。他向圍在床邊的家人道歉,說他快死了,辜負了他們的期望;然后閉上眼睛,全身癱軟。他們以為他死了,結果后來他醒來,開始向他們說起自己夢到的怪事。夢中有一龍一虎一雄雞走進房間,后面跟著幾個奏著樂、合抬一頂轎子的樂師。他們請他上轎,抬他到一個“華麗而光明之地”。那里有許多男女,看到他非常高興。有個老婦為他洗凈全身,除去污穢。還出現一群老者,他認出其中有古代的中國圣賢。他們用刀剖開他身體,拿出內臟,換上鮮紅簇新的內臟,然后替他合上傷口,但后來他完全找不到剖開的痕跡。他在別人陪同下進入一個大廳,廳內最高的寶座上坐著一個金須黑袍的老者。老者流淚道,世人不尊敬他。他告訴洪秀全:“世人以我之所賜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惱怒。你勿要效法他們。”然后,他給了洪秀全一把劍,用以斬除鬼魔(但告誡他別用來殺兄弟姐妹);又給他一方印璽和一顆黃果。他吃了黃果,味道是甜的。黑袍老者引他俯瞰世間蕓蕓眾生,他到處都看到污穢和罪孽。然后他就醒了。 洪秀全做異夢,斷斷續續做了四十天,洪仁玕待在他身旁,聽他醒來時講述夢中所見。夢中還有其他一再出現的人物,其中一人是個中年男子,他稱為“長兄”,“長兄”帶他一起“遨游遐邇”,用他的寶劍斬除鬼魔。在另一個異夢中,黑袍老者痛斥孔子未將正確學說教予中國人,孔子羞愧地低頭認錯,洪秀全全程在旁觀看。那幾個星期,他的兄弟緊鎖房門,不讓他出去,有時看到他在房間里四處跳,嘴里喊著“斬妖!”對著空中亂砍。他的精神失常引來鄰居的好奇,讓鄰居覺得好笑。他們在他睡覺時上門,湊近端詳這個有名的瘋子。有一次他醒來,聲稱自己是中國皇帝。他家人覺得丟臉又担心。照洪仁玕向韓山文所說的,“親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異,但其時人皆以為并非實際經驗也。”當時,洪仁玕并不相信族兄的異夢其實是天啟——但到了向韓山文敘述自己的遭遇時,他已經相信。 后來洪秀全康復,洪仁玕看到他大病后整個變了一個人——更高,更壯,更聰明許多。這時他變得更好看,膚色白晳,鼻子高挺。他的目光變得“銳利,令人難以卒視”。聲音洪亮,大笑時“響震全屋”。他身體變得更健壯,心智變得更機敏,然后他重拾教鞭,再度準備參加科考。但考運還是不佳。一八四三年他第四次赴廣州參加鄉試,再度落榜。就在這一年,另一個族中兄弟在洪秀全的柜子里找到被遺忘的一本書。那是一本中文的基督教布道小冊,名叫《勸世良言》。幾年前在廣州時,有個傳教士塞給洪秀全這本小冊子,他把它擺在一旁,未拿來看。這位族中兄弟看了一遍,覺得很有趣,于是洪秀全花了時間仔細研讀, 于焉大徹大悟。他告訴洪仁玕,那本書解開了他六年前的異夢之謎。讀了基督教基本信條之后,他茅塞頓開:那個命他斬妖除魔的金須黑袍老者是上帝,助他斬殺鬼魔的長兄是耶穌基督。那些鬼魔是中國人在儒佛寺廟里所拜的偶像,他的兄弟姐妹是漢人同胞。洪秀全自己替自己施洗,然后丟掉他學堂里的孔子牌位。 洪仁玕和鄰居馮云山是最早皈依洪秀全所創宗教的人。他們在河里替自己施洗,拿掉學堂里的“偶像”——孔子牌位和肖像。三人開始一起研讀,四處搜羅中譯的經文。洪秀全向他們講道,不久就向被他的主張吸引來的其他人講道,并以福音書小冊子和他的異夢補充內容——他宣稱福音書小冊子和異夢互證真實不虛。他深信《圣經》明顯是為他而寫。 三位信徒——洪秀全、洪仁玕、馮云山——開始勸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小孩皈依上帝,洪秀全則是上帝派來的先知。傳教并非一帆風順,洪仁玕拆掉孔子牌位,學生因此不再上私塾,他沒了收入,也因此挨了哥哥一頓棍打。氣憤難平的洪仁玕回道:“我是不是老師呢?孔夫子死了許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為什么迫我拜他呢?”洪秀全和馮云山于一八四四年離開家鄉,向廣東省內其他村子和遠地族人傳揚他們的理念,洪仁玕很想同去,但親戚逼他留下來教書,因為他才二十二歲。他不得不把孔子牌位放回私塾,以使學生愿意回來就讀。但即使被困在家鄉,他仍使至少五六十名皈依者受洗。比起韓山文一生的傳教成績,這個成績好多了。 隨著馮云山在鄰省廣西山區逐村傳教,這個運動日益壯大,勢力更廣。自治禮拜會迅速出現,為數達數百的追隨者自稱“上帝會”的一員。他們把洪秀全當作精神領袖,盡管其中許多人從未見過他。洪秀全于一八四五年返鄉時,洪仁玕注意到他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他不再只關注儒家學說,而是以崇拜上帝取代之。他傳道時多了個新基調:把清朝的滿人統治者斥為不當竊據中國者。“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為界,猶如父親分家產于兒輩,”洪秀全向洪仁玕如此解釋道,“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業耶?”他的宗教運動漸漸變成政治運動。 到了一八四七年,上帝會已有約兩千名信徒,以客家人居多。在信仰和人數眾多的鼓舞下,他們開始搗毀佛像與佛寺,引來當局的懷疑。到了一八四九年,“獨立禮拜會已出現信徒(因神靈附體)昏厥痙攣,說靈語情形”。他們希望洪秀全指點他們所說的靈語里,哪些來自上帝,哪些來自魔鬼。一八五○年瘟疫肆虐廣西,病人向洪秀全的上帝禱告即可痊愈的說法傳開之后,信徒大增。無數人加入上帝會,瘟疫平息后,他們把自己得以活命歸功于洪秀全的宗教。 但這些都還不足以催生出軍隊。真正使局面改觀的因素,乃是從外地移來廣西的客家人和當地人發生的土客械斗。較晚來的客家人爭奪土地和水權,住在當地較久的本地家族蔑稱他們是闖入者。一八五○年秋,幾個客家莊和本地人村莊爆發械斗;本地人燒掉客家人房子,客家人找上帝會尋求保護和支持。早已對這個教派心存猜忌的當地官府,這時開始認定它為亂民的庇護所。但據洪仁玕的說法,洪秀全早預見到此事,耐心等待出手時機。 隨著土客械斗蔓延開來,認為亂子是客家人搞出來的清朝官員派了一隊士兵搜捕洪秀全和馮云山。附近的一個上帝會禮拜會得到消息,拿起劍矛,前去解救他們的領袖。他們三兩下就擊敗人數居于劣勢的官軍,洪秀全首次發出號令,要該地區所有上帝會信徒聚集于一地,準備展開下一階段行動。許多人為此賣掉房子跟土地。接下來幾天,他們聚集于一地,人數達數萬。他們輕松拿下一個小鎮,取得第一個軍事勝利。官軍來圍,從鎮外向上帝會信徒開火,但他們于午夜時溜走,隔天早上官軍攻入時,鎮上已幾乎沒人。奉命追擊的官軍在林中遭殲滅,惱火的其余官軍把氣出在留在鎮里的倒霉鎮民上。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宣告成立太平天國,自封為中國的新皇帝“天王”,并分封四位得力助手為東、南、西、北王(馮云山為南王)。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往北打,沿途吸收窮人和賤民、罪犯、所有害怕或痛恨清朝當局者,以及所有愿意皈依他的教派、矢志摧毀儒家學說者,特別是推翻滿人主子者。一八五三年一月他們穿過華中抵達長江邊時,已有五十萬之眾,但途中也死了馮云山和其他無數人。但洪仁玕都是透過他人之口得知此事。第一次聚眾起事他沒趕上,等他抵達那個小鎮時,上帝會的人已趁夜逃走。他想追上他們,卻只見到獵捕掉隊者的官府巡捕。于是他開始逃亡,改名換姓,躲避將他家鄉村子燒光的清廷差役的追捕,然后被一名想領他項上人頭賞金的男子劫持,所幸逃脫,最后避難于香港,得到瑞典傳教士韓山文的收留。 韓山文這輩子所做的事,就只有一件會得到他小小傳教士圈以外的人注意,那就是將洪仁玕所陳述的事譯成英文出版。他這么做是因為那份陳述使他相信了一件事,這場叛亂在他眼中最神奇、最不可思議、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從中國內陸起事欲推翻滿人的叛軍是基督徒。他的書先在香港和上海以《洪秀全的異夢》(Visions of Hung-Siu-Tshuen)為名出版,然后在倫敦以《中國叛軍首領》(The Chinese Rebel Chief)為名出版。那其實無異于宣傳冊子,意欲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相信,太平叛軍和他們拜一樣的上帝。此外,用韓山文的話說,那也是欲借由喚起“對中國數百萬人……更熱切、更持久的同情”,以爭取外國支持這些叛軍——而他所謂的中國數百萬人,當然不是指那些仍效忠于滿人的中國人。 最后,韓山文出版此書以為太平天國募款,由于他與洪仁玕的友誼,他已成為該運動的熱情支持者。他在該書末尾寫道:“讀者幫助此書之推銷,即有功于書中多人之赒濟,此可以為慰者也。” 一八五四年五月,韓山文完成此書時,給了洪仁玕和兩名友人到上海的盤纏,冀望他們能從上海溯長江而上,穿過清軍警戒線,與南京的太平天國再度會合。他送了洪仁玕重重的禮物,其中有多種中文書籍:外國傳教士所編的欽定《圣經》譯本,還有歷史著作譯本和多張世界地圖、中國地圖以及巴勒斯坦地圖。韓山文還給了他歐洲人想讓中國人留下深刻印象時會送的標準物品——單筒望遠鏡、溫度計、指南針(盡管指南針是中國人所發明)。他希望洪仁玕成為歐洲傳教士與太平天國搭上線的橋梁。而那將只是開始:韓山文真正希望的乃是他們一旦到了南京,他本人能跟著過去,然后他能以宗教導師身份加入太平天國。洪仁玕提過他很希望韓山文跟他一起去天京,但韓山文不想造次,堅持要太平天國正式邀請,他才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但南京之行未能如愿。洪仁玕與在上海接待他的傳教士發生爭吵(他們在他房間里發現一根鴉片煙管,盡管他聲稱那是某個來找他的友人留下來的),而且無論如何,他們沒辦法幫助他到南京。 據夏春濤引施其樂相關敘述,裴士鋒原文所謂這次“爭吵”似在洪仁玕與同行友人李正高間發生,因李氏邀請一癮君子舊友同住,導致洪仁玕等人俱被逐出教會接待住處。上海的中國人居住區,即上海縣城,當時由一個支持太平天國的秘密會社(小刀會)控制,而那個會社不相信他是天王的親戚,不愿幫他。洪仁玕在上海待了幾個月,在那段時間到處找門路,在一所教會學校讀天文、歷數,最后打消與太平天國再度會合的念頭。他搭汽輪回香港,途中輪船以驚人速度航越中國外海。返港后有感而發,他寫了首詩,將波濤翻騰的大海比擬為戰場,將破浪的船行聲比擬為“軍聲十萬尚嘈嘈”,抒發他渴望加入那場無緣與會的戰爭的心情。但回到香港時,他的瑞典朋友沒有來找他;洪仁玕離港赴滬幾天后,韓山文染上殖民地的“瘴氣”,死于痢疾,享年三十五歲。 洪仁玕一八五五年返港,結果一待數年未離開。他找到一份長期工作,當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助理,替新入教者傳授基本教義。他是受過洗的基督徒,由于和已故的韓山文交好而為人所知,因此極受信賴,而和善可親的個性,使他贏得更廣大傳教士圈子的好感。他的上司和接下來幾年與他合作最密切的人,是身體笨重、留著大絡腮胡的蘇格蘭籍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當時理雅各正致力于將整套儒家典籍(即煉獄般的科舉考試的命題來源)譯成英文。理雅各與洪仁玕合作無間,常一起講道——先是理雅各以他新學會的粵語講,然后洪仁玕以客家話講。與過去的做法不同的是,洪仁玕在香港的講道內容,反映的是理雅各的理念,而非他族兄的理念。 不輕易稱贊中國人的理雅各,極喜愛洪仁玕,稱他是“我所認識最和藹可親、最多才多藝的中國人”。理雅各女兒贊同此說,說她壞脾氣的父親對洪仁玕“特別喜愛,極為敬佩,幾乎沒有其他中國人得到他這樣的喜愛和欣賞”。洪仁玕的個性里的確有某個地方——謙遜的特質、聰明的特質——得到與他共事的許多教士注意。另有一位傳教士稱他是“能力出眾、人品極佳之人”,“對基督教真理有明確且高明的認識”。理雅各在倫敦傳道會里的一位同僚俏皮地說道,只要看到有個中國人常與洪仁玕交談,“大概就可以確定會有好事發生”。敬佩他的不只外國人,有個曾赴愛丁堡留學的中國醫生,也說他是“極聰明、口才甚佳之人”。但由于后來所發生的事,其他人檢視他過去的言行,會懷疑那是不是裝出來的,懷疑使洪仁玕博得外國人好感的“和善可親個性和討人喜歡的基督徒作風”,只是遮住狼身的羊皮。 南京陷落后那些年,香港人口開始有了變化。滿清政府開始大舉搜捕太平天國黨羽,將抓到的全部正法,有些人因此逃到這個安全、穩定的英國殖民統治區避難。清朝官兵動不了太平天國所控制的南京周邊地區,但在名義上仍歸朝廷管的中國其他地方,肅清黨羽的活動非常殘酷。朝廷的目標除了太平天國黨人本身,還有每個太平天國已知成員的親戚——不管那些人有多無辜——就連他們家族最遠的分支也不放過。在廣州——距珠江出海口處的香港只約一百五十公里——兩廣總督葉名琛帶頭在轄區內掃蕩,肅清太平天國黨羽,手段特別殘酷。一八五四年,為回應他所認定(很可能是誤以為)的支持南京叛民的一場秘密會社暴動,他的部屬在廣東撒下大網,捕獲被控支持太平天國之人,據估計有七萬五千人。對于那些漏網之魚,官府設立了自殺站:備有自殺工具(匕首、繩子)的亭子,亭子上張貼布告,呼吁亂黨的支持者選擇速速自我了斷,以免最后被生擒凌遲,不獲全尸,而使家人蒙受更大羞辱。 一八五四年直到一八五五年間,兩廣總督葉名琛命人執行了英國領事所謂的“一連串處決,那是人類信史所記載,在規模和方式上最駭人的處決之一”。據某位親眼所見的英國人所述,數萬名被指控支持太平天國之人在廣州刑場遭到殺害。刑場是條擺滿陶器的小巷(在較安定時期那是個市場),散發鮮血凝結后的腥味。他說:“數千人死于刀下,數百人以十二人為一組綁在一起丟入河里。”他看著那些人遭處決,大為驚駭:一名劊子手抓住被綁著跪在地上的囚犯頂髻,另一名劊子手揮刀砍下他的頭。那地方非常窄小,但劊子手手法利落,這名目擊者看了四分鐘就看不下去,而在這四分鐘內,他算過共有六十三顆人頭落地。他寫道:“場面很恐怖,斷手斷腳斷頭的軀體,幾十具布滿整個刑場,無頭軀體之間散落許多剝掉皮的肉塊。”現場有數只箱子,等著裝砍下的囚犯人頭,送到總督面前,以證明已執行應行的處決,但砍下的人頭太多,箱子裝不下,最后劊子手只把耳朵(右耳)裝箱,僅此亦箱箱滿溢。 另一名目擊行刑場面的是中國人容閎。他于一八五四年自耶魯大學畢業,這時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已完全美國化的他,希望為朝廷效力,希望以美國為師推動教育改革。他先到廣州以拾回他幾乎忘光的中國話,卻在刑場看到這一幕,使他重新思考該不該支持一個容忍如此野蠻行徑的政府。誠如他所述:“(嗚呼!)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尸縱橫遍地。蓋以殺戮過眾,不及掩埋。”而被屠戮者太眾,“且因驟覓一遼曠之地,為大壙以容此眾尸,一時頗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時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此累累之陳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 廣州大肆處決人犯,大大改變了香港的命運。大批難民涌入這個殖民統治區,除了性命受到兩廣總督手下威脅的逃犯,還有來自華南想找個較安穩地方經營事業的富商。這些新移民蓋房子,推高既有房屋的租金,創立新的貿易公司,為香港注入旺盛的新活力,使香港欣欣向榮。傳教士大為欣喜,原本洋傳教士要到廣州并不容易,如今看來反倒可能所有廣州人都來到他們跟前。廣州城殘酷血腥的鎮壓,也使外界對朝廷有了新的認識,并感到心寒,就連質疑太平天國動機的外人,都無法替現行政權回應太平天國時做法的野蠻可怕辯解。 理雅各很清楚他的三十三歲助手洪仁玕是太平天王的族弟,但他遠不如韓山文那樣欣賞這些叛軍。他堅決認為,只要太平天國的教義是來自他們所謂的天王,而非來自受認可的教派,他們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此外還有他很不能接受的事:洪秀全自認是耶穌基督之弟。理雅各很喜歡洪仁玕,但他對于洪仁玕的大家族所為大體上不感興趣,一再勸他別想著南京的事,應全心奉獻于香港的傳道和進修——因為他深信,如果情勢照目前這樣繼續擴大,全中國遲早會被打開,屆時傳教士將通行無阻。 洪仁玕本人似乎謹記理雅各的勸諫,幾年時光就這么過去。他接下多種職務——除了陪理雅各四處跑,還赴獄中探望囚犯,赴醫院講道。香港有一所傳教士創辦的學校,名叫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洪仁玕在該校教中國基督徒學生中國歷史與文學,也協助理雅各英譯儒家典籍,就是他為了在清帝國當官這個已揚棄的夢想而精通的那些典籍。在華北的內戰陷入僵局,華南因報復行動而動亂不已之際,洪仁玕在香港當理雅各的助手,安全、安靜、有效率地工作。太平天國的同志找不到他,若抓到他會將他就地正法的清朝官府也找不到他。 對后來的發展影響更大的,乃是洪仁玕在香港這幾年期間也對中國以外的世局有了廣泛的了解。了解的程度或許不如在耶魯受教育、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容閎,但絕對比其他任何太平天國的支持者高上許多。嚴格來講,香港仍在中國境內,卻是中國與大英帝國和更廣大的世界聯結的節點。在傳教士所辦的學校里,在他們所翻譯、用以宣揚他們自己文明之長處和發現的書籍里,他學到歐美在政治經濟、科學、醫學、政府行政乃至軍事科學方面的觀念。他見識到這個英國殖民統治區的運作——使社會井然有序的方式、貿易在其經濟中的地位、教堂在其道德生活中的地位。這些只是對大不相同于他已知社會的香港社會浮光掠影的一瞥,但這一瞥讓他銘記在心,且將久久難忘。但最重要的,那是那幾年里難得的愜意日子。他和理雅各研讀、講道,間或到香港島的山上踏青健行。那四年,中國大陸烽火連天,而他們過著以讀書、講道和野餐為主的生活。 但洪仁玕的好人緣有利也有弊。因為他不僅受到傳教士喜愛,也受到每次他冒險出門就圍在他身邊的大批中國人、被廣州刑場的幽靈趕到香港的大批難民喜愛——甚至應該說大受喜愛。理雅各很清楚,那些在洪仁玕一到碼頭時就湊上去的人,不是要問他宗教的事,至少不是問理雅各所認知的宗教的事。他們要問他族兄和叛亂的事,問他是否會帶他們去南京和太平天國。其他傳教士私底下悄聲說道,如果洪仁玕能到南京,他能照他在香港所學的東西糾正他們的教義。他能獨力將真正的基督教帶到中國。最后,就是這些傳教士背著理雅各讓洪仁玕前往南京。 一八五八年晚春理雅各返鄉探親期間,洪仁玕偷偷離開香港。其他傳教士給了他盤纏,承諾發薪俸給他留在香港的親人,但未將此事告訴一再告誡他遠離太平天國的理雅各。洪仁玕留下一首詩,表白他離開安全的香港時的心境。那是首樂觀的餞別詩,一個終于覺醒而準備與其家人、會眾重聚的孤獨旅人的心聲: 枕邊驚聽雁南征, 起視風帆兩岸明。 未挈琵琶揮別調, 聊將詩句壯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 地隔關山雁有情。 把袖揮舟爾莫顧, 英雄從此任縱橫。 這一次他未帶《圣經》或望遠鏡,也未搭便捷的汽輪。他未帶在香港簇擁著他的那些民眾,甚至未帶費盡千辛萬苦到香港和他會合的寥寥幾個親人。他留下族兄當理雅各家的管家,免去后顧之憂,然后喬裝改扮只身啟程,踏上跋涉一千一百公里,橫越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大地,前往南京的陸路之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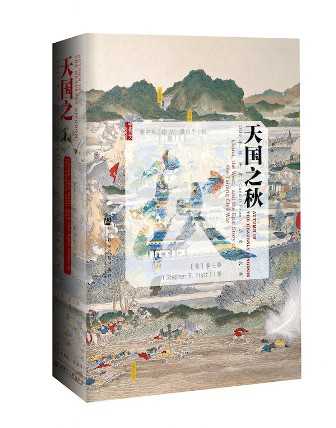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36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