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燈風雨:《讀書》書人書話精粹 一日一書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一燈風雨 副標題: 《讀書》書人書話精粹 作者: 《讀書》雜志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11-9 讀書人與讀書雜志相濡以沫、風雨同舟,一路行來已整三十年。精選結集三十年間雜志所刊涉及古今中西、談論書林掌故、普及版本知識、記敘書人書事的文章,既有助于文化史研究,又祈愿能以此見證和紀念這永不磨滅的書人情結。 不記得是誰曾經說過,“雪夜閉門讀禁書”,算是人生一樂。我想這是說得不錯的。要選一個下雪天,還得是晚上,外加關門上鎖。這樣的典型環境實在刻畫得好,沒有切身體會,怕是萬萬想不出的。 因此讀禁書也就被賦予了一重濃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內容實在豐富得很。 溯本窮源,發明了禁書的手段并嚴格付諸實施的還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這以后就有很長一段時間繼起無人。雖然提起“圖籍之厄”,燒書的事確曾不斷發生,但那大都是戰亂之間不問青紅皂白一把火通通燒光,與贏政的有目的、有綱領、有明確規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書還是不能同日而語。禁書與文字獄發生關系,較早也較著名的是宋代蘇軾的“烏臺詩獄”,清代的張秋水有《眉山詩案廣證》,就是專論此案的。張鑒的《冬青館集》里收有許多有關南明史事的論文,他生于嘉、道之間,正當清代中葉文字獄盛行之后,他的特別關心宋代詩人蘇東坡的命運,應該不是沒有緣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確是遙遙繼承了秦始皇的傳統,并后來居上的。論手段、論規模,也都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單是“禁毀書目”就先后修了幾次,成書若干冊。“禁書”成為一種通行的術語,也就從這時開始。不過有清一代,人們明明知道這一客觀存在,但口中、筆下卻誰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舊書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書字樣標在書目上,同時售價也就相應飛快地提高,終于在有些圖書館的目錄上也逐漸露面,做為審定“善本”的一種根據了。 為了習慣與方便,這里談到禁書,也姑且以此為限斷。 “禁書”雖然已經成為寶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過若干種。這就使我悟出,禁書者,不論是有著無上威權的封建統治頭子還是別的什么聰明人,也不論他們用盡了怎樣的心機,到頭來也終于是無效的。書是禁不絕的,因為有無數正直、公平的讀者的保護。 唐末的詞人韋莊,寫過一篇著名的長詩《秦婦吟》,詩中涉及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時的一些情況,有“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這樣的句子。韋莊自己后來覺得不大好,“公卿”們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頭目也不會喜歡的,因此就自行“抽毀”,從《浣花集》中刪去,還給家屬留下了禁令。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們都無法看到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終于從敦煌的石洞里發現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韋莊用心良苦的安排終于還是無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讀者喜歡它,作品還是被傳抄、保存下來了。 韋莊后來雖然貴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個個人,與能動用國家機器,在全國范圍內搜查禁毀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過皇帝又怎樣呢?事實證明,成績也并不理想。不過兩百年,清代禁毀的一些作品,也還是陸續出現了,并沒有禁得一干二凈。那原因也并不兩樣,也是得到了人民保護的結果。 近三十年前,我看到過從浙江紹興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陰祁氏澹生堂的藏書。這是一批由祁氏子孫深藏密鎖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與稿本。其中絕大部分是符合禁毀的條件的。經過清初的殘酷鎮壓,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慘禍,但還是冒著殺頭、滅族的風險保存下了這些著作。事實本身就是極為悲壯的。 這批書中有一部祁承鄴的《澹生堂集》,是崇禎刻本,在禁書目中是有著錄的。仔細一看,凡是集中“奴”、“虜”、“酋”……等字,都已用濃墨仔細地涂去了。同時我還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詩文鈔》,是祁氏子孫選抄待刻的稿本。原書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經過細密的修改。這些工作,想來都是在“雪夜閉門”的情況下進行的吧? 后來在蘇州又得到過一部刻于崇禎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錢栴撰《城守籌略》,則是南明政府官員為了抵御“北虜”南下而提出的作戰方略。奇怪的是這樣的書,禁書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見清初統治者花了如許氣力搜索、審查,工作也還是粗疏得很。原書卷一第一頁的書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馬虎,卷一以下都還好好地保留著書名和撰人。這就不能不使人揣測,藏書者要應付即將到來的大搜查,他所藏的這種違礙書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這樣馬虎地處理一下的吧?那時代可能就在錢栴被捕殺頭的前后。 我還有一部清初刻的《新樂府》,是吳炎、潘圣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這兩位都是在莊史之獄中被殺頭的。書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樣被撕去了。這樣的殘跡,好象意在提醒后來的讀者,書冊曾經歷過怎樣的命運,才終于保存下來,好象直到今天也還能隱隱嗅到血腥氣,以文獻論,是非常可貴的。 提到莊氏史獄,就不能不聯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冊稿本,《私史紀事》(這是經過修改的,那原題是《史禍紀事本末》)。這可是一冊很有價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驤,與陸麗京等三人都受到“莊史”的牽連。他們大概都曾為此書寫過序或曾列名參校。案發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聽審,后來總算放還了。這書詳細回憶記錄了起解途中,下獄審訊……以及如何打點營救,被釋還家的全過程。浙江離開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氣又是嚴冬,范驤等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的身份是逆案的“欽犯”,在押解兵丁的驅趕下趕路,后來到了刑部獄中,前后半年光景,過的是怎樣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動人的描繪。不只是文字獄的珍貴史料,作為社會風俗史,這也是難得的原始紀錄。尤其使我吃驚的是,這本回憶錄記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禍以后,彼此間曾經發生過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責難。在書冊的上端,有陸麗京的后人屬名“宗楷”的墨筆批注,都是駁斥范驤、為麗京辨誣的。他們被釋放歸以后,不用說,家都已破了,陸麗京的結末是離家出走,不知所終。看來與這種糾葛是不無關系的。封建統治者的殘酷迫害,在明遺民內部散布的矛盾……,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們深深的思索的。 《讀書堂詩集》,原刻的黑格紙,精抄,無疑是康熙中的清寫稿本,不題撰人也沒有分卷,后面還有許多空白頁,可證尚未編定。這是錢塘汪無己的詩集,無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種當然必禁而不見于禁書目的異書。無己名日棋,后改名景棋,是錢塘汪東山(霜)的兒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時的作品,后來他投入年(羹堯)幕,因《西征隨筆》一書獲罪,“律以大逆不道立決梟示”。《西征隨筆》的原件后來在故宮里發現,曾經有過新印本。作者是有才華的,筆記中有些紀事的篇章,其實是很好的短篇小說,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場丑行的紀事,我讀過以后始終未能發現獲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實汪景棋最大的過錯是成為年羹堯的親信。當時議政大臣所定年羹堯的“大逆罪”的第三條就是“汪景棋《西征隨筆》,見者發指。羹堯亦云曾經看過,視為泛常,不行參奏。”后來查嗣庭文字獄發,雍正在“上諭”中還念念不忘于景棋,“去年正法之汪景棋,文稿中有‘歷代年號論’,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繼承人乾隆之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媲美。他寫起“上諭”來,往往下筆萬言,反復聲說,終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霧中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權威”而后已。他運用種種奇怪的邏輯,驚人的捏造,將他所選中的對象一個個羅織入文網之中,又一個個殺掉,還要罪及妻孥親屬朋友和簡直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是清代文字獄事業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綱領、理論和實踐范例。可惜他的統治只沿續了十三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來最后完成。 據《永憲錄》記,汪景祺“伏誅”以后,妻子照例要“發黑龍江披甲人為奴”。“景棋之妻,巨室女也。遣發時,家人設危跳,欲其清波自盡。乃盤匍匐而渡。見者傷之。”簡單的幾句話,寫盡了一場陰森的鬧劇的陰冷凄涼的結末。 汪景棋的《讀書堂詩集》不過是少作,并無可觀,全書充斥著封建文士無聊生活的描繪,但書前卻有七八通詩序,作者都是當時的名家。除了朱彝尊,現在已經記不起還有誰了。我曾經查過這些作者的文集,發現沒有一篇序是保留下來的。這是難怪的。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卷二十,還保留了與景棋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詩。這是因為朱集刊成在景棋獲罪之先。但后印的,“日祺”兩字就已經削去了。出于同樣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喜春宮再建”詩,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廢太子以后,重印時也削去了。一個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況的變化,不同時期的印本就會有不同的面貌。這就是藏書家重視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斷重印時期的重要根據,也算是板本目錄之學的一點小小的知識。 上面隨意想到的幾個例子,幾乎無一不是清初文網的漏網之魚,這就說明,盡管皇帝雷厲風行,作為頭等政治任務來抓,效果還是很不理想的。當時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樞的文化官員實在值得同情,他們担著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讀著汗牛充棟的書本,又實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標準,他們的為難是可以想見的。手邊有四冊《無悶堂集》,閩張遠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庫未收、禁書目也沒有著錄,照我看也是一條漏網之魚。只要看卷中有許多地方都開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婦小傳》,照例這樣題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為篇中挖去了將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終于發現這實在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字。傳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節是, “甲寅之變,生靈涂炭。身污名辱,終于不免者,不獨女子也。女子為尤慘。楚蜀兩粵,不可勝數。以予所目擊耳聞者,獨浙閩江右。其死于鋒鏑、盜賊、饑餓、損傷、老弱廢疾者不具論。其姿容少好,騾車馬背輦之而北者,亦不具論。惟其棄載而鬻之者,維揚、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數計。市之者值不過數金,丑好老少,從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這里所說的是三藩之變,干出種種慘絕人寰的獸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軍。其在浙閩江右一帶作戰的則是討伐耿精忠的部隊。揚州、南京的人肉市場,竟與奴隸社會無異。不見舊記,是無從想象的。那挖去的幾句也不知道說的究竟是怎樣的事物。但僅此一節,難道就不該劈板禁毀、追究作者嗎?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輕輕地放過了。 乾隆肚皮里的標準,捉摸起來是困難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獄檔”,就可以約略知道那大概。不是連測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還有什么標準可言?其實這也正是一種標準。運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獨斷”,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萬萬不可忽視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聰明,早已發現這樣蠻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須轉變作風,采取新的積極措施。這就是《四庫全書》產生的背景。聚集群書,暗暗改削,寫成“正本”,頒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統一思想之實效。確是一條好計。但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發明創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見及此并付之實施了。入關以后首先為崇禎帝治喪;康熙下江南專程去孝陵致祭,他寫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還完好無恙。已死的明臣給以美謚,尚存的就用“博學鴻詞”的辦法招徠。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兩個側面。不懂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書的全部奧妙的。 禁書是一種歷史現象,非常丑惡的歷史現象。人類社會本來是沒有這種事物的,但后來出現了,在某些時候還頗行時。我相信,它終究是要消滅的。前些時曾經就此進行過一些討論。我自己是贊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的。當然,一時實行起來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頭腦的人,我想都應該贊成并努力創造條件把禁區徹底打破,并最終消滅這一丑惡歷史痕記的吧。那種一聽見要取消禁區就不舒服,惟恐這種寶貝事物斷種、失傳的精神狀態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農”嘗百草,在他心目中本來就沒有禁區。后來發現了毒藥,他也只是向人們提出警告,同時寫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設了“禁區”然后又用科學的方法打開了“禁區”。假使一開始“神農”就是滿眼“毒草”,不敢觸動,科學的本草學、藥物學是不可能出現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馬列主義曾是“禁區”里的“禁書”。多少人如饑似渴地“雪夜閉門”讀之,后來終于誕生了新中國。“禁”的后果往往卻是相反的宣傳,這是反動派所不及料的。這些事過去了還不算太久,大概我們總多少還有些印象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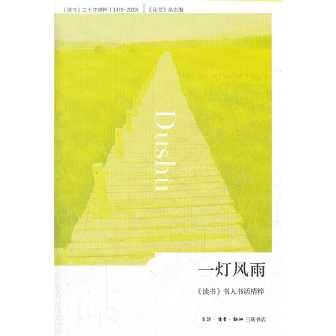

鳳凰讀書 《讀書》雜志 2015-08-23 08:55:35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