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重新注冊:詩人西川首部翻譯詩作自選集 一日一書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重新注冊:西川譯詩集 詩人西川首部翻譯詩作自選集,當代世界詩壇最新地圖 從1995年6月我去荷蘭參加第26屆鹿特丹國際詩歌節,至今由于文學原因我受邀去過的國家有二十來個,這其中印度我去過四次,英國也是四次,美國有六次,德國我去過不下十次。在印度、美國和德國我都有過廣泛的旅行:時常一個人在路上,看人,看古跡或名勝,看風景。但是,隨著我國際旅行經驗的增加和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在乎在漫長旅行的終點我會與什么人見面:我不僅需要看風景,我也需要遇到出色的頭腦。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說過:寫作對于作家最好的回報就是,一個被寫作訓練出來的頭腦能夠一眼就認出另一個被寫作訓練出來的頭腦。我想,古人“行萬里路”的說法里一定也包括了在萬里路途中與他人交談的構想。讓我感到幸運的是,這十幾、二十年來,我在世界各地遇到過一些優秀的頭腦、優秀的詩歌頭腦。他們帶給我啟發。我成為他們的讀者。 也是由于國際旅行經驗的增加和年齡的增長,我腦子里的“世界地圖”在不斷地調整,日益豐富和清晰起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我所認識的“國際”其實只是歐美。歐美到現在對我來說依然很重要,但恰恰是在歐美,我理解到所謂“世界”還包括東亞、中亞、南亞、小亞細亞、北非、南非、南美等許多地區——當然也少不了中國。一位南京姑娘曾經問我她是不是很“國際化”,我回答,對不起,你只是很“西化”,不是真正的“國際化”。我認為真正的國際化視野對于今日真正在乎文化創造力而不僅僅是生活方式的國人來說格外重要。“多元化”不只是一個詞,至少不只是一個由“西化”派生出來的詞,它也應該是一種切身感受。回望這些年我個人的閱讀經驗和關注點,我對自己的知識構成特別是詩歌知識構成,以及感受世界的方式所進行的調整,使我保持了“文學在路上”的精神狀態。我對東歐、亞洲、非洲文學的閱讀在某種程度上清洗了我從前對西方、俄羅斯、拉美文學的閱讀,而推動自己這種詩歌知識、詩歌意識清洗的是我的現實感和歷史感。當然,年齡的增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20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國際書展期間,我曾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歐亞研究所做過一個發言,談的就是何謂“世界地圖”。本譯詩集中收有一首美國詩人弗瑞斯特·甘德寫給我的詩《世界地圖》,他對“世界”有著與我相似的看法。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沒有人比翻譯家更能體會“世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所以,讀者會在這本譯詩集中讀到不少我轉譯自英語的非英美詩人的詩歌。很遺憾,我只能弄些英文。法文原是懂一點的,曾經可以大略讀一讀法國人寫的法國文學史,也能背幾首法文詩,但1985年大學畢業后我那趟七個月的遠足使我把自己本不牢靠的法文扔在了大西北和黃河兩岸。好在英文是一個好工具。英文告訴了我世界是什么樣的——它首先告訴我世界并不只是英語世界,而是多元的。即使是在當今英語國家,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移民作家其實相當活躍,他們的作品構成了英語寫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近年來我讀英語國家本土詩人的作品反倒不多,除非是朋友們的或朋友們推薦的作品(這其中美國作品我讀得更多一些)。此外,我還有幸在國內、國外參加過幾個翻譯工作坊,使我得以與外國詩人面對面地翻譯他們的作品。本書中有一些作品我就是這么翻的。例如2010年我曾去斯洛文尼亞參加過那里舉辦的“大語種—小語種詩歌翻譯工作坊”,我們的工作語言是英語。我在這次活動上的工作成果被收入了本書的第一部分“托爾斯泰花園的蘋果:1950—1970年代出生詩人十家二十三首”(但這一輯中也包括了其他零散翻譯)。 通過翻譯,我們得以走近這世界上說其他語言的人們。在最好的情況下,通過翻譯,我們各自的靈魂甚至可以相互進入;我們也可以通過認識他人來更好地認識自己。但翻譯行為本身從來沒能夠免于被質疑:會有感覺真理在握或神秘兮兮的人大聲告訴我,偉大的直覺和知覺可以超越翻譯。可是譯者是為交流做基礎工作的人,所以抱歉我們的認識就是這么腳踏實地的膚淺。會有很弗羅斯特的人說,詩歌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但據我的經驗,說這種話的人幾乎都是缺乏外語能力的。對弗羅斯特的看法(聽說有人查遍其全集也沒能找到這一說法),我想說,首先,弗羅斯特本人不做翻譯;其次,翻譯中丟掉的不外乎語言的音樂性、雙關語、特定語言中的特定思維、特殊語境中的特殊表達等,但所謂詩歌在今天所包括的東西比這要大得多,況且好的翻譯一定少不了對稱于原文的本語言再造;再況且,有些即使在翻譯中有所丟失的作品,似乎依然值得一讀。博爾赫斯就說過:好的文學作品能夠戰勝粗制濫造的翻譯。還有一種幾乎不可思議的情況:譯文勝過原作。我聽說德語的莎士比亞就比原文的莎士比亞還要出色。 翻譯行為會觸及翻譯的政治。而翻譯的政治必然觸及語言和文化的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以及性別、文化身份塑造等多方面的問題。不是只有國家主導的翻譯工程才會有政治內涵,任何翻譯都免不了政治,因為只要是有差異的地方就會有政治。在當下中國,翻譯的政治首先涉及翻譯的選擇,即翻譯誰不翻譯誰、翻譯什么不翻譯什么的問題。其次,翻譯行為還涉及誤讀—— 不是技術層面上的誤譯(誤譯的問題我后面會談到)。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也就是從一種文化語境到另一種文化語境。即使在縱跨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中國文學內部,我們也能夠感受到今人對古人的普遍的誤讀。比如古今共用的“詩”這個字: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們說到“詩”,那一定指的是《詩經》——楚辭雖然也是詩,但卻是不同于“詩”的詩。但是到漢朝人們說到“詩”的時候,就已經不非得指《詩經》了。而到今天,使用現代漢語的我們所說的“詩”已經既不一定是指《詩經》,也不一定是指漢詩、唐詩了,這也就是說,無論“孔門詩教”還是歷代詩話,都不能被不假思索地、百分百地拿來套用于當代詩歌,盡管當代詩歌割不斷與各類古詩的血緣聯系。再舉一個從外文到中文的例子:T.S.艾略特《荒原》的英文題目為The Waste Land,原本有垃圾場、廢墟的意思,但是在中文里,我們大多數人會傾向于把“荒原”理解成一個自然意象。類似的誤讀如果發生在政治、社會領域,其對歷史、文明、思想的影響得有多大,大家自己可以想象。 我想,翻譯不僅涉及翻譯的政治,它也可以作為文化、文學批評的手段來使用。比較英文的莎士比亞和翻入中文的莎士比亞,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文作為一個龐大的文化身體所積累的文化潛意識。比較中文的李白和翻入英文的李白,我們也許可以發現一個13世紀波斯神秘主義詩人杰拉魯丁·魯米意義上的李白。米沃什就曾這樣干,在他編選的世界詩選《明亮事物之書》中。 對翻譯的理論探討,在世界上,既不是大熱門,也不是冷門。本雅明、德里達、加亞特里·斯皮瓦克等大頭腦、大學者都有專門討論翻譯的文字。但我印象中從理論高度而不是經驗層面深入探討詩歌翻譯問題的工作好像還不多見。詩歌翻譯是“翻譯”,但又與一般人們所理解的“翻譯”有所區別。對比一下詩歌翻譯與小說翻譯,我們就會看到不同。小說家中自己也做翻譯的人不是沒有,但不多。而“詩人翻譯家”在全世界的詩人們中間并不鮮見。T.S.艾略特翻譯過圣-瓊·佩斯,瓦雷里翻譯過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翻譯過莎士比亞,保羅·策蘭翻譯過曼杰施塔姆,龐德翻譯過的東西就更多了:從意大利的卡瓦坎提到中國的李白、《詩經》《大學》《中庸》。我們國家20世紀以來,馮至、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鄭敏、陳敬容、綠原等等,甚至艾青,都是“詩人翻譯家”。為什么詩人中會有一些人成為“詩人翻譯家”,我一時琢磨不透,這其中一定蘊含著一些深刻的、與文明有關的神秘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說,“詩人翻譯家”的存在,極而言之,為翻譯這一行貢獻了一種翻譯的類型,即“詩人翻譯”,它有別于“學術翻譯”和“職業翻譯”。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幾種翻譯會相互滲透,也就是說,詩人翻譯也可以在準確性上向學術翻譯看齊,而學術翻譯也可以富含文學色彩。 ……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1995年我去荷蘭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的經歷。那是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詩歌節有一個翻譯項目:他們選出一位國際著名詩人,由與會的其他詩人在詩歌節期間將他/她的詩歌翻譯成各自的母語。那一年他們選中的是比利時詩人雨果·克勞斯。在英譯文的幫助下,我翻譯了克勞斯的兩首詩(翻譯過程中我曾與荷蘭漢學家柯雷和當時在荷蘭的多多進行過討論)。然后在克勞斯的專場上,由克勞斯朗誦弗萊芒語原文,我們朗誦各自的譯文。我譯的這兩首詩都收在了本書中。這一次為了寫克勞斯的簡介,我上網查維基百科,驚訝地發現,克勞斯已在2008年去世了。在那次詩歌節上我見到的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捷克詩人米羅斯拉夫·赫魯伯,如今也已過世。——生命一茬茬離開,而詩歌留下。 西川 2010.8.23/2014.2.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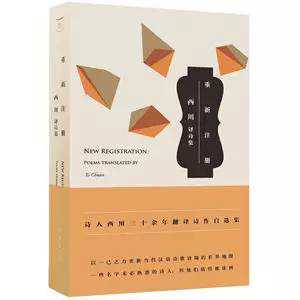

鳳凰讀書 西川 2015-08-23 08:55:4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