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海明威談寫作:戀愛時寫的最好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記者:在實際寫作過程中,你喜歡早晨的時間? 海明威:很喜歡。 海明威:在寫書或寫故事的時候,我早晨天一亮就動筆。沒有人打擾你,早晨涼爽,有時候冷,你開始工作一寫就暖和了。你讀一遍你寫好了的部分,因為你總是在你知道往下寫什么的時候停筆,你現在往下寫就是了。你寫到自己還有活力、知道下面怎樣寫的時候停筆,想辦法熬過一個晚上,第二天再去碰它。比方說,你早晨六點開始寫,可以寫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寫了。你停筆的時候,好像是空了,可同時你沒有空,你是滿的,這種感受好比你同你所愛的人做過愛之后一樣。什么事也不會讓你不高興,什么毛病也不會出,什么事也不要緊,只等第二天早晨你再動筆。難就難在你要熬到第二天早晨。 海明威:當然能。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得有訓練。這種習慣,我已經練成了。不練不成。 海明威:我每天總是把停筆之前的稿子修改一遍。全文完成之后,自然再改一遍。別人替你打了字之后,你又有機會改正和重寫,因為打字稿看得清楚。最后一次改稿是看校樣的時候。你得感謝有這么多次不同的修改機會。 海明威:這就看情況了。《永別了,武器》的結尾,就是最后一頁,我改寫了三十九次才算滿意。 海明威:尋找準確的字眼兒。 海明威:重讀的時候正是你得往下寫的時候,因為你知道你能在那兒激起活力來。活力總是有的。 海明威:當然有這種時候。但是,你只要在知道下面將發生什么的時候停筆,你就能往下寫。只要你能開個頭,問題就不大了。活力自會來的。 海明威:我不記得我一口氣用過二十支鉛筆。一天用七支二號鉛筆就不錯了。 海明威:哈瓦那的安娜波斯·孟多斯旅館是非常好的地方。這所農莊也是一個極好的地方,或者說以前是極好的地方。不過,我到哪兒都工作得很好。我是說我不論在什么環境下都能很好地工作。電話和有人來訪是破壞寫作的事情。 海明威:好一個問題。不過,我不妨試試得個滿分。只要別人不來打擾,隨你一個人寫去,你在任何時候都能寫作。或者,你狠一狠心便能做到。可是,你戀愛的時候肯定寫得最好。如果你也是這樣,我就不再發揮了。 海明威:如果錢來得太早,而你愛創作又愛享受生活,那么,要抵制這種誘惑可是需要很強的個性。創作一旦成了你的大毛病,給了你最大的愉快,只有死了才能了結。那時候經濟有了保障就幫了大忙,免得你担憂。担憂會破壞創作能力。身體壞同憂慮成比例,它產生憂慮,襲擊你的潛意識,破壞你的儲備。 海明威:不,我一直想當作家。 海明威:那年在馬德里我的腦子顯然不算正常。唯一可提的一點是我只是簡單地提到揚先生那本書和他關于外傷的文學理論。也許兩次腦震蕩和那年頭蓋骨骨折弄得我說話不負責任。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告訴過你,我相信想象可能是種族經驗遺傳的結果。在得了腦震蕩之后愉快、有趣的談話中,這種說法聽來是不錯的,不過我以為問題多少正在那里。這個問題等我下一次外傷使我腦子清楚之后再說,現在就談到這里。你同意嗎?我感謝你刪去我可能涉及到的親屬的名字。談話的樂趣在探究,但是許多東西以及一切不負責任的說法都不該寫下來。一寫下來,你就得負責。你說的時候也許是看看你信不信。關于你提那個問題,創傷的影響是十分不同的。沒有引起骨折的輕傷不要緊,有時候還給你信心。影響到骨頭,破壞神經的創傷對于作家是不利的,對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海明威:我說,他應該走出去上吊,因為他發現要寫得好真是難上加難。然后,他應該毫不留情大量刪節,在他的余生中盡力寫好。至少他可以從上吊的故事寫起。 海明威:這要看你所謂的妥協是什么意思。是受了污損的婦女的用語嗎?還是政治家的讓步?還是你愿意多付點錢給你的食品店老板或裁縫,可是想晚點付?是這種意義的妥協嗎?既能寫作又能教書的作家應該兩件事都能做到。許多有才能的作家證明他們能做到。我知道我做不到。不過我認為,教書生涯會中止與外界接觸的經驗,這就可能限制你對世界的了解。然而,了解越多,作家的責任越大,寫起來也越難。想寫出具有永恒價值的作品是一件全任性的工作,雖然實際寫起來一天只有幾個小時。作家好比一口井。有多少種井,就有多少種作家。關鍵是井里的水要好,最好是汲出的水有定量,不要一下子抽光,再等它滲滿。我看我是離題了,不過這個問題沒意思。 海明威:在《星報》工作的時候,你不得不練習去寫簡單的陳述句。這對任何人都有用。做報館工作對年輕作家沒有壞處,如果及時跳出,還有好處。這是最無聊的老生常談,我感到抱歉。但是,你既然問別人陳舊的問題,也容易得到陳舊的回答。 海明威:我不記得我這么寫過。但是,這話聽起來是夠愚蠢、夠粗暴的了,好像我是為了避免當場說謊才發表這一通明智的談話似的。我當然并不認為寫這類東西是自我毀滅,不過,寫新聞報道過了一定的程度對于一位嚴肅的創作家來說可能是一種日常的自我毀滅。 海明威:當然有價值。 海明威:自從喬伊斯寫《尤里西斯》之后,沒有感覺到這種影響。他的影響也不是直接的。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了解的那些字不許用,我們不得不為了一個單字而斗爭,他作品的影響在于他把一切都變了,我們有可能擺脫限制。 海明威:你同本行的人在一起,通常談論其他作家的作品。自己寫了什么,談得越少,這些作家就越好。喬伊斯是一位非常大的作家,他在寫什么,他只跟愚笨的人作些解釋。他所尊重的那些作家讀了他的作品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海明威:這個問題復雜些。你創作越深入,你越會孤獨。你的好朋友、老朋友多數去世了,其他的遷走了。你不常見得著他們,但是你在寫,等于同他們有來往,好像過去你們一起呆在咖啡館里一樣。你們之間互通信件,這些信寫得滑稽,高興起來寫得猥褻、不負責任,這同交談差不多。但是你更加孤獨,因為你必須工作,而且能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如果浪費時間,你會覺得你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海明威:對不起,我不善于做尸體解剖。對付這些事情,有文學界和非文學界的驗尸官。斯泰因小姐關于她對我的影響,寫得相當長而且相當不精確。她有必要這么做,因為她從一部名叫《太陽照常升起》的書里學到了寫對話。我很喜歡她,而且認為她學到了如何寫對話是件好事。在我看來,盡量向每個人學習,不管是活人還是死人,這并不新鮮,但是對她影響這么強烈,我是沒有想到的。她在其它方面已經寫得很好了。依茲拉對于自己真正了解的課題是非常精通的。這類談話,你聽了感到厭煩嗎?在這個私下談話中去揭三十五年前的隱私,我很討厭。這同你說出事情的全貌是不同的。那還有點價值。這里,說簡單點為好:我感謝斯泰因,我從她那里學到了字與字之間的抽象聯系,看我多喜歡她;我重申我對依茲拉作為大詩人和好朋友的忠誠;我非常關心麥克斯·潘金斯,我一直無法相信他是死了。我寫的東西,潘金斯從來沒叫我改過,除了去掉一些當時不能發表的字眼。去掉的地方留下空白,知道這些字眼的人明白空白的地方該是哪些字。對于我來說,他不是一個編輯。他是一位明智的朋友,極好的同伴。我喜歡他那種戴帽子的方式和嘴唇抽動那種奇怪的樣子。 海明威:馬克·吐溫、福樓拜、司湯達、巴哈、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安德魯·馬韋爾、約翰·多恩、莫泊桑、吉卜林的好作品、梭羅、馬利埃特船長、莎士比亞、莫扎特、吉瓦多、但丁、維吉爾、丁都萊多、希羅尼默斯·包士、布魯蓋爾、帕提尼、戈雅、喬陶、塞尚、梵高、高更、圣·胡安·德·拉·克魯茲、貢戈拉——全想起來要花一天的時間。這樣一來,好像我是要賣弄我所不具備的學問,而不是真的想回憶一切對我的生活和創作發生過影響的人。這倒不是一個陳腐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好,是個嚴肅的問題,必須憑良心回答。我把畫家放在里面,或者說開始這么做,是因為我從畫家身上學習寫作與從作家身上學習寫作同樣多。你要問這是怎么學的?那要另找一天時間同你解釋。我認為,一個作家從作曲家身上,從和聲學與對應法上學到東西是比較明顯的。 海明威:玩過大提琴。我母親讓我學了一整年音樂和對應法。她以為我有能力學音樂,哪知我一點才能也沒有。我們在室內組織小樂隊——有人來拉小提琴,我姐姐拉中音小提琴,母親彈鋼琴。我呢,大提琴,反正拉得世界上沒有比我更糟的了。當然,那一年我還出去干別的事。 海明威:讀吐溫的作品,你得隔兩、三年。你記得很清楚。我每年讀點莎士比亞,常常是《李爾王》。你讀了心里高興。 海明威:我總是在讀書,有多少讀多少。我給自己定量,所以總是有所儲備。 海明威:我有過夢魘,所以了解別人的夢魘。但是你不一定把它們寫下來。凡是你省略掉你所了解的東西,它們在作品中依然存在,它們的特質會顯示起來。如果一個作家省略掉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東西,它們在作品中就會像漏洞一樣顯示出來。 海明威:它們是我們學習去看、去聽、去想、去感覺或不去感覺以及去寫的一個部分。你的“活力”就在那口井里。誰也不知道它是由什么形成的,你自己更不知道。你只知道你是有“活力”呢,還是得等它恢復。 海明威:我想是存在的,因為批評家們不斷地找到了象征。對不起,我不喜歡談象征,也不喜歡別人問。寫了書、寫了故事,又不被別人要求去解釋,真是夠難的。這也搶了解釋者的工作。如果有五個、六個或者更多的好批評家不斷的在解釋,我為什么要去干擾他們呢?讀我寫的書是為了讀時的愉快。至于你從中發現了什么,那是你讀的時候的理解。 海明威:從這些話聽來,那位顧問編輯好像有點鉆牛角尖。誰說過杰克是“閹割過的,正像一頭閹牛”?他是在很不相通的情況下受的傷,他的睪丸是完好的,沒有受到損傷。因此,作為一個男子的正常感覺,他都具備,可是就是無法過性生活。他重要的一點在于:他傷在肉體,而不在心理,所以他不是閹割。 海明威:明智的問題既不叫你愉快,也不叫你惱火。不過,我仍然認為作家談論自己如何寫作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寫作是為了讀者用眼睛看,作者去解釋或者論說都是不必要的。你可以肯定,多讀幾遍比初讀一遍所得到的東西要多得多,這一點做到之后,叫作者去解釋或者叫他在他作品更艱難的國土上去當導游,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 海明威:我不相信吐溫拿《哈克貝利·芬》給聽眾“檢驗”過。如果他這么做,說不定他們讓刪掉好的東西,加進壞的東西。了解王爾德的人說他講得比寫得好。史蒂文斯也是講得比寫得好。他不論寫作還是說話,有時候叫人難以相信,我聽說他年紀大了之后許多故事都變了。如果瑟伯談得跟他寫得一樣好,他準是一個最了不起、最不叫人生厭的說故事人。我所認識的人中,談自己行業談得最好的是斗牛士胡安·貝爾蒙特,他的談話最令人愉快,也最邪惡。 海明威:那是長久以來一個令人生厭的問題,如果你花上兩天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你就會覺得不好意思,弄得無法寫作了。我可以說,業余愛好者所謂的風格就是不可避免的別扭,那來自你首次嘗試去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新的名著幾乎沒有一部與以前的名著相同。一開始,人們只見到別扭。后來不大看得出來了。當它們顯得那么別扭的時候,人們以為這別扭就是風格,于是許多人去模仿。這是令人遺憾的。 海明威:我想一想。《太陽照常升起》,我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七月二十一日動筆的。我妻子哈德萊和我一早去買看斗牛的票,那是七月二十四日開始的盛會。和我年齡相同的人個個寫過一部小說,可我寫一段還覺得挺困難。所以我在生日那一天開始寫,整個節日都在寫,早上在床上寫,到馬德里又寫。那里沒有節日盛會,我們訂了一間有桌子的房間,我就舒舒服服地伏在桌子上寫,旅館拐角在阿爾凡瑞茲街上有一處喝啤酒的地方,那地方涼快,我也去那兒寫。最后熱得寫不下去,我們就到漢達依去。在那片又大又長的美麗的沙灘上,有一家便宜的小旅館,我在那兒寫得很好,后來又到巴黎去,在圣母院路一一三號一家鋸木廠的樓上公寓里寫完初稿。從動筆那一天開始,一共寫了六個星期。我把初稿拿給小說家納桑·艾奇看,他那時說話口音很重,他說,“海姆,你說你寫了一部小說是什么意思?哈,一部小說。海姆,你是在坐旅游車吧。”我聽了納桑的話并不太灰心,改寫了這部小說,保留伏拉爾勃的什倫斯村陶柏旅館的旅途那部分(關于旅行釣魚和潘普洛納那部分)。你提到一天之內寫的幾篇小說,那是五月十六日在馬德里圣·依西德路斗牛場寫的。當時外面正下著雪。頭一篇我寫的是《殺人者》,這篇小說我以前寫過但失敗了。午餐以后,我上床暖和身子,寫了《今天是星期五》。那時候,我活力旺盛,我想我都快瘋了,我還有六篇小說要寫。因此,我穿上衣服,走到佛爾諾斯那家老斗牛士咖啡館去喝咖啡,接著回來寫《十個印第安人》。這使得我很不好受,我喝了點白蘭地就睡了。我忘了吃飯,有一個侍者給送來了一點鱈魚、一小塊牛排、炸土豆,還有一瓶巴耳德佩尼亞斯酒。開膳宿公寓的女主人總担心我吃不飽,所以派侍者來。我記得我當時正坐在床上邊吃邊喝巴耳德佩尼亞斯酒。那位侍者說他還要拿一瓶酒來。他說女主人問我是不是要寫一整夜。我說,不是,我想休息一下。侍者問,你為什么不再寫一篇。我說我只想寫一篇。他說,胡說,你能寫六篇。我說我明天試一試。他說你今天晚上就寫。你知道這老太婆干什么給你送吃的來?我說,我累啦。胡說,他說(他沒用“胡說”這個詞)。你寫三篇蹩腳小說就累啦。你翻譯一篇我聽聽。你由我去吧,我說。你不走我怎么寫呢?所以我坐了起來喝巴耳德佩尼亞斯酒,心想我頭一篇小說如果寫得如我期望的那么好,我該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海明威:有時候你知道故事是什么樣的。有時候你邊寫邊虛構,不知道最后寫成什么樣子。一切事物都在運動過程中變化。運動的變化產生故事。有時候,動得這么慢它好像不在動了。但總是有變化、有運動的。 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是我每天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大體上知道下面要發生什么事情。但每天寫的時候我虛構出小說中所發生的事情。 海明威:不,不是這樣。《非洲的青山》不是一部小說,寫這部書的意圖是想出一部極為真實的著作,看看如果真實地表現一個國土和一個月的活動,能不能與一部虛構的作品相比。我完成《非洲的青山》之后又寫了《乞力馬扎羅的雪》和《弗蘭西斯·麥考伯短暫的幸福生活》這兩個短篇。這些故事是我根據那次長時間游獵得到的知識和經驗虛構出來的,那次游獵中有一個月的經歷,我想把它寫成忠實的記實,那便是《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沒有的》和《過河入林》這兩部小說開始時都是作為短篇寫的。 海明威:我中斷嚴肅的工作來回答這些問題,這件事說明我多么愚蠢,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罚。我會受到懲罚的。你別担心。 海明威:從來沒有想過。我過去是想超過一些我認為確有價值的死去的作家。現在,長期以來我只想盡我的努力寫好。有時候我運氣好,寫得超過我能達到的水平。 海明威:那個情況我不了解。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只要他們頭腦好使就能堅持干下去。在你提到的那本書里,如果你查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是同一個沒有幽默感的奧地利人在吹噓美國文學,我當時要做別的事,他非要我談。我把當時談話的內容忠實地記了下來。不是想發表不朽的聲明。有相當一部分的看法是不錯的。 海明威:當然不是。有的取自現實生活。多數是根據對人的知識和了解的經驗之中虛構出來的。 海明威:如果我說明我有時是怎么變的,那么這就可以給誹謗罪律師當手冊了。 海明威:如果你是去描寫一個人,那就是平面的,好比一張照片,在我看來這就是失敗。如果你根據你所了解的經驗去塑造,那他該是立體的了。 海明威:這名單開起來就太長了。 海明威:有時候我感到難寫下去的時候,我讀讀自己的作品讓自己高興高興,于是我想到寫作總是困難的,有時候幾乎是辦不到的。 海明威:盡我力量取好。 海明威:不是的。我寫完一篇故事或者一本書之后開列一大串篇名或者書名——有時候多到一百個。然后開始劃掉,有時劃得一個也不剩。 記者:你有的篇名取自小說原文,例如《白象似的山峰》,也是這樣情況嗎? 海明威:是的。題名是后來想的。我在普魯尼爾遇見一位姑娘,我是在吃中飯之前到那兒吃牡蠣去的。我知道她已經打過一次胎。我走了過去,同她聊天,不是聊打胎這件事,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到這篇故事,連午餐都沒有吃,花了一個下午時間把它趕了出來。 海明威:那當然。作家不去觀察,就完蛋了。但是他不必有意識地去觀察,也不必去考慮將來如何使用。也許開始的時候是這種情況。但到了后來,他觀察到的東西進入了他所知、所見的大倉庫。你知道這一點也許有用:我總是試圖根據冰山的原理去寫作。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你刪去你所了解的任何東西,這只會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如果作家所略去的是他不了解的東西,那么他的小說就會出現漏洞。《老人與海》本來可以長達一千多頁,把村里每個人都寫進去,包括他們如何謀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其他作家這么寫了,寫得很出色很好。 在寫作中,你受制于他人已經取得的、令人滿意的成就。所以我想學著另辟途徑。第一,我試圖把一切不必要向讀者傳達的東西刪去,這樣他或她讀了什么之后,就會成為他或她的經驗的一部分,好像確實發生過似的。這件事做起來很難,我一直十分努力在做。反正,姑且不談怎么做到的,我這一次運氣好得令人難以相信,能夠完全把經驗傳達出來,并且使它成為沒有人傳達過的經驗。運氣好就好在我有一個好老頭兒和一個好孩子,近年來作家們已經忘記還有這種事情。還有,大海也同人一樣值得寫。這是我運氣好。我見過馬林魚的配偶,了解那個情況。所以我沒有寫。就在那一片水面上我看見過五十多頭抹香鯨的鯨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頭鯨魚,這頭鯨魚幾乎有六十英尺長,卻讓它逃走了。所以,我也沒有寫進小說里去。漁村里我所了解的一切,我都略去不寫。但我所了解的東西正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 海明威:這個奇聞不可靠。我從來沒有給堪薩斯《星報》寫過關于棒球賽的報道。阿契要回憶的是我一九二○年前后在芝加哥怎樣努力學習,怎樣探求使人產生情緒而又不被人注意的東西,例如一位棒球外野手扔掉手套而不回頭看一看手套落在哪里的那副樣子,一位拳擊手的平底運動鞋在場上發出吱吱扎扎的聲音,杰克·勃拉克本剛從監獄出來時發灰的膚色等等,我像畫家一樣加以素描。你見過勃拉克本那種奇怪的臉色,剃刀刮破的老傷疤,對不了解他歷史的人說謊話的方式。這些事情使你激動,寫故事是以后的事。 海明威:那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所謂親自了解,你是指性欲方面的了解?如果指的是那個,回答是肯定的。一個優秀作家是不會去描寫的。他進行創造,或者根據他親身了解和非親身了解的經驗進行虛構,有時候他似乎具備無法解釋的知識,這可能來自已經忘卻的種族或家庭的經驗。誰去教會信鴿那樣飛的?一頭斗牛的勇氣從何而來?一條獵狗的嗅覺又從何而來?我那次在馬德里談話時頭腦靠不住,現在我這是對那次談話內容的闡述,或者說是壓縮。 海明威:這要看什么經驗了。有一部分經驗,你從一開始就抱完全超脫的態度。另一部分經驗就非常復雜。作家應當隔多久才能去表現,我想這沒有什么規定。這要看他個人適應調整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或她的復原能力。對于一位訓練有素的作家來說,飛機著火、碰撞當然是一次寶貴的經驗。他很快學到一些重要的東西。至于對他有沒有用,決定于他能不能生存下來。生存,榮譽的生存,那個過時而又萬分重要的詞兒,對于作家來說始終是又困難又重要。活不下來的人常常更為人喜愛,因為人們看不見他們進行長期的、沉悶的、無情的、既不寬恕別人也不求別人寬恕的拼搏,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在死以前應該完成某件任務。那些死得(或離去)較早、較安逸的人們有一切理由惹人喜愛,是因為他們能為人們所理解,富于人性。失敗和偽裝巧妙的膽怯更富于人性,更為人所愛。 海明威:人人都有自己的良心,良心起作用該到什么程度,不應當有什么規定。對于一位關心政治的作家,你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如果他的作品要經久,你在讀他作品的時候得把其中的政治部分跳過去。許多所謂參予政治的作家們經常改變他們的政治觀點。這對于他們,對于他們的政治——文學評論,很富于刺激性。有時候他們甚至不得不改寫他們的政治觀點……而且是匆匆忙忙地改寫。也許作為一種追求快樂的形式,這也值得尊重吧。 海明威:不。沒有一點影響。我認為依茲拉應該釋放,應該允許他在意大利寫詩,條件是他保證今后不再參預任何政治。我能看到卡斯帕盡快入獄就很高興。大詩人未必當女生向導,未必當童子軍教練,也不一定要對青年發生極好的影響。舉幾個例子,魏爾倫、蘭波、雪萊、拜倫、波德萊爾、普魯斯特、紀德等人,不該禁閉起來,只是因為害怕他們的思想、舉止或者道德方面為當地的卡斯帕所模仿。我相信十年之后這一段文字要加一個注解才能說明卡斯帕是什么人。 海明威:說教是一個誤用的詞,而且用糟了。《午后之死》是一本有教益的書。 海明威:這是誰說的。這話太簡單了。說這話的人自己可能只有一種或兩種思想。 海明威:格林先生發表聲明的才能,我并不具備。在我看來,不可能對一書架小說、一群鷸鳥或者對一群鵝作一個概括。不過,我還是想概括一下。一個對正義與非正義沒有感覺的作家還不如為特殊學生去編學校年鑒,可以多賺點錢。再概括一條。你看,一目了然的事情是不那么難概括的。一位優秀的作家最主要的才能在于他是一位天生的、不怕震驚的檢察謊言的人。這是作家的雷達,一切大作家都具備。 海明威:為什么為那種事費腦筋?你根據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根據現存的事情,根據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根據這一切進行虛構,你創造出來的東西就不是表現,而是一種嶄新的東西,它比實際存在的真實的東西更為真實,你把它寫活了,如果寫得好,它就夠不朽。這就是為什么你要寫作,而不是因為你所意識到的別的原因。可是,一切沒有人意識到的原因又怎么樣呢? 轉自豆瓣
記者:你能不能談談這個過程?你什么時候工作?有沒有一張嚴格的時間表?
記者:你離開打字機的時候,你能不去思考你關于寫作的種種打算嗎?
記者:你重讀前一天已經寫好的部分時進不進行修改?還是等以后整部作品寫完之后再修改?
記者:你修改的程度能多大呢?
記者:這里有什么技巧問題沒有?你感到為難的是什么呢?
記者:你重讀的時候是不是激起你的“活力”?
記者:但是,有沒有根本沒有一點靈感的時候?
記者:桑頓·懷爾德談到一些記憶法,可以使作家繼續他每天的工作。他說你有一回告訴他,你削尖了二十支鉛筆。
記者:你發現最理想的寫作地方是哪兒?從你在那里寫的作品數量看,安姆波斯·孟多斯旅館一定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周圍的環境對寫作沒有多少影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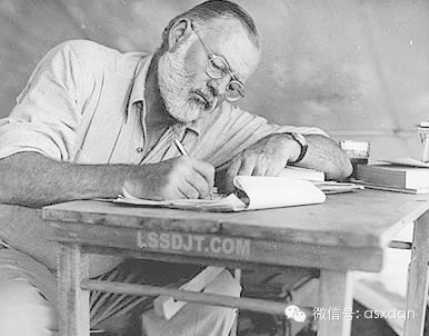
記者:要寫得好是不是必須情緒穩定?你跟我說過,你只有在戀愛的時候才寫得好。你可以再發揮一下嗎?
記者:經濟保障呢?對寫好作品有害嗎?
記者:你記得起你想當作家的確切時刻嗎?
記者:菲利普·揚在評論你的書里提出,你在一九一八年中了迫擊炮彈片、受了重傷,這場震驚對你當作家起了很大的影響。我記得你在馬德里簡單地提起過他的論著,認為沒多大道理,你還說,你認為藝術家的才能不是后天獲得的特征,根據門德爾的意思是先天固有的。
記者:對于想當作家的人來說,你認為最好的智力訓練是什么?
記者:你對于進入學術界的人有什么想法?大量作家到大學去教書,你是不是認為他們犧牲了文學事業,作了妥協?
記者:你說年輕作家做做新聞工作好不好?你在《堪薩斯市星報》受到的訓練對創作有沒有幫助?
記者:你在《大西洋兩岸評論》上寫道:寫新聞報道的唯一好處是收入多。你說,“你寫報道,是毀了你有價值的東西,你這是為了賺大錢。”你覺得寫這類東西是自我毀滅嗎?
記者:你覺得同其他作家相處對促進智力有沒有價值?
記者:你在寫作的時候,感沒感覺到自己受正在閱讀的書籍的影響?
記者:你能從作家身上學到關于寫作的東西嗎?例如,你昨天對我說,喬伊斯不能容忍談寫作。
記者:你最近好像避免同作家們在一起。為什么?
記者:有些人,你的同時代人,對作品的影響怎么樣?葛屈露德·斯泰國有沒有影響?還有依茲拉·龐德、麥克斯·潘金斯怎么樣?
記者:你說誰是你的文學前輩——你學到的東西最多的那些人?
記者:你玩過樂器嗎?
記者:你列的那些作家重不重讀?比如,吐溫。
記者:這么說來,讀書是一種經常性的消遣和樂趣了。
記者:我們還是回到你開列的那張名單上去,談談一位畫家,比如——希羅尼默斯·包士,怎么樣?他作品里那種夢魘般的象征好像同你自己的作品相去很遠。
記者:這是不是說,你熟悉了你開的名單上那些人的作品之后,你就能灌滿你剛才說的那口“井”?還是說,它們會有意識地幫助你提高寫作技巧?
記者:你承不承認你的小說中存在象征主義?
記者:在這個方面繼續問一個問題:有一位顧問編輯發現《太陽照常升起》中,在斗牛場登場人物和小說人物性格之間,他感覺到有一點相似。他指出這本書頭一句話說羅伯特·柯恩是一個拳擊手;后來,在開鐵欄時你描寫那頭公牛用它兩只角又挑又戳,活像一個拳擊手。那斗公牛見了一頭閹牛便被它吸引住,平息下來,無巧不巧,羅伯特·柯恩聽從杰克的話,而杰克是閹割過的,正像一頭閹牛。邁克一再挑逗柯恩,那位編輯便把邁克看成斗牛士。編輯的論點這樣開展下去,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用斗爭儀式的悲劇性結構來框架小說。
記者:這些追究技巧的問題確是叫人惱火。
記者:同這一點有關,我記得你也曾經告誡過,說作家談論自己正在寫作過程中的作品是危險的,可以說會“談沒了”。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有許多作家——我想起吐溫、王爾德、瑟伯、史蒂文斯——都先把他們寫的東西請聽眾檢驗,然后修改潤色。
記者:你能不能說一說,你經過多少精心的努力才形成你特殊的風格?
記者:你有一次在信中告訴我,在簡陋的環境中能寫成各種不同的小說,這種環境對作家是有益的。你能用這一點說明《殺人者》——你說過,這篇小說、《十個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是在一天之內寫成的——或許還有你頭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嗎?

記者:你寫短篇小說的時候腦子里構思完整到什么程度?主題、情節或者人物在寫的過程中變不變化?
記者:寫長篇小說是不是也如此?還是你先有一個總的計劃,然后嚴格遵守?
記者:《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沒有的》和《過河入林》是不是都是從短篇小說發展成長篇小說的?如果是的,那么這兩種體裁非常相似,作家不必完全改變寫法就能從一種體裁過渡到另一種體裁,是這樣嗎?
記者:你覺得從一種創作計劃轉變為另一種創作計劃是容易的嗎?還是你堅持去完成你所開始的寫作計劃?
記者:你想到自己是和別的作家在比高低嗎?
記者:你認為作家年齡大了以后寫作能力會不會衰退?你在《非洲的青山》中提到,美國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變成赫巴德老媽媽。
記者:我們還沒有討論過人物性格。你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不是毫無例外都取自現實生活?
記者:你能不能談一談把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變成虛構人物這個過程呢?
記者:你是不是也象 E·M·福斯特一樣,把“平面”人物與“立體”人物區別開來?
記者:你塑造的人物性格中,回想起來感到特別喜愛的是誰?
記者:那么,你重讀你自己作品的時候,并不感覺到要作些修改嗎?
記者:你怎么給你的人物取名字?
記者:你在寫故事的過程中,書名就想好了嗎?

記者:這么說,你不在寫作的時候,也經常在觀察,搜求可能有用的東西。
記者:阿契巴爾德·麥克里什說起過,有一種向讀者傳達經驗的方法,他說是你過去在《堪薩斯市星報》寫棒球賽時形成的。這很簡單,就用你保存在內心的細節去傳達經驗,使讀者意識到只有在下意識才有所感覺的東西,這樣便能達到點明整體的效果……
記者:不是親自了解的情形,你描寫過沒有?
記者:你覺得對一種經驗應該超脫到什么程度才能用小說形式去表現?比如說,你在非洲遇到的飛機碰撞事件?
記者:我能不能問一下:你認為作家關心他時代的社會政治問題應該限于什么程度?
記者:依茲拉·龐德對種族隔離主義者卡斯帕發生了影響,這是不是也影響了你,你還認為那位詩人應該從圣·伊麗莎白醫院釋放出來嗎?
記者:你能說你的作品里沒有說教的意向嗎?
記者:聽說一個作家在他通篇作品中只貫穿一個或兩個思想。你說你的作品反映一種或兩種思想嗎?
記者:好,也許這樣說更好一些:格拉姆·格林說過,一書架小說由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感情所支配,形成一種統一的系列。我相信,你自己也說過,偉大的創作出自對于不正義的感覺。一位小說家就是這樣——被某種緊迫的感覺所支配,你認為這是重要的嗎?
記者:最后,我問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你作為一位創作家,你認為你創作的藝術有什么作用?為什么要表現事實而不寫事實本身?
愛思想的青年 2015-08-23 08:46:2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