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周末一讀】劉震云:這個時代,不想看戲都不可能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他認為自己“正在成長為一個偉大作家”。去年他因《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但他對是否獲得這個獎有種無所謂的態度。有人認為這個獎至少可以為他的新書帶來更多的銷量,但他說:“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我給它帶來了什么呢”? 這個時代,不想看戲都不可能 作者 | 蕭三匝 劉震云坐地鐵前來,他有寶馬車,只是不常開,來得匆忙,頭發有些亂。 “拍個照片吧?” “好。” 他悉悉索索地翻隨身背的旅行包,三分鐘后,摸出來一把刨花梳,“我得梳梳頭”。 他以前小說的主角都是男的,在新書《我不是潘金蓮》里,著力寫了一個叫李雪蓮的女人。李雪蓮開始上訪生涯之前,辦了七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找了個美發館拾掇頭發。 劉震云的書首印量不斷攀升。當年《一地雞毛》的首印量是20萬,到《一句頂一萬句》是40萬,《潘金蓮》已經是50萬。而且《潘金蓮》上市才一個多月,已加印了10萬冊。按劉的預估,下本書首印就會是60萬、70萬。 長江文藝出版社是他相對固定的合作伙伴,他很信任該出版社的“金大姐”,“金大姐她會擺(題材),就這么簡單。” 金大姐就是知名出版人金麗紅。1989年底,金麗紅還在華藝出版社。彼時她策劃做一個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邀請王蒙和從維熙担綱主編。首批推出的13個人是張抗抗等如今60歲以上的作家。第二批就是劉震云、王朔、余華、蘇童、葉兆言等人,從維熙推薦的劉震云。這個榜單,爭議與反響都極大。 此后,劉震云的小說除了《一腔廢話》,都是金麗紅出的。金2003年到長江文藝出版社任副總編以后,把劉震云這個作者資源也帶了過來。 如今,劉震云與長江文藝的合作模式是:劉震云寫作前會告訴長江文藝他的計劃,寫完以后,長江文藝會提修改意見。 《潘金蓮》原來的結尾不是現在這樣的,書稿拿到長江文藝北京圖書中心以后,該中心總編輯安波舜就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劉震云修改時也參考了安的意見。《潘金蓮》的書稿其實在《一句頂一萬句》之后不久就已經寫完,但長江文藝準備拿《一句頂一萬句》申報去年的茅盾文學獎,安波舜感覺《潘金蓮》“寫得太好了,太有沖擊力了,我們要把它放出來的話,那劉老師的《一句頂一萬句》能否評上茅盾文學獎很難說”。出于出版周期等方面的考慮,安波舜建議《潘金蓮》今年出版,劉震云也同意了。此外,按劉震云的想法,新書書名就叫《嚴肅》,他提供了幾個備選方案,其中一個是《我不是潘金蓮》,但長江文藝上下都認為《我不是潘金蓮》比《嚴肅》強得多,劉震云雖然開始時有些顧慮,后來還是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見。 金麗紅與劉震云是一種“相互感激”的感情。因為與金麗紅合作默契,劉震云后來還把顧城的《英兒》和吳小莉的書推薦給金麗紅出版。 “劉老師人品特好,總想著讓我們也有利益。王朔不是說嘛,‘最好的關系是一種契約關系’?”金麗紅眼中,劉震云對自己的生活品質既有要求,又很自律的人。他住順義,離出版社遠,金麗紅每次要派司機去接他都不讓。在出版社時,到了飯點,金麗紅要請他,他都堅持到街邊小店吃炸醬面。 金麗紅覺得,劉震云之所以走得長遠,是因為他不忘本,著眼的都是“國家與民族的大問題,微言大義”。這么多年來,劉震云“在本質上從來沒有變過,變的只是寫法”:他年輕時的作品如《一地雞毛》是典型的白描式現實主義;《故鄉》系列有意識流和浪漫主義的色彩;從《手機》、《我叫劉躍進》開始,到《一句頂一萬句》、《潘金蓮》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 《潘金蓮》講了個簡單的故事。 劉震云喜歡軸人,女主角李雪蓮就是一個軸人。她為了超生一個孩子,和丈夫秦玉河辦了假離婚。哪曉得孩子生了,秦玉河卻弄假成真,和別的女人迅速結了婚。為了給自己的背叛找到借口,秦玉河還反誣她是潘金蓮,“天知道這個二胎是誰的”?李雪蓮于是上訪,訴求很簡單:“上面”要判定她當初和秦玉河的離婚是假的,他們得復婚,復婚以后她再和秦玉河離婚。 接訪的人基本上都很嚴肅地對待這案子,不過離婚證是真的,他們又怎么能隨便改判呢?李雪蓮要讓別人相信她不是潘金蓮,從縣法院上訪到縣政府,到市政府,一直到兩會期間的人民大會堂。既然領導都管不了她的事,她后來干脆把每一級領導都告了。一個芝麻大的事最后驚動了國家領導人,領導人一發火,沒想到下面的人把與這案子有關的省長、市長、縣長、縣法院院長、縣法院專職委員、縣法院審判員一干人等都給辦了。 事情搞得如此驚天動地,李雪蓮就成了新任領導的祖宗。她不知疲倦地上訪,領導們就只能不知疲倦地截訪——截訪史簡直就是領導干部對一個草民的求情史。 正文說的是下臺縣長史為民的故事。 史為民下臺后,在縣城開了個小飯店“又一村”貼補家用,專賣“連骨熟肉”。這一年,老史的姨媽去世,他千里奔喪,往回走的時候正逢春運。他本打算慢慢安排歸期,但在北京時接到了牌友老布的電話,叫他趕緊回去打麻將。麻將對他來說本來就重要,更重要的是老布告訴他牌友老解得了腦瘤,不知是良性還是惡性,年后就要開刀,所以這最后的一次麻將對老解來說很重要。老史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趕緊趕回家。但春運期間買票難,他只有干著急。這一瞬間他大概想到了李雪蓮,就在包里掏出了一張紙,上書幾個大字:我要申冤。四個警察在一分鐘內摁倒了老史,他被協警遣送回了老家,還沒買票。回到家后警察發現他竟然是假上訪,問他行為動機,他的回答是:“玩呢”。 一個人逐級上訪為了討個說法,一個人為了陪牌友打最后一次麻將冒充上訪者,前者還是后者下臺的原因。 按劉震云的話說,他的小說讓人看后會脫口而出一句評價——“這孫子!”他對這個評價很受用。 但他不承認自己幽默。“我的語言不幽默。語言幽默是個特別淺的層次,說相聲沒問題,演小品沒問題,但如果在文學作品中局限于一種語言幽默,挺討厭的,那你改說相聲就完了。真正的幽默是第二層——事兒和事兒之間的幽默,比如《潘金蓮》第一章第一節李雪蓮去找王公道,攀了半天遠親,是為了上訪;第二章第一節王公道找李雪蓮,也是攀了半天遠親,是為了不讓她上訪。好多人看了樂得肚子疼。但事兒和事兒之間的幽默,還不是幽默最高的層面,最高的層面是你后面的認識。為什么這事兒表面那么莊嚴,背后這么荒謬?荒誕感不是靠一個人巧舌如簧說出來的,真正的幽默是沒說出來的東西。小說中的認識,一定跟生活中的認識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這個小說才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劉震云的看法跟所有人的看法是一樣的,那所有人為什么要看劉震云呢?” “這是一個喜劇時代。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戲都不可能。”劉感嘆,比如,在中國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領導在臺上講話,手里拿一疊文件在讀,下面的人坐著聽,拿的是同一文件,他在不停地記。“他念的跟你手里的一樣,你記什么呢?我是領導我就急了,難道我這個文件還不夠嗎?你還要再寫點什么發揮一下嗎?如果你沒發揮,你記的是什么?你為什么不集中精力聽我念呢?如果你記的跟我念的是一樣的話,那你是騙誰呢?你騙臺上的領導,那你不把領導當傻逼了嗎?我是傻逼能當官比你大嗎?”生活已然如此幽默,他只需要做“生活的搬運工”就行了。“搬運工需要特別老實,機場一搬運工,卸下來一行李,從里面拿出點東西裝你自己包里,這不行啊。另外,你也不能往顧客包里擱東西,擱大麻和搖頭丸,一樣進監獄。” 搬運很簡單,不簡單的是怎么碼放。劉震云現在看別人的作品,就看人家碼放素材的水平,一看馬上就知道他行不行。“你把好幾個八爪章魚放到一塊兒,它們之間會編織出一種不同的形象。” 碼放能力其實就是結構能力,從這個角度看《潘金蓮》,劉震云沒有明說的話立馬噼里啪啦蹦出紙面:縣長史為民就跟李雪蓮見過一面,對話不會超過十句話,為什么李雪蓮能讓他從一個縣長變成飯店小老板?整個故事中,官員們并無過錯,他們很嚴肅地對待李雪蓮的上訪,為什么反倒是有錯的李雪蓮給他們帶來了霉運?國家領導人雖然發了火,但并沒有指示讓一干官員或停止升遷,或即刻下臺,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的仕途發生了巨變? 這說的已經不是上訪的事了。 劉震云說,這個國家什么都不缺,就缺思想,缺遠見,所以會三天兩頭修路,會三天兩頭塌橋,官當到了相當高的級別還貪錢。他希望從小說家的視角關注現實,而故事不過是思想的載體。在他看來,把故事、人物寫得栩栩如生,不過是初級作家干的事兒。況且,“真正創造故事的是政治家”。 在《潘金蓮》首發式上,評論家雷達說,《潘金蓮》寫的是“中國官員的生態,包含著極為尖銳的對現實的干預,對人民疾苦的呼吁。” 最早概括出劉震云的文學觀的大概是摩羅,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他說,他在1997年寫過一篇研究劉震云的專題論文,標題就是《喜劇時代的批評家》。在他1998年的成名作《恥辱者手記》里,就曾斷定劉震云是當代中國文壇不可多得的大作家。“看一個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是看他與他的民族、他的時代的精神生活聯系得有多深,或者說揭示得有多深。” “我可是北大畢業的。”劉震云說,他的文學觀與北大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在北大念書的時候,吳組緗教授曾告訴他趙樹理與魯迅的區別:兩人都寫鄉村,但趙樹理是通過村莊看世界,而魯迅是通過世界看村莊,所以立意高下有別。為了通過世界看村莊,他認真讀過康德、尼采、亞里士多德、黑格爾、迪卡爾、胡塞爾、維特根斯坦,到現在他都覺得這些哲學家“很偉大”。他們影響了他,一個顯見的例證是,西方當代哲學曾經是語言哲學的天下,而劉震云幾年前就曾告訴本刊記者,他的“一字頭”系列小說(如《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等)探討的就是人與語言的關系。 有人為中國現當代作家搞了一個排名,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錢鐘書之后就是劉震云。 “哎呦!非要跟他幾個排一塊?其實我心目中不是這么排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李清照、柳永、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蒲松齡、魯迅、劉震云,(這么排)不行嗎?”聽說這個排名后,他如此回答。也不知是為了找補還是揶揄,他接下來一句是:“當然,林語堂也不錯,林語堂英語挺好”。 他認為自己“正在成長為一個偉大作家”。去年他因《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茅盾文學獎,但他對是否獲得這個獎有種無所謂的態度。有人認為這個獎至少可以為他的新書帶來更多的銷量,但他說:“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我給它帶來了什么呢”? 不過他還是那個天天買菜、有事沒事都往河南老家跑的中年男人,他的狂有收束,他清楚自己的邊界。 中國作家網主編劉颋長期關注劉震云的創作變遷,在她看來,劉最近幾部作品最大的變化是,作為作家的劉震云正在從作品中隱身。 劉震云很高興有人能看出他的變化。他說,變化是從《一句頂一萬句》開始的,那時他認識到了作者的見識永遠是偏頗的、主觀的,最主觀的東西是最站不住的,他必須把主觀還原成客觀,所以作家不應是一個訴說者,而應是傾聽者。 “作家想一部比一部寫得牛逼,我覺得這特別膚淺與自私,一定是作品往前走,作者往后退。我越往后退,覺得眼前越開闊。過去你會看到劉震云帶著一幫人在往前走,現在你會發現,書里的人物在哇哇地往前走,作者可能在這個隊伍里正東張西望跟人聊天呢。我覺得這是作家最好的狀態。有人出于對家庭的反感,說我爹不是東西,我跟他吵架了,動刀子了,出走了,我覺得這不是作家該扮演的角色。有些作家開始評論社會現象,跟現實的事貼得特別緊,那就不是說往前走的問題了,他已經跳過來了。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家特別多,這樣的作家一定特別膚淺。”劉震云說,他不會寫雜文、時評一類的文章,不會做那種讓他討厭的、通常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我的話基本上在小說里都說完了”。 他甚至不愿意嘗試散文、詩歌寫作,理由是“如果你沒有深入地研究,想散文寫的跟韓愈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散文,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詩歌?這么多年你都不跟李白、杜甫打個電話,怎么能一下就寫好?就把小說寫好,對我這樣一個人來講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他不拒絕導演把他的作品改編成電影,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他說:“影視讓我的作品知名度呈幾何級數擴展,讓我拿到第二次稿費。錢對作家不是最重要,但也是相當重要的,可以維護他的自尊。如果是在寒酸狀態下,寫出的作品也是寒酸的。” “現在有沒有導演想改編《潘金蓮》的意向?” “會有,但是我覺得困難會很大。”劉震云暫停幾秒鐘后,“但是,一定有,關鍵問題是能不能碰到個偉大的導演,一個偉大的導演一定能把它拍成特別好的電影,因為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說”。 本文選自蕭三匝《劉震云:這個時代,不想看戲都不可能》,轉載請注明來源。
“如今嚴肅文學(作品)能賣5萬冊就相當不錯了,一般都只能賣5千冊、一兩萬冊。我覺得,在中國,像我這樣(暢銷)的作家肯定是不多的。”他有些小得意。生活本身就挺幽默的,你不想看戲都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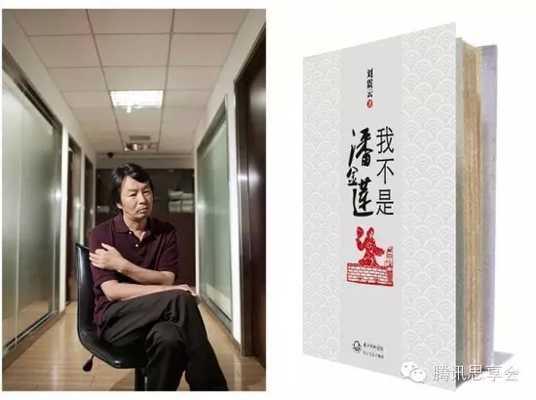
小說到此結尾,劉震云就不是劉震云了。他用了267頁鋪陳李雪蓮的上訪史,但這267頁只是整本小說的序言。而正文,只有16頁,三四千字。這種結構贏得了與他熟識多年的評論家張頤武的一頓猛夸:“我建議正文拿去得魯迅文學獎(魯獎主要獎勵短片小說——記者注),把前面的拿去得茅盾文學獎,。”正在成長為一個偉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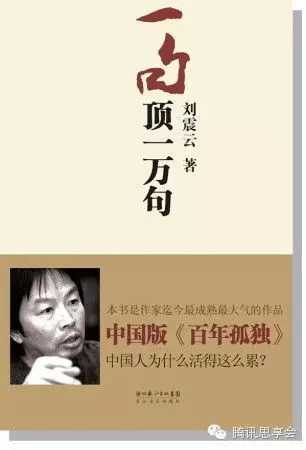
劉震云有些狂。
再說說電影《溫故1942》。多年以來,在與馮小剛合作的多部影片里,劉震云都是編劇,他眼中自己不是編劇,而他改編的只是自己的小說。“今天的飯是在你們家做,也是在你們家吃,跟飯館可不一樣,所以你就不能叫廚師,專門在飯館做飯才能叫廚師。另外,原來你老蒸蛋羹吃,但今天說能不能變個雞蛋炒西紅柿?我說行啊,這就是我與編劇的關系。如果有導演說讓我改編個別人的作品,我馬上會問:‘你誰啊’?”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8:12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