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思享】人從哪里來,往何處去?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如果來讓我們做一個具有倫理意義的選擇:如果人類的起源需要有一個終極的假設,那么我們是選擇猴子還是選擇上帝?回答不言而喻,當然選擇上帝。 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作者 | 劉剛 歷史學里,有一種史觀,叫做“地理決定論”,曾經很流行。然而,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它卻過時了。因為人類的生存狀態,已不再受制于相對封閉的地理空間,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不具有決定性了,信息化生存超越了地理性的歷史空間。 直到20世紀以前,地理因素對人類文明的影響都舉足輕重,雖然其影響不一定是根本性的或決定性的,但其重要性則不容忽視。當然,地理因素再怎么重要,也比不過人自身。 雖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物”,但人生而自由,卻不是由一方水土養出來的,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不管在地球的哪一方水土,所有人都要直立行走,不管受怎樣的地理因素影響,幾乎沒有人不會自發地使用石頭,在決定文明的基本面上,一方水土的作用,理應排在人的本質之后。 可不同的水土,還是會產生不同的文化。文化類型,一般來說,跟產生它的地理環境有關,人的本質雖然決定文明的基本面,但文化還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征。 例如語言,人類無不使用語言,這是文明的基本面,但地域不同,人的語言也不同,則屬于文化范疇。地理環境的制約性,更多地反映在文化的類型方面,而非體現于文明的基本面。還有,人的植物性使人類從采集走向農耕,人的動物性使人類從狩獵走向游牧,這些都是文明的基本面,但不同地域之人,究竟以農耕為主,還是以游牧為主,則取決于地理環境,并由此形成與之相應的文化類型。 如果要談文化,那就必須從文化的地理環境開始;要談原始文化,理所當然,就要從原始人生存和發展的地理環境開始。受了進化論的影響,一提起原始人就以為是類人猿,其實“原始人”,并非從猿進化到人過程中的類人猿,而應該是那些跟文明起源有關的人。 這些人從哪里來,往何處去?他們當年應對氣候變化的選擇,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我們的命運。確切地說,他們來自東非大裂谷,地球上那條最大的斷裂帶,看似傷疤,一條碩大的“刀痕”呈三角形,位于三點之間,南點莫桑比克入海口,西北點位于蘇丹約旦河,北點可入死海。裂谷縱貫南北,將肯尼亞裂開,恰與橫亙的赤道相交,故有人稱“東非十字架”,似乎隱含了人類起源的密碼。 據說,三百萬年前,就有類人猿出現,那時,冰原正以北極為中心往陸地擴展,每數萬年為一周,地球進入冰河期,降雨驟減,森林變草原,采摘變狩獵,猿人瀕危也!從150萬年前開始,走出大裂谷,轉往海岸,獲取海洋食物。他們走過紅海,走向歐亞大陸,不止一次上演著直立人的“出非洲記”,并在歐亞大陸上留下了他們遷徙的痕跡。其中有一支,約于40余萬年前后,來到了歐洲,1907年,考古人在德國海德堡附近毛爾距地表24.5米的砂層中發現了他們,稱之為“海德堡人”,乃尼安德特人祖先。入亞兩支,為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從遺存來看,爪哇猿人寥寥無幾,而北京猿人則可謂大觀,可以說世界各地發現的那一時期的遺物都不及北京猿人多。可他們卻在20萬年前突然消失了。再次出現在周口店龍骨山一帶的北京人是山頂洞人,這些人有可能是人類原始的“北漂”一族。關于山頂洞人的種族,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對出土的三件頭骨作了識別,指出,老年男性頭骨的測量指數很像歐洲的克羅馬農人,據形態觀察又可確定為蒙古人種,而兩件女性頭骨,一為美拉尼西亞人類型,另一為愛斯基摩人類型。他們從世界各地來,共處一洞,同居一穴,組成了一個新的血緣族群——北京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們來自北京猿人。 但有可能提供證據的,倒是從大裂谷中兩次出走的新人類。第一次,是在12萬年前的一個間冰期的溫暖時代,新人類經由西奈半島進入新月沃土區,卻遭遇了9萬年前的那一次急遽寒冷,沃土沙漠化,使得這支新人類再度消失,究竟是滅絕了,還是回歸了,抑或早已四海為家,遍地開花?須知新人類擁有兩三萬年的時間,什么人間奇跡都有可能發生,從天堂到地獄,從地域到天堂,可以有好幾個來回,故滅絕一說似不可輕信,也許他們之中也有人來到了北京參與了山頂洞人?暫留此一問。證據較為確鑿的,是8萬年前第二次出非洲的新新人類,分子生物學和人類遺傳學證明,他們就是當今世界所有人類的祖先,最有力的證據便是基因——母系血緣的“粒線體夏娃”和父系血緣的“Y染色體亞當”。 基因便是證據,雖非盡善,若無更好的證據,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來自基因的判斷。用基因技術溯源,指出人類從哪里來,比用比較解剖學的類比所作的猜想式的猴子變人要靠譜得多。在傳統進化論中,盡管人類放下了萬物之靈的高貴身段,愿意屈尊為來歷不明的猴子的子孫,決然以科學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直奔真理而去,結果,反而遠離了人的本質。基因分析,使人類從此告別猴子,就像柏拉圖的靈魂、亞里士多德的最高形式和牛頓的“第一推動力”,順著思想的邏輯,我們仿佛又通往了上帝。 因為科學的價值在于實驗和實證,如非實驗和實證,而又必須以假設和猜想來解釋,那就沒有必要非得強調所謂的“科學性”,因為科學在猜想方面并不真正具有優勢,多半是科學的文學化,反倒不如哲學的詩意化和宗教的神學化。我們之于后者,并不要求它們必須拿出證據來,它們可以是主觀的表達和主體的選擇,而科學則必須拿出證據來,必須以實驗和實證來表達。如果來讓我們做一個具有倫理意義的選擇:如果人類的起源需要有一個終極的假設,那么我們是選擇猴子還是選擇上帝?回答不言而喻,當然選擇上帝。作為一種價值取向,選擇上帝,使人更接近萬物之靈的本質,更能體現人是萬物尺度的價值,更何況基因檢測已證偽了人類起源于猴子。 “原始”是什么,是蒙昧嗎?啟蒙主義者歷來這么認為。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所謂“原始”,首先跟本原有關,其次跟創世有關,而原始人,就是直立本原,創造世界的人。 自從拿起石頭,人類就站立起來,在蒼茫大地上開始自由行走,追逐獵物,從日出到日落,從天亮到天黑,追隨日月星辰,跟著人類的宿命走。人類拋出石頭,那一條美麗的拋物線,就能擊倒獵物,連豺狼虎豹也要逃走……蒼穹之下,人類終于站穩了,人類可以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了。 人類站立之初,想必成了猛獸的笑料,剛站起來的人類,不僅喪失了奔跑的速度,還搖搖晃晃,跌跌撞撞,成了猛獸最容易捕捉的獵物。可人還是站起來了!無依無靠,直立行走。想想看,人類下了多么大的賭注?人一站立起來,就抱定了要么從萬物中消失,要么成為萬物的尺度。 人的命運使他天生就不愿意在自然循環里被萬物同化掉,不愿意像所有動物那樣在大地上低著頭,更不愿意像所有植物那樣把根扎在地里一動不動沒有行走的愿望和自由。人的選擇是,既要像大樹那樣向著天空直立起來,又要保留自己在大地上追逐獵物盡情奔跑的自由。當猛獸撲向剛學走路的人類時,人類很可能就像幼兒天真爛漫的蹣跚行走一樣,那初步行走的姿態有多么危險和可笑,可人類居然就這么走出來了。 不知道人類為了直立行走究竟做了多大的犧牲,不過可以試想一下,也許別的動物也曾嘗試過直立行走,可一旦猛獸追來,為了逃命,那動物又改回四條腿了。究竟是什么使人類在生死關頭還能堅持直立行走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自由,生而自由,那是要成為萬物之靈的人而不能沒有的自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從人類直立時就已開始,人獸之別,在于人生而自由。 自從人類拿起了石頭,石頭就被人賦予了自由,人與動物之間,從此就改變了時空尺度,從以奔跑的腿為尺度,到以飛石為尺度,腿的尺度變成了人的尺度,人生而自由應該是萬物的尺度。 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里說:“如果人是萬物的尺度,那么辯證法是無用的。”對于手里拿著石頭的直立人來說,辯證法的確是無用的,你讓他們來選擇,他們寧可選擇普羅泰戈拉在《論真理》中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 辯證法是有用的,這還用解釋嗎?但它有適用范圍,要有邊界,而且有必要加以說明。辯證法適用于語言和思辨領域,因而有對話辯證法和思維辯證法,超出這些范圍,也就沒什么用了。試想一下,那些生而自由的直立人,想一想他們追逐動物時那種萬物之靈的姿態——矯健如龍,還需要辯證法嗎? 幾乎所有的動物都不知道有萬物存在,因為動物的存在方式都是被自然一次性給定的,只能在固定的自然循環中感知與其食物鏈相關的他物存在,唯有人能超越自然循環而感知萬物存在。因此,讓我們暫時放下柏拉圖,跟著普羅泰戈拉再說一遍:“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萬物之中,惟人豪邁,除了“我思故我在”,還有“人在萬物在”。 古希臘哲人有句名言,叫做“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可那是理性時代的說法,而在新石器時代,人類理性未萌,但靈性已開,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靈性為自然立法,靈的憲法就是神話。神話世界是靈的世界。靈賦予人的精神追求,可以為神,為英雄;靈附在物上,可以為仁獸,為嘉木。 今人常犯一個錯誤,就是常常用理性去評價靈性,結果,往往就是以理性貶低靈性,將人類邁向文明的第一步,看作是人之初,而未能真正意識到這正是人成其所以為人的決定性一步。邁出這一步,就意味著人從自然界里走出來了。迄今為止,人類所有的進步都是在文明體系內取得的,只有這開啟文明的第一步是在文明以外邁出的。那時,人生而自由,束縛人的制度性枷鎖尚未形成。但是,再后來,當直立行走,被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要求而被體制化以后,人從此就在體制內了,雖然還在直立行走,卻忘了生而自由,成為群眾一部分,異化為民了。體制化的王和帝,也不再是個體,他們成為統治者,化為王制或帝制,當體制化成了人的習慣后,人反而像動物一樣在權威面前匍匐、下跪和低頭。 普羅米修斯是古希臘神話中象征自由意志和悲憫心的神,而凱撒則是古羅馬歷史上最具有權力意志象征的統治者。 20世紀最有影響的俄羅斯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說,普羅米修斯是自由人和解放者,同時也是暴君和奴隸。他這樣一說,就說到了革命者的本質,因為革命包含了這一切。暴君和奴隸,看似天淵之別,瞥如云泥,其根本是一致的,它們都從自由人轉化而來,都是以革命為契機,都基于生命本能中與生俱來的權力意志的得與失。 普羅米修斯用火,用從神的世界里偷來的天火,也許就是從緊握在眾神之神宙斯手里竊取的閃電,那擁有最大能量體現最高權力的全能之火,照亮了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光以革命的方式實踐人自己,還要以革命理想召喚并推動自由意志轉向權力意志,進而實現其統治。 征服與革命,是人的權力意志實現其統治的兩種基本方式。如果說征服是權力意志的惡性膨脹,那么革命則多少還能算是權力意志的合理追求,但它們都不能給人自身帶來真正的自由。 神話傳說中的革命者普羅米修斯不能,歷史活動中的征服者凱撒也不能。別爾嘉耶夫說,凱撒也是奴隸,是世界化的權力意志的和大眾的奴隸。奴隸們簇擁凱撒登上權力的峰巔,可別忘了,奴隸們還可以推翻他,推翻一切所謂的“凱撒”。仿佛命運如此,凱撒只能受限于厄運,一切對他都是既定,他不能成為自己,不能限制自己,在自己的去路上,他永遠得走下去,一直走到喪鐘敲響的時刻。 普羅米修斯式的自由,與生俱來,那是未經道德應允而且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是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自由,是可以偷盜與反叛的自由,諸神已慣于不論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真假,只管成敗。普羅米修斯的卓越在于,他還是個關注人類命運的神,為此,他不惜發動革命,為之獻身,給人類樹立了一個革命者的榜樣,馬克思稱他是“哲學的日歷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如此贊美,顯然是把革命當作了最高的目的。革命取代自由,手段僭越目的,高尚往往是異化的開始。 人因其生而自由而天然的具有革命性,這本無可厚非。不過,人因自由而革命,但革命卻不能保障人自由,人為自由而斗爭最終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對此我們應有所警惕。即使斗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也只能確保勝利者成為統治者而難以確保勝利者因勝利而自由,因為自由從根本上是一種個體人格,它不僅遠離奴隸狀態,也遠離了統治者。統治者沒有個體人格,奴隸也沒有,唯自由人有個體人格,即便整個世界都想奴役它,摧毀它,它還是要說“凱撒歸凱撒,我歸我,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凱撒式的自由是統治者的自由,那是一種將個體自由意志轉化為權力意志的自由,將一己權力意志轉化為帝國意志的自由。這樣轉化,在我們看來,就是自我奴役,一旦走向權力,便是通往奴役的開始。如果說普羅米修斯的自由只是有可能通往奴役,那么凱撒式的自由則必然通往奴役。普羅米修斯被釘在巖石上讓鷹來啄食,那不是被奴役,而是為自由而斗爭,是革命必須的代價,普羅米修斯最終能與宙斯和解,有可能為神和人的和解找到另外一條出路,那就是通往立憲之路,在這條道路上,人類一步步回歸自由。 人之于自由,無論普羅米修斯式,還是凱撒式,都會有迷失,或迷失于革命,或失足于帝國,使暴君和奴隸不絕。不過,我們還是從普羅米修斯與宙斯的和解,看到了革命與統治之外的第三種方式——契約。在契約里,受到節制的自由意志只能轉化為法權形式的個體權力,即使神如宙斯,人似凱撒,行使權力,也必須適度,而且要合法,因為在他們的頭上,除了命運,還有更高的權力,那就是通過人們協商生產的憲法。 本文選自劉剛著《中國近代的財與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轉載請注明來源。人從哪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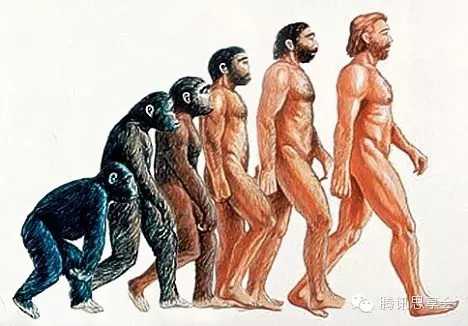
▲人類進化史靈性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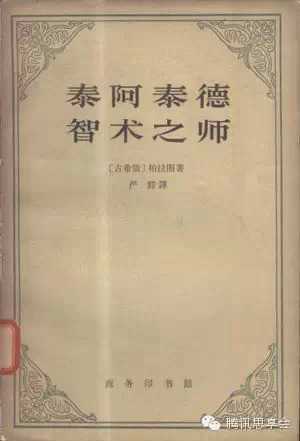
▲柏拉圖著作《泰阿泰德智術之師》人往自由去

▲油畫中的普羅米修斯
騰訊思享會 劉剛 2015-08-23 08:51:01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