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八十年代訪談錄 一日一書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八十年代訪談錄 作者: 查建英 主編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06-5 《八十年代訪談錄》之阿城 查建英:你想怎么來講八十年代這個題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十年”這種概念。就像藝術的變化不會隨著政治時期的改變而變化,好比我們文學史上,兩漢、魏晉,或者隋唐,不會因為有了一個新朝,就會出現新的藝術,政治的、權力的轉換決定不了藝術。事情也許早就發生了,也許還沒有發生。單從“八十年代”劃分,有點兒難說了。 查建英:那個時間其實是人為的計量。比如說,從外部環境看,八九年好像是一個句號,它正好又是八十年代末。九○年以后,文學上就有了王朔,大家很習慣就把王朔看成一個九十年代的現象。實際上他早在八十年代就開始了,不過那時他不突出,只是舞臺上眾多的人之一。其實這個年限不見得。 阿城:對,不見得。就像世紀末兩千年那個分界點,叫個事給攪和了:到底二○○○年,還是二○○一年算是兩千年的開始呢?我記得有些國家是二○○○年的時候慶祝,有些國家不認這個,二○○一年慶祝。很多人慌了,因為大部分人習慣了以一個十年或者一個時間的量度去決定自己的情緒。“我要跨過這一年,我要有一個新的,我要做什么事情”,突然發現不是,說下一年才是,有挫折感。美國人喜歡搞十年這種東西,decade,搞得有聲有色,有好多套叢書,你肯定看到過。臺灣前些年搞過七十年代,找了很多人回憶。 查建英:你是說他們回顧過七十年代? 阿城:對,很多人都卷進去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楊澤主持的吧。 我自己的量度不是這種,而是知識結構,或者文化構成。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來說,一八四○年是一個坎兒,新的知識撼動中國的知識結構,船堅炮利;一九一九年“五四”是一個坎兒,新的文化撼動中國文化構成,科學民主;一九四九是最大的一個坎兒,從知識結構、文化構成直到權力結構,終于全盤“西化”,也就是惟馬列是瞻。中國近、現代史,就是這三個標志,其他就別再分什么十年了。不過既然定的話題是八十年代,總要來說說吧。對一九四九年這個坎兒,我覺得七十年代算是一個活躍的時期,七六年,官方宣布“文革”結束,造成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的時期,畢竟出版又被允許了。 查建英:是不是一個從地下轉到地上的過程?比如那些詩人。 阿城:也沒有全轉上來吧。不過確實在八十年代,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人的七十年代的結果。比如說北島、芒克,七八年到八○年的時候,他們有過一次地下刊物的表達機會,但變化并不是在那時才產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末的白洋淀就產生了。七十年代,大家會認為是“文化革命”的時代,控制很嚴,可為什么恰恰這時思想活躍呢?因為大人們都忙于權力的爭奪和話題,沒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鄉下的年輕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對,六六年、六七年是特厲害的,六八年以后就開始下鄉了。 阿城:管不著了,這些學生坐在田邊炕頭了。他們在想什么,傳閱一些什么,寫什么,權力者不知道。像六十年代末的芒克、根子、多多、嚴力他們在河北白洋淀形成那樣一個詩的區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銳利迷茫,與食指的《魚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區別得很開。《三月的末日》在我看是那時的經典,可惜沒有人提了。我記得岳重跟我說,他當時提了一桶魚從白洋淀坐火車回北京,到北京的時候桶里的魚死得差不多了;春天了,但是,三月是末日。這樣,一直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所以,好像是壓制得最厲害的時期,但是因為把他們推到權力、行政力管理相對松散的地方,他們反而有些自由。 查建英:你就是那時候去了云南? 阿城:對。人的成熟其實是很快的。現在講究超前教育,其實人在十二歲左右有一次生理的變化,大致與性發育有關,會在一年內,將之前的所有知識一下就掌握了。所以所謂小學,就應該放羊,讓他們長身體,防止近視而已。小學為什么要六年?中學為什么要六年?活生生讓人混到十八歲!其實是因為規定十八歲以下為兒童,兒童不能到社會上去做工,童工是非法的,于是將他們管制在學校里磨時間,磨到法律的底線。一般一個人在十二到十八歲的時候,思想、感覺最活躍、最直接,二十歲一過,進入成熟了,以后是把成熟的部分進行調理。 查建英:很多部分成熟了,但整體還沒揉勻乎呢。 阿城:對,面還沒有“醒”透。所以呢,七十年代,正好是這個年紀,摁都摁不住。你想,他走上幾十里地,翻過幾座大山,來跟你談一個問題,完了還約定下一次。多數人其實也不會寫什么,也就是互相看看日記。當時不少人寫日記就是為朋友交流而寫的。 查建英:實際上是一種創作。 阿城:思想記錄。我覺得那個時候另有一種意思。《中國時報》他們搞七十年代,我就很有興趣。為什么呢,我要看七十年代他們那邊在干什么,我有對比的興趣。到了美國,我也是這個興趣。比如,一九六七年吧,那么一九六七年我們在干什么?美國人在干什么?橫向看看。有意思。 查建英:對,我也愛這么比。比如在美國結識了很多所謂“六十年代”那一代的美國人,他們講他們六十年代的故事,我就會回想我們在六十年代做的、想的那些事,這樣就更明白為什么現在他們和我們這么不同。當年就不同!成長的大環境、社會體制都不一樣,受的教育也不一樣。有人相信地球上有一個場,六十年代很多國家都在發生所謂的社會革命,青年人都在游行。比如說一九六八年,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個什么場,在那里起作用,西歐、東歐、美國、中國,都有所謂的社會動蕩,青年人到處騷動不安,都在造反。但實際上這些造反是不是一回事呢?你再仔細一比較,發現騷動背后那個動因其實很不一樣,動機、目的都不一樣,鬧事只是表面的相似。比如我剛到美國那些年,身邊有幾個要好的法國朋友,大家一起處得很融洽,但就是不能談六十年代,一談就變成他們集體跟我辯論。他們幾個法國布爾喬亞青年,一齊來捍衛毛澤東思想,把中國的“文革”說得浪漫極了!想想也好笑,其實這是一個中國人和幾個法國人共同回顧六十年代造成的誤會。 阿城:對,像薩特,“文革”時跑來中國,還上了天安門觀禮臺。福柯,法國新左,做教授時直接參與街頭抗爭,在房頂上扔石頭,還小心不能臟了絲絨外衣。 查建英:那你說說,臺灣的七十年代,和你那個知青的七十年代,比較起來感覺怎么樣? 阿城:臺灣的七十年代呢,比較感性。大陸的七十年代呢,就我接觸到的,比較理性。因為我們在大陸碰到安身立命的急迫的東西,你在這個地方怎么安身立命。雖然臺灣處在戒嚴時期,比較起來,臺灣還是有活動的自由。有自由,又是很多人的青春期,更多的是感性的東西,所以他們回憶起來更多的是感嘆。 查建英:嗯,不過,我想中年人回頭看青春期,多少都有點這種感嘆吧。先是純情時代,后來就有了挫折有了城府,油滑了,感情也不太純粹了,你能說這是臺灣的特殊現象嗎?還是一個生理現象?不過,也許這和臺灣處在轉變期有關。七十年代他們經濟起飛,從鄉土轉向市場,轉向那種做貿易做買賣的城市經濟,生活方式變了。 阿城:對,就是陳映真寫的那個時代。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臺灣編《人間》,《人間》雜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出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后來告訴我,我離開后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重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寫字的人,將自己精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沒說啊。不過在精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么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里沒權,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于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也會有模有樣地刁難欺負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動物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一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出矯情。 查建英:我見到陳映真是在山東威海的一個會上,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臺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里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后就上來一個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來搞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后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唉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么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這也變成段子了。其實張賢亮和陳映真年紀大概也差不多。 阿城:所以形成不同。人民就像水中的懸浮物,上上下下變化著,我們不都是其中一粒嗎?誰能代表其他的粒呢?你想要代表,一般來說你就有了權力之心了,人民很可能就成了你的真理的犧牲品了。我們見得還少嗎? 再說“文革”一結束,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可以考大學了。我遇到不少那個時候在大學里做教師的人,他們都說剛開始很討厭這批插隊考回來的人,太難教了!但是,這批人畢業走了,開始正常了,高中畢業就可以上大學了,他們又很懷念這批人,說上課沒勁了!就是因為插隊那批人已經是社會油子,經驗多得很。你不要跟我講馬列教條,不要,我有一大堆的東西等著為難你呢。做一個教師就會覺得挺煩的。過了這個時候,他們又覺得,哎呀,沒有這種人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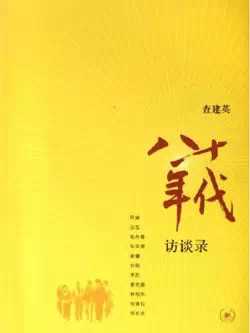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1:0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