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為何有人恐懼同性戀? 讀藥
 |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 簡體 傳統 |
近日,臺灣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在出柜14年后再度開腔,坦言同性戀身份所帶來的壓力,“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向爸爸媽媽證明我們不是妖怪”。在公眾對同性戀日益理解的今天,為何仍有人對同性戀持恐懼憎恨的情緒?這本《男人之間》或可給予答案:它從社會、經濟及權力關系的角度,揭示了傳統異性戀結構的實質——以女性為交易媒介的男-男關系,更論述了“恐同”的成因,指出男性之間的“恐同”和“同性戀”同樣是厭女的,有時甚至難以區別。 本期主題書:男人之間 著者:[美]伊芙•科索夫斯基•賽吉維克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讀藥點評:換個角度看“同性戀恐懼癥” 精彩觀點: 從男性同性社會性紐帶看“恐同”心理 “女人愛女人”與“女人促進女人的利益”之間的連續體涵蓋了性愛、社會、家庭、經濟和政治等領域。它表面上的簡單性和一致性,如果不是和男性之間的關系形成了強烈反差的話,就不會那么驚人了。當羅納德·里根和杰西·海爾姆斯為“家庭政策”互投贊成票時,他們是促進男人利益的男人。(實際上,他們代表了海蒂·哈特門對男權的如下定義:“[男權]即男人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具有物質基礎,它們盡管是等級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間建立或創造了相互依賴和團結,以使他們能夠支配女性。”)他們之間的紐帶與男同性戀伴侶之間的紐帶是否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里根和海爾姆斯會厭惡地說,不。大多數男同性戀伴侶們也會厭惡地說,不。但為什么不呢?難道“男人愛男人”與“男人促進男人的利益”之間的連續體沒有像對女性那樣有著天生的力量嗎? 正好相反:許多關于父權結構最有用的近期作品指出,“義務異性戀”被建構到了男性主宰的親緣關系系統中去,或是說,恐同是諸如異性戀婚姻之類的父權制度的必要結果。顯然,不論使男人彼此聯系、彼此促進的各種紐帶合在一起會多方便(這樣做產生的對稱性很有用),這樣的“合”會遇到一個起阻止作用的結構障礙。從我們的社會的角度來看,不論如何,想象一種非恐同的父權形式,明顯是不可能的。比如,蓋爾·魯賓寫道,“對人類性欲中同性戀成分的壓制,以及,由此推導,對同性戀者的壓迫是……用其規則和聯系方式壓迫了婦女的同一制度的產物。” 對同性戀者的這種父權式壓迫,從歷史表現上看,一直是野蠻的,而且幾乎沒有盡頭。路易·克朗普頓做過詳細研究,并將這個歷史形容為是滅絕性的。我們自己的社會也具有殘酷的恐同特征;而且,針對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無緣無故的,而是緊密地交織于家庭、性別、年齡、階級以及種族聯系構成的纖維中。如果其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不改變,我們社會中的恐同就不會停止。 然而,尚需闡明的是,由于大多數父權制度從結構上涵括了恐同,因此,父權從結構上要求恐同存在。K.J.多弗的近作《希臘同性戀》似乎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古希臘反例。根據多弗的證據,男性同性戀在這一文化中廣泛存在、合法而且深具影響。年長男性對青少年男孩的追求在結構上以階級為標準,而在市民階層內部則以年齡為標準。用來形容這種追求的典型方式我們通常是用到浪漫的異性戀上去的(比如,征服、投降、“殘酷的美人”以及愛的對象身上缺少欲望)。男孩在這樣的關系中是被動的一方。但同時,由于男孩注定要成人,所以角色的分配并不是永恒的。因此,盡管這樣的愛情關系對對象具有暫時的壓迫性,但也有著極大的教育作用。多弗引用柏拉圖《饗宴篇》中珀薩尼亞的話說,“對他(這個男孩)而言,為改進他的頭腦和性格的人提供任何服務都不為過。”那么,盡管有情欲成分,這也是一種師徒關系紐帶;男孩們成為學徒,學習作為一個雅典市民的方式和道德標準,并繼承了市民才能享有的特權。這些特權包括掌握男女奴隸勞動的權力,以及掌握包括他們自己階級在內的任何階級的婦女的勞動的權力。“婦女和奴隸屬于同一類人,并生活在一起,”漢娜·阿倫特寫道。清楚的階級控制系統和性別控制系統是男性文化最看重的東西的必要部分:“對勞動的蔑視最初(起源)于一種對不受制于必須的自由的熱烈追求,以及一種同樣熱烈的不耐煩--對任何不留痕跡、沒有豐碑、不留下值得記憶的功績的努力的不耐煩”;因此,被蔑視的勞動就被留給了婦女和奴隸。 我認為,希臘人這個例子證明了,盡管異性戀對于維系任何父權形式都是種必要,而恐同,至少是針對男性的恐同,則不是。實際上,對希臘人而言,“男人愛男人”與“男人促進男人的利益”之間的連續體,似乎是延續無間的。用我們的話說,就好像是在大陸浴場夜總會的男性紐帶與波西米亞林的男性紐帶--或者說,在會議室里或上議院衣帽間里的男性紐帶--之間,并沒有感覺得到的不連貫。 那么很清楚,我們當前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不對稱,即女性同性社會性紐帶及同性戀紐帶之間相對連續的關系,與男性同性社會性紐帶及同性戀紐帶之間強烈的不連續關系之間的不對稱。此外,希臘人的例子(以及諸如G.H.赫特研究的新幾內亞“薩姆比亞”之類的部落文化的例子)顯示,同性社會性連續體的結構依據不同文化而發生改變,而不是“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的先天特征。的確,盡管這種解釋和男女權力競爭的問題緊密相關,但是,它要求一種比“父權”更明確的歷史分類模式,因為父權權力結構(即哈特門理論意義上的父權權力結構)不僅是雅典社會,也是美國社會的特征。不過,我們不妨認定這樣一條直接的公理:男女同性社會性的歷史差異--它們自己同時也隨時間而改變--一直會是持續的男女權力不平等的表現和機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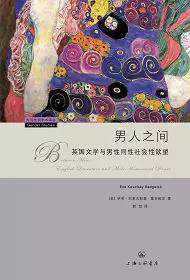
鳳凰讀書 讀藥周刊 2015-08-23 08:56:1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