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曾彥修:他把槍口抬高了一厘米 紀念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昨日凌晨4點43分,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雜文大家曾彥修先生,即嚴秀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95歲。 曾彥修先生是四川宜賓人,1919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起先后入陜北公學、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夏調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3年調中央宣傳部。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社社長。1954年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據介紹,在“反右”中,曾彥修曾把自己劃為“右派”,轟動全國。當時在“反右”中,曾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遲遲沒有行動,他認為沒有什么人應當劃為“右派分子”。上級追得緊,而且還有“百分比”。曾老作為一個領導,實在沒有辦法應付上面下達的“任務”,于是把自己作為“右派”報上去。曾老被劃為右派后,被開除出黨,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領導職務。1960年到1978年,曾彥修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1983年申請退休。著有《嚴秀雜文選》、《審干雜談》、《牽牛花蔓》、《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覺此生未整人》、《京滬竹枝詞》等。 2011年,已經年過90歲的曾老先生開始寫回憶錄《平生六記》。在這本回憶錄中,記錄了他一生中記憶深刻的幾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運相關。《平生六記》于201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干。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在《平生六記》中,曾老先生用這句話作為這本回憶錄的開場,這也是他一生最問心無愧的地方。而在《九十自勵》詩中曾彥修先生寫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6 1950年初,即全國解放的一年多(有些地方才幾個月,如廣東、四川、云南等地)后,在全國發動了一場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最大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恐怕整整有近一年或一年多,是最中心的工作。天天要向北京報告鎮壓人數(“鎮壓”,長期以來的死刑代名詞)。這個運動為什么叫“大張旗鼓”呢?就是這是一切工作中心的中心,隨便你火車站、菜市場、電影院、醫院、公園中,都必須貼滿大標語,牽起大紅布的口號,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須是滿墻滿壁的大標語口號。 報紙更是幾個版面都是“鎮反”宣傳品,前后總要宣傳好幾個月。各大學(以至中學)、工會、青年團、婦聯,特別是各街道居民委員會……更是長時間學文件、讀報紙、開控訴會……總之,凡是進行這項任務的,黨、政、軍、民、學,全民各界,都要事先宣傳到,同時充分揭露到、控訴到,確是成了一個時期大中城市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那一兩年,對這件事是:公安管實行;黨、政、軍、民、學、宣則長時間管宣傳活動。 廣州是 1949年 10月初旬后解放的,敵人前幾天就全部跑光了,我大軍是在敵軍全部撤退后晝夜兼程趕進廣州城的。 北京是 1949年 1月解放的,上海是 1949年 5月解放的,南京比上海更早一些。以地下工作來說,廣州雖然也很可觀,但比起北京、上海來,恐怕還是要差一截。因此,廣州的廣大市民,對共產黨、解放軍的了解程度,比起上述城市來當然也就有相當的距離。何況地鄰港澳,反動派利用港澳為基地而做的反共宣傳的影響,當然在全國是最深的。 上面這些說明,似乎全是廢話。其實這些是說明本節問題的根本背景資料,不然你就無法理解本節所述問題的重要性。 1951年快 4月底時,我在廣州《南方日報》工作,我和楊奇分任正副社長,另一總編輯,似新來不久。近 4月底,一晚九時后各有關同志,如采訪部主任曾艾荻、編報部主任吳楚、編輯部秘書陳魯直等六七人正在商議決定明天四個版面如何安排時,采訪部政法組組長成幼殊(女,地下黨員),忽然緊急拿來政法組記者剛從省公安廳緊急拿回的,明天要處決一百四十多人的名單,和每個人兩三行的罪狀。 我說,壞了,壞了,我們事先沒聽說半個字呀,怎么能配合宣傳呢!?大家通通變色了。因為大家都看了近一年的京滬各地報紙,知道大鎮反一來,報紙是必須同時推出四個版面甚至是加頁,集中持續宣傳此事的。而我們則剛剛拿到罪狀名單,明天如何見報?我們沒有社論、沒有事先寫好的大量控訴資料,沒有社會名流支持的談話,沒有受害者對死刑犯的控訴,任何宣傳資料都沒有,連個社論也寫不出。何況一次處決一百四十多人,歷史空前,新區群眾如何能體會這些!?我們報社亂成一鍋粥,都認為明天絕不能這樣出報呀,怎么辦呢?中央的方針明確得很,是強調大張旗鼓,即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要讓群眾家喻戶曉這些人的罪惡。 同時,我們看見,這當中確有一些曾是殺害我們重要著名人物(現已記不清了)及 1927年時殺害蘇駐廣州總領事的執行連長。其中還有一個解放前的省教育廳長,經記者了解,是解放廣州后又從香港公開回來的,這人要處決究竟是怎么回事? 此外,我早在延安或進北京前在西柏坡時,就聽說過或聽過報告,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記得好像有沈鈞儒、黃炎培)對我們善意地提過意見,說,你們鎮反時,總是“公審”,罪名總是“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之類,這怎么行啊!(說不定是 1949年 3月進北京后才聽說的。) 我們這個“編前會議”,苦了兩個小時,連十一時的夜餐也端進來了,只是沒有人吃得下一口。大家毫無辦法,我們有什么發言權呢?我們的義務就是照登不誤,標題越大越好。 如此苦惱了兩個小時,毫無辦法,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忽然,副社長楊奇同志說,“現在只有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由老曾同志打電話給 203 了”。這是什么意思呢?廣東初解放時,葉劍英同志的代號是“ 203”。半夜三更我又怎么可以干這種事呢?原來當時有這么個規定,報社的主要負責人,在萬不得已時,可以在后半夜打電話與黨委主要負責人。因為第二天出不了報,對黨委主要負責人來說也是個麻煩事。大家又議論了半個小時,都說,只有這一個辦法了。我說,規定是規定了,誰敢實行?又議論了很久,我說,萬一是“ 203”看過的呢,這個釘子可碰的大了。 再議論很久,這回主要是分析葉帥知不知道此事,看過這罪狀沒有?我說,分局每周一次擴大會,我參加的,但上一二次沒提起過這件事情,從這點看,“203”可能不知道。再說這個罪狀,“203”長期在蔣區做上層交往工作,論道理他是不會接受按這些罪名去處決人的,這種處決罪名還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做法,連我們都接受不了,他會同意嗎?這樣分析來分析去,楊奇特別同意后一說法,這種罪名“ 203”不會同意,他說,恐怕只有與“ 203”打電話一條路了。我橫下一條心,大著膽子就打了,時近午夜十二點,打與他的身邊秘書。秘書那兒倒也順利,說他先去報。約十分鐘后,“203”本人來了,“203”先說: “你是曾嗎?這事你有意見嗎?這可是毛主席定的政策啊,你有什么意見!”我說,“不是,是具體情況太奇怪了”。我只能簡陳幾分鐘。葉帥又反復問,我說“真是這樣的,……所以我要報告”。葉帥回答說,“好,你在一點鐘前趕到小島。”東山小島小區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與葉帥的住地。我立即出發。見省府常務副主席古大存、華南分局另一個宣傳部副部長李凡夫已先到,另有分局辦公廳主任林西,葉帥的主要秘書姚天縱已在座,第三書記方方出差了。我到后不久,葉帥也下樓來了。不久,省府廳長(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華南分局社會部一處長同時也很生氣地來了。那個處長把身背的兩個麻布口袋的材料往地下重重一丟,二人均有怒色。坐下,葉開場幾句,即叫我發言。我講完,對方也講情況,說今晚分局社會部、省公安廳,市公安局等均漏夜辦公,參加這一具體行動的(包括沿途及周圍警戒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均已準備完畢,準備明天,不,今天九點執行。我一聲不吭,知道對方名聲很大,在江西時代就是做此事的。 葉帥再叫我講,說“報館”有點意見(這些老前輩用詞多是老習慣,把我們叫“報館”),聽他們也講一講。我就大致講了上述意見。李凡夫也發言支持我,說,我們宣傳工作全不能配合,也是違反中央指示的呀!對方反復講準備了兩三個月,今晚一千多人漏夜辦公,不大好辦了。跟著古老(古大存,省府常務副主席、華南游擊運動老負責人,延安整風時中央黨校一部主任)也表示,他也不知道此事,只有一個空洞罪名的東西,“一貫反動,民憤極大”,怎么行呢?對方反復堅持,一切已完全準備好,要改變影響也不好。 葉帥很沉著。他說,這么大的行動,分局事先不知道。對方立刻反駁說:“分局開會討論過。”葉說,“那是原則性的,決定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報館也參加了,知道的人很多,那是個內部動員會,不是行動指令。”對方再三強調他們只是在執行中央與分局的指示。葉帥回答有點刺激了:“要不是報館通知我,這么大的事情我也要明天看報才知道呀!”古老說,我也是,用省法院的名義,我根本不知道。對方又說,“大張旗鼓”,我們沒有那么多宣傳干部呀(作者按:那時,“筆桿子”這一詞還未出現)。接著,李凡夫立即回應:這事是全黨動員呀,我們還會找不到宣傳干部嗎?總之,說來說去,對方并未讓步,堅持明天執行已難于更改。這時,葉帥不得不把最后的重話講出來了,說:“我們要記住中央蘇區的教訓呢,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黨委手里,還是掌握在保衛部門手里,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訓呀!” 我一聽這話,就知道葉帥已下了最后的決心。對方當然更知道,葉帥已講了最后一句話了,立即很不滿地說,我通知明天停止執行!于是就離座到廳內邊上打了一個電話:明天停止執行!等一會兒又說,“是,全部停止執行,原因等我回來再說。”之后我說我也要打個電話,報館也是一百多人在等著我回話呢。那里只有一部電話機,我也只能在那里打。 之后,就由葉帥指定林西、李凡夫同志,草擬內部開動員大會與組織宣傳隊伍,遵中央規定,要做到家喻戶曉,每個居民小組都要開宣講會,聲討會。 重新整理罪狀事,葉帥說,這事是報館提出來的,就由報館抽人去重新研究和起草草稿(指布告)吧!我說,我兩天后就要帶領華南代表團去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第一次會議,會上就決定先由報社副社長楊奇帶領一個隊伍到公安廳去幫助他們整理材料。 我可能是 1951年 4月 26或 27日離開廣州去北京開會的。兩個星期會完后,我們隊伍應上海市委宣傳部之邀,往上海走一趟,因為我們中有人未離開過廣東、海南島,所以很想多走幾個地方看看。 5月底了,我回到廣州,已執行了。具體情形,我就無權再過問了。但為什么又拖這么久?楊奇說,我們幾人是到監獄辦公室去工作的,材料亂得很,很難整理出一個個人的明顯事跡來,所以拖了個把月。我說,還用“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嗎?楊說,這個取消了。 又過了幾十年,大概是二十世紀末,陳魯直、成幼殊夫婦作為外交部的離休干部與我同住方莊,我因行動不便,閉門不出,他們來看我。我詳細問過成幼殊兩次,成說,是亂,是雜,材料不具體,我們開始去四個人,在監獄辦公室辦公,有兩個新黨員,不起什么作用,不久,就是我跟楊奇兩個人了。我問,人數有什么大變動沒有。她說,沒有大變化,重新摸了材料,把空洞的“一貫反動”的一類詞改為一些具體罪行。但應如何具體處理,我們就無權過問了。報紙當然準備了很久,算是大張旗鼓地做了一些宣傳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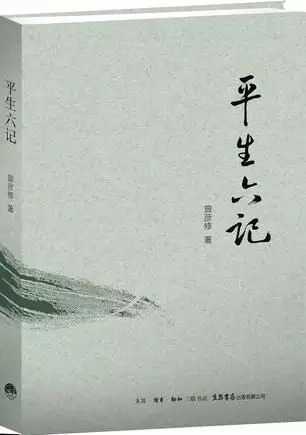
《平生六記》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56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