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李昕:我幫錢鍾書打《圍城》官司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1993年6月,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兩周年之際,北京各大報刊忽然之間接二連三地刊登了這樣的熱點新聞:“《圍城》再度被圍”,“《圍城》被盜印本圍困,錢鍾書欲依法突圍”,“《<圍城>匯校本》版權烽煙起”,“錢鐘書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陷入侵權困擾”,一時間,一場有關《圍城》的版權官司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這些新聞,來自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5月27日邀集各大媒體舉辦的一場新聞發布會。而在發布會上,代表出版社發布新聞的人就是我。 (一) 那時,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下簡稱人文社)担任社長助理兼編輯室主任。1992年初冬的一天,社長陳早春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一進門,他便遞給我一本紅色封面的書,我一看,書名是《圍城》,心中不免詫異。《圍城》在人文社印行十幾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記得換過呀。陳社長告訴我,這是四川文藝出版社(以下簡稱川文社)的《<圍城>匯校本》,現在正在大量發行。 《圍城》匯校本 我看了一下這本書,署名錢鍾書著,胥智芬匯校。我沒有聽說過胥智芬其人。再看內容,不過是將《圍城》1947年在《文藝復興》雜志發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八十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進行了比對,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詞用字一一標示出來,作為注釋,注在每一頁的下方。整體上看,書的內容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釋的長篇小說《圍城》,但注釋的內容,一概只是關于某個字詞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詞一類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過來的個別錯訛,也有經編輯更正的解放前舊版中的排版錯誤,更為大量的是由于漢字簡化而出現的同一漢字的不同字體(例如舊版作“一枝筆”,新版作“一支筆”;舊版作“拿著”,新版作“拿著”等等),這些都被不厭其煩地羅列出來,全書號稱兩千多條注釋,大量屬于最后這種情況。看了不禁令人發笑,以為這樣的“匯校”,實在太不專業了。一看便知,所謂“匯校”不過是障眼法,川文社真正想出版的是長篇小說《圍城》。 誰都知道《圍城》現在是熱門書。1990年《圍城》電視劇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長篇小說《圍城》多次重印,仍供不應求。不法書商乘機盜版,國內幾年中先后出現了近20種盜印本,總印數據估計逾200萬冊。但凡盜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無聲息地賣,讓你查不到,抓不著。但是川文社的《<圍城>匯校本》,卻是打著“為學術研究提供新版本”旗號,堂而皇之、大模大樣地公開銷售,他們的大言不慚和理直氣壯著實令我震驚。 陳社長向我介紹說,這本書是1991年5月出版的,6月份,錢鍾書先生收到四川方面寄來的樣書,當即和我社編輯聯系,表示不知此事,問出版社是否同意如此“匯校”?得知此書是四川方面擅自出版之后,錢先生即委托我社與四川方面交涉。7月23日,我社代表錢先生致函四川省新聞出版局,要求查處川文社出版《圍城>(匯校本)侵害錢鍾書著作權和我社專有出版權的行為。8月8日,川文社曾經回函,承認了自己的侵權行為,表示愿意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并承諾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陳社長見信后曾表示:“都是兄弟社,好商量。” 但是,陳社長說,“沒想到他們是說一套,做一套”,就在1991年8月以后,川文社又繼續重印發行這本書,到現在總數累計超過10萬冊。而且,他們甚至把封面上的“匯校本”三個字也取消了,侵權更加明目張膽,變本加厲。 “他們這樣搞法”,陳社長說,“是要逼著我們打官司呀。” 深入一想,我明白了。這個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贏,不能打輸。因為如果輸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積累的大批現代文學名著,都可以被別人輕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這樣《著作權法》所保證的專有出版權就名存實亡了。所以這個官司并不僅僅為了這一本書,而更重要的是要在《著作權法》實施以后為出版界立一個規矩,建立一個游戲規則。 陳社長告訴我,現在錢鍾書先生已經全權委托我們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們替錢先生委托了兩位律師,但是社里也要有一個代表負責此事。他看了看我說:“你是我的助理,你辦事,我放心。” 這樣重要的任務,我當然要接下來。但是我知道打官司需要出差,而我的家庭有些具體困難。因為家住得很遠,我每天上下班都得接送孩子,不便出差。如果能夠有一套位于出版社附近的家屬宿舍,孩子放學可以自己回家,這問題就解決了。雖然當時我作為社長助理,在等待分房的人中排名第一,但是出版社下一批分房子,大約至少還要等半年到一年。 陳社長說,“那我就提前給你分一套房子。”此言一出,我知道他是下定打官司的決心了。 (二) 接受任務之后,我和社里主管版權事務的副總編李文兵、總編室主任馮偉民、版權室負責人王睿以及社里為此案聘請的兩位律師陸智敏、李浩一起開過幾次會,大家統一認識,研究對策。 陸律師情緒激動,顯然是窩了一肚子氣。他不久前剛從成都回來。因為川文社早先曾表示愿意“抱著誠懇態度妥善解決這一糾紛”,他去成都找川文社社長研究解決方案。誰知那社長“工作太忙”,竟然讓他在賓館里“待見”了9天。最終見面,那社長的態度陡變,矢口否認川文社有任何侵權行為,連陸律師代表錢鍾書查詢此書印數也遭到拒絕。 “他們現在全不認賬了”,陸律師說,“而且好像有恃無恐,并不怕我們打官司。” 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人文社和錢鍾書先生一起打官司,錢先生的態度至關重要。我從陸律師那里,看到了錢先生有關此案的一系列信函,并了解到他對此案的基本觀點和看法。 錢先生的態度,讓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支持。 1991年6月錢先生收到《<圍城>匯校本》樣書,扉頁上,川文社一位編輯給錢鍾書、楊絳先生寫了一封信,這樣說:“去年,頓生念將錢老《圍城》弄出匯校本,曾托人函示錢老。現書已出,乞支持這項吃力不討好的造福子孫后代的做工。”錢先生立即致函人文社編輯黃伊,指出此書是“一種變了花樣的盜版”,說:“托人函示云云,全無其事,語意曖昧,想蒙混過關;假如有此事,得我同意,何必‘現’請‘乞支持’?《出版法》(按,指《著作權法》)公布后,想此人感到緊張,故作此補筆,向我當面撒謊。……特此奉告,隨貴社處理吧。”然后便向人文社開具了全權委托書。 人文社同川文社展開交涉以后,曾詢問他們的編輯所言“托人函示”是否確有其事。對方答復說,“曾委托‘錢學系列叢書’作者之一的陳子謙同志”“書面或口頭報告錢鍾書先生”。錢先生聞知后,立即向陳子謙查詢。陳回函,稱此說“純屬捏造”,他們這樣說,“也損害了我的名譽”。“這個社的一些人對《著作權法》一點也不尊重,這是我不能容忍的”。錢先生接此信函,更加證實了自己最初的判斷。 對于“匯校”本身,錢鍾書和楊絳先生也都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圍城》責任編輯黃伊前往府上拜訪錢楊二老時,談論起“匯校”問題,楊先生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這些書,因為年代久遠,有人研究這個版本,那個版本。《圍城》這本書,作者和我們都還活著,有什么必要搞‘匯校本’呢?”錢先生則非常氣憤地表示:“什么‘匯校本’呀,這是變相盜版嘛。要使用我的作品,也不預先征求我的意見。再說,個別排版錯誤,或者疏漏之處,我在再版時已經改了過來,作者有對他自己的作品的修改權呀,有什么必要特別將它標明出來呢?” 基于錢楊二老的認識,后來我和陸律師等曾四出拜訪文藝界和法學界、版權理論界知名人士,征詢他們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匯校”的意見。我們最初估計到這可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不敢奢望得到所有專家學者的支持。然而無論大家在一般意義上如何評價“匯校”的價值,一旦聯系到《<圍城>匯校本》的個案,幾乎所有專家都無一例外地指出,川文社已對人文社構成侵權。特別是巴金老人來信,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他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居然有人要出《家》的‘匯校本’,這是否定版權時代的做法,我不會同意的。” 這些專家意見增強了我們的信心。于是,我們在1993年初,給新聞出版署幾位主要領導致函,尋求支持。函中表明了我們對“匯校本”的看法: “眾所周知,‘匯校’是我國古籍整理的一項專門工作,對于年代久遠、原作散失、并已進入公有領域的古籍,進行版本匯校,判別文字真偽,是有意義的工作。古籍版本沒有專有出版權的問題,因而翻印使用流行版本不構成侵權。但當代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修訂定稿,不存在判別文字真偽的問題,而當代作品的專有出版權受法律保護,未經出版權享有者及作者同意,任何翻印原作都是侵犯著作權及專有出版權。” 為此我們指出,如果不妥善處理版權問題,“就把對待古籍的態度和方法套用在當代作家作品之上,是一種常識性錯誤,而這種錯誤,必然導致‘專有出版權’的滅亡。” 因為這封信函代表著人文社和錢先生的共同立場,所以我們預先呈送錢先生審閱。錢老閱后,當即復函,寫道: “公函理充詞正,以老朽外行看來,無懈可擊。此非為爭幾張鈔票,乃維持法律之嚴,道德之正也!” 錢先生“不為鈔票”打官司的立場是明確的。在此之前,他已經不止一次嚴詞拒絕和川文社私下和解。 在雙方對簿公堂之前,川文社自然明白錢先生與人文社聯手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他們曾試圖單方面和錢先生和解,以釜底抽薪。1991年8月13日,錢先生在給人文社的一封函件中說:“頃得XX同志電話,告我云:四川文藝出版社派人來京,一面請XXX同志向貴社疏通,一面請XX同志向我疏通,要求‘送錢’給我‘私了’。我向XX說明此事已交貴社辦理,秉公執法,我不和他們‘私人’接觸。特此奉聞。想貴社必能維護《出版法》(按,指《著作權法》)之尊嚴也。”9月30日,錢先生再次來函,表示“不與對方‘私相授受’”,“決不背前言,‘私了’一節請放心。” 川文社也很有一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韌性。當面送錢不成,又改為匯款。當年12月中旬,錢先生莫名其妙地收到某工商銀行的領款通知,告知9800余元的匯款已到。錢先生猜想,準是川文社所為,請人去銀行查詢,果然不錯,當即表示拒收,此舉引來銀行工作人員一片詫異。 錢先生的態度可謂絕決。我想,他這是在力主依法辦事的同時,也在力挺人文社。當然,之所以力挺,是為了維護正常的出版秩序,為了游戲規則的公平和公正。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是我們幫錢先生打官司,還不如說是他老人家在幫我們打一場維權的官司呀。 (三) 說到這里,讀者大概會問:川文社開始曾經認錯,為什么后來改變態度,公然繼續侵權,且有恃無恐? 這是因為他們拿到了“尚方寶劍”。 川文社是不肯輕易認輸的。兩年來,他們也一直在為自己的侵權行為尋找“合法”的理論依據。他們托人找到國家版權局,就“匯校本”問題尋求法律援助,結果便如愿收到了1992年11月13日該局辦公室的標明(92)權辦字第37號信函。該函對《<圍城>匯校本》發表了幾點意見: “一,‘匯校’是對原作品演繹的一種形式,匯校者依法匯校他人作品,對其匯校本享有著作權。 “二,胥智芬未經錢鍾書的許可對《圍城》進行‘匯校’侵犯了錢鍾書的著作權(使用權和獲酬權)。四川文藝出版社在未作任何調查和防范措施的情況下,出版侵權作品《<圍城>匯校本》,應承担連帶責任。 “三,人民文學出版社在與錢鍾書簽訂的合同有效期間對《圍城》一書享有專有出版權,但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匯校’不屬于專有出版權的范疇,錢鍾書又未將‘匯校’這種使用形式轉讓或授予人民文學出版社專有使用,因此,胥智芬及四川文藝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學出版社對《圍城》一書的專有出版權。” 這可以算是一份版權事務的“裁定書”。但如此違背常識的裁定,幾乎可以用“荒謬”二字形容。它的副本寄到人文社,令我們大感詫異。國家版權局是《著作權法》的權威解釋機構,然而他們竟然可以隨意地把作者對作品的著作權轉移給“匯校者”所有,而且還把一家出版社有計劃、有組織的侵權行為(這是川文社已經承認的),解釋為一個不明身份的“匯校者”的個人過失,僅讓出版社承担“連帶責任”。如此的一番解釋,向錢鍾書先生交代,怎么能說得過去?難怪錢先生看了“裁定書”,連稱“可嘆,可嘆!” “裁定書”說到“匯校本”的出版并不侵犯專有出版權,我們覺得事情重大,需要和版權局協商對話。 在一場安排好的對話會上,雙方各執一說。版權局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始終揪住一條:《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關于專有出版權的規定,只講包括“原版、修訂版和縮編本”,并沒有把“匯校本”包括進去。所以,如果認為“匯校本”也屬于專有出版權的范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但我們強調指出,“匯校本”的核心內容是什么?不就是“原版”和“修訂版”嗎?小說還是這部小說,作品還是原來的作品,《圍城》還是那個《圍城》。這個“匯校本”不過是以“匯校”的名義翻印“原版”和“修訂版”。 我們引用錢先生致人文社信函中的話作為依據: “《圍城》原印本雖非由貴社出版,但《圍城》作為作品,已由作者正式同意貴社出版,權屬貴社。原本上改動處皆屬作者著作權,現既已由貴社出版,則翻印原本顯系侵犯貴社之違法行為。” 人民文學版《圍城》 但版權局辦公室一位處長對錢先生的話報以輕蔑,他沖口而出:“錢鍾書不懂法!”我們見到這一情景,便知道協商對話不可能奏效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打官司,通過法律程序,把國家版權局的“裁定”搬倒。但誰都知道,這是極為困難的。國家版權局是國家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掌握著《著作權法》的解釋權,他們的言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法律。他們支持川文社,給我們形成的壓力很大。 四川方面已經放出風來,說是“誠惶誠恐地等待”與我們“對簿公堂”。這種以退為進的口氣,似乎是胸有成竹。 而錢鍾書先生明確表示,官司要打,但他不能自己出面了。這一階段,錢先生身體狀況不佳,與我們溝通,大多通過女兒錢瑗。錢瑗因為小時候隨錢楊二老在清華園生活,住處離我父母的家不遠,她熟識我的父母和大姐,也知道錢楊二老在清華外文系任教時曾與我父親同事。所以她得知人文社派我幫助錢先生打《圍城》官司以后,便回家把這消息告訴二老,二老自然非常高興。錢瑗很感慨地對我說,父母年事已高,很多事都需要有人幫忙了。如果人文社不能利用法律手段了結此事,那她父親豈不是“任人宰割”了嗎?這話說得令人動容。 在我們這里,此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我們沒有退路。專有出版權是我們面前的一道大堤。洪水襲來,只有保衛大堤才是求生之路。否則堤壩決口,人人遭殃。 (四) 為了給錢先生,也為了給自己的出版社討回公道,我們于1993年底,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了胥智芬和川文社。 為什么要在上海立案?這是因為我們考慮到川文社在四川的勢力和影響,担心地方保護主義因素、人情因素干擾司法公正。由于我們了解到胥智芬在上海任職,所以便理所當然地把上海選擇為侵權發生地。這一下,使得嚴陣以待的川文社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但川文社迅速擺出應戰的姿態,他們立即在上海聘請了著名律師朱某作為委托代理人。朱律師有一張"名嘴",曾經打過許多著名的官司,也算是律師界的知識產權問題專家。 我們這邊,則在抓緊時間補充證據,我們邀請了多位權威法律專家表態,請他們寫下自己的專業意見,準備提供給法庭。同時也動用媒體制造輿論,除了召開新聞發布會以外,我也親自執筆寫了一篇長長的新聞通訊,題為《<圍城>(匯校本)盜版風波》,刊登在人民日報主辦的《大地》雜志上。 幾個月后,這場官司在上海開庭。我和兩位律師一起去參加法庭辯論。那天的辯論差不多進行了整整一天。雙方都做了充足的準備,你來我往,唇槍舌劍。對方聘請的朱律師不愧辯論高手,他非常善于鉆空子,找漏洞,發言時始終保持洪亮的嗓音,自信的語氣,時時發出咄咄逼人的提問。但因為我方提出的證據嚴謹、全面,無懈可擊,甚至是無可辯駁,所以朱律師雖巧舌如簧,也難以提供言之成理的見解,最終無法挽回頹勢。 例如,辯論中談到錢先生拒收川文社的稿費。因為這筆稿費在銀行幾經周折,最后退回川文社的時間,相對稿費寄來的時間晚了4個月。朱律師以為有隙可乘,不由分說,便認定錢先生在這四個月里的“沉默”,實際是“默認”了這筆匯款,由此也便“默認”了“匯校”的行為,使得“匯校”的性質由“非法”轉變為“合法”。至少川文社在這4個月里不構成侵權。這種強詞奪理的辯詞,誰都知道不能成立。 再比如,細心的朱律師發現,關于《圍城》一書,錢先生在1980年和人文社簽訂過10年期的出版合同,然后又在1992年3月和人文社再次簽訂10年期的出版合同,兩者中間,有一個1年零3個月的空擋期(即1991年1月至1992年3月)。而川文社的《<圍城>匯校本》正是在這個空擋期內出版的(1991年5月),所以他說,川文社并沒有侵犯人文社的專有出版權,因為那時人文社本身并不享有這種權力。但是,我們出具了錢先生于1991年2月4日給人文社開出的出版授權書,并說明,這個“空檔期”未簽協議,是因為《著作權法》正待公布,雙方約定先以授權方式繼續合作,待《著作權法》實施后再根據新的法律規定簽訂新的合同。這樣便一下堵住了朱律師的嘴,令他無話可說。 辯論中我方強調川文社是巧立名目翻印《圍城》,“匯校”只不過是個幌子,舉出的例證是他們在后來大批加印此書時,竟然將“匯校本”三字從封面上取消,而直接以《圍城》作為書名進行征訂,此舉暴露了他們追逐利潤的真正目的。朱律師對此辯護說,這是印刷部門和經營部門的疏忽,并非川文社的故意。他似乎是認為除了編輯部門以外,其他部門都不能代表出版社,如此解釋,怎能服人? 在開庭過程中我方律師明顯占了上風。休庭后,審判員將雙方人員找到一起,例行公事,做庭外調解。但雙方都拒絕和解,愿聽候宣判。這時雙方又短兵相接,辯論起來,核心問題還是“匯校本”的出版是否侵犯專有出版權。朱律師聲稱“匯校”是一種新的演繹作品形式,可以獨立享有版權。這時我接過話茬說:如果這樣“匯校”就可以形成新的版權,那么你可以給一本小說后面附幾篇評論,稱之為“評論本”;我可以給一本小說加幾條考證,稱之為“考證本”;他還可以給一本小說加幾條注釋,稱之為“注釋本”,然后大家都大模大樣地翻印使用原作品,各自擁有新的版權。如此一來,這個世界上還能存在保留專有出版權的小說作品嗎? 朱律師對我的說法顯然缺乏思想準備。他沒有說話。散場以后,他走到我旁邊說:李先生口才這么好,為什么法庭辯論時不講話?我笑笑說,我們的律師口才比我更好呀! 這場官司一直持續了三年。經過上海中院初審,上海高院二審,至1996年12月結案。我們沒有懸念地獲得完勝。法院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而非《著作權法》)做出判定,除了胥智芬和川文社需要在《光明日報》上公開向錢鍾書先生和人文社就侵犯著作權和專有出版權的行為賠禮道歉之外,還需要賠償錢先生約8萬8千元,賠償人文社約11萬元,并承担訴訟費用。 這個結果讓錢先生和我們長舒一口氣,深感我們的法律還是公正的,它終究會與社會良知站在一起。侵權者的責任注定要被追究,哪怕他們有口吐蓮花的律師坐鎮,手握"尚方寶劍";哪怕他們有權威機構做靠山,而那權威機構號稱自己代表法律,這一切都無濟于事。 錢先生早就表示“此非為爭幾張鈔票”,他和楊絳先生商定,要在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得到賠償金后,他們將這筆錢和自己著作多年積累的版稅一并捐了出去。 (五) 一轉眼,這樁歷史舊案已經過去了20年,在我的記憶中,它原本已被淡忘。然而不久之前,我在網上無意之中發現一篇文章,題為《〈圍城〉(匯校本)十年祭》,作者是當年川文社策劃此書的編輯龔某,他在向讀者痛陳自己的委屈和苦衷,竟然也引發了我的頗多感慨。 我其實早聞龔先生大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界的知名學者。從他曾著有《〈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箋評》,可知他有心致力于現代文學的版本研究。他曾談到過自己希望出版一系列現代文學作品“匯校本”的設想。但是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圍城>匯校本》被判決“死了死了的”之后,“已經醞釀成熟”的一切都“胎死腹中”。 這場《圍城》侵權案的法律判決,成了中國知識產權案件中的一個著名判例。前車之鑒,足以使效仿者引以為戒。從那以后,人們的確再未見到其他現代文學作家和作品因為“匯校”而被侵權。我們當初設想,要在《著作權法》實施以后,為保護專有出版權“建立一個游戲規則”,這個目的似乎是達到了。 但是,現代文學作品可不可以“匯校”,需不需要“匯校”?不僅川文社的龔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而且他在學術界也獲得一些輿論支持。例如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先生寫了《為新文學校勘工作說幾句話》,他以郭沫若《女神》的修改和巴金的序跋為例,指出新文學研究者,常常是從一部作品的初刊文、初版本出發,也就是首先要做匯校工作,才開展研究的。因而他認為現代文學作品的“匯校本”是為適應這種高層次的研究而出版的,“匯校本”包含了匯校者的嚴肅勞動,對于新文學研究的工作大有益處。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先生甚至認為《<圍城>匯校本》案的審判結果是禁止了現代文學“匯校本”的出版,這對于現代文學的研究“損害是嚴重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新版《圍城》精裝本 “匯校本”被禁絕,這令我們始料未及。在這場爭論中,無論是錢先生還是我們,考慮的都只是如何為作者和出版者“維權”,而不是要封殺一種類型的演繹作品。其實在我們看來,如果文學研究確有需要,一些現代文學作品“匯校本”自然就有存在的理由。但這種存在,應該是針對少數研究工作者的,當然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而且應當是取得作者授權和專有出版權所有者許可的。 這里關鍵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根本沒有人“禁絕”過現代文學作品“匯校本”,但是多年來無人問津此事,恐怕是這一條限制了出版者的積極性。其實,如果出版者肯于“不以營利為目的”支持現代文學研究,要把“匯校”作為一項宏大事業恐怕也并不難(當然也需要原作者接受)。例如商務印書館計劃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文庫》,其中很多品種涉及兄弟出版社的專有出版權,但商務“文庫版”不以營利為目的,限量出版幾千冊,與其他兄弟社協商版權使用,多獲支持。所以“匯校本”出版者其實大可效仿這種合作模式。話說回來,當年川文社的《<圍城>匯校本》被禁止出版,原因并不在“匯校”的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是以營利為目的,進行了不正當競爭,“違背誠實信用和社會公德原則,擾亂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法院判決書語)。獲得道歉賠款的判決結果,是賴不到“匯校”頭上的。 對此,龔先生的《〈圍城〉匯校本十年祭》里也做了一點反思。他說: “我也想到一些“如果”,或許可以使惡因緣轉為善因緣。” “如果《〈圍城〉匯校本》發行總量不高達十多萬冊,只印五千冊且永遠也賣不完,錢鍾書先生和人文社當不會打官司吧?” 這話大致靠譜。果真是這樣,雙方一定會像陳早春社長說的那樣,“兄弟社,好商量。” 龔先生還十分感嘆地說: “四川文藝社確實沒有得到《圍城》作者的書面授權,又確實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十多萬地印行,我這個只有權利認字的責任編輯實際上什么‘責任’也負担不了!連封面上的‘匯校本’被挖去,我至今都不清楚系誰人之主張!稍有常識的讀者都知道,‘匯校本’三個字就是我弄這本書的品牌呀,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的某些同行,為什么這樣傻------你們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嗎?” 他意識到,對他這個“失控”的策劃人來說,事情的結果可能和初衷背道而馳。進入商品社會以后,在某些出版機構里,圖書的出版在商業的剛性目的面前,其學術的追求通常是軟弱無力的。我能理解他的一些苦衷。 此外,他提到的另外一事令我感觸頗深,文中說: “北京友人代我從潘家園弄來一堆當年各色人等關于《〈圍城〉匯校本》官司的多種書信、手跡復印件材料,有錢鍾書先生的好幾封信,有人文社負責人和人文社版《圍城》責編的信,有之前公開贊揚《〈圍城〉匯校本》但官司一來就馬上向錢鍾書向人文社‘說明情況’的京滬著名學者的信,有四川文藝出版社時任社長的信……總之,都是‘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些史料價值極高的出版檔案,竟然成了龔先生的收藏品! 我已調離人文社多年,對于該社疏于檔案管理,我無話可說。 但這可能就是我舊事重提,寫下這篇文章的一個動因。 2015年2月5日-7日 原載《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2期 作者系三聯書店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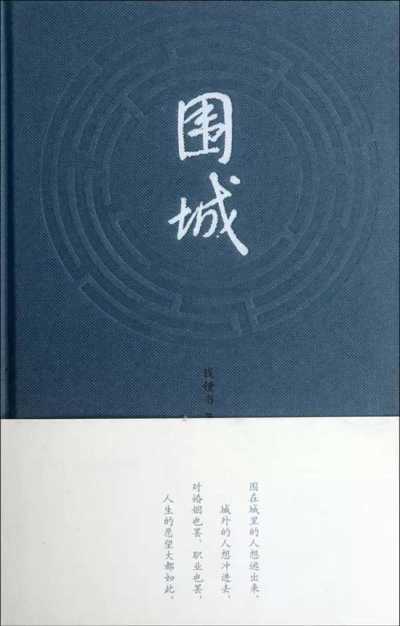
燕南園愛思想 李昕 2015-08-23 08:53:4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