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一部多災多難書稿的坎坷傳奇歷程----《愛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訂后記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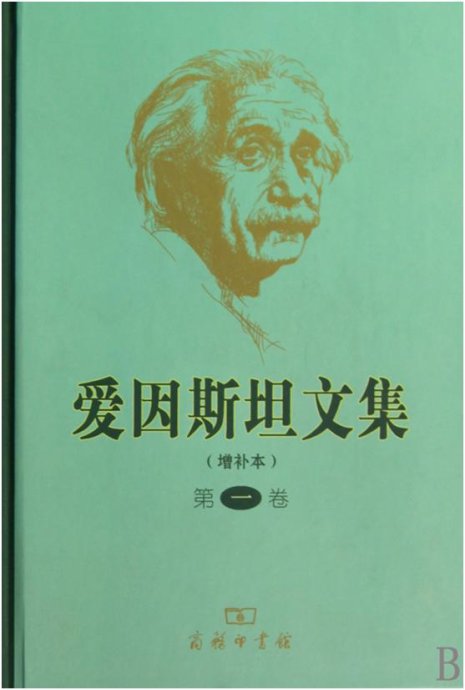
一部多災多難書稿的坎坷傳奇歷程
我大學時學物理,初中二年級就崇拜愛因斯坦,1938年考大學前認真讀過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觀》,使我開始思考人生道路問題。兩年后決心投身革命,1946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館參加中國共產黨,1947年任地下黨浙江大學支部書記和杭州工作委員會委員。1952年調到中國科學院,負責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關”和《科學通報》的編輯工作。1956年調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1957年因公開反對“反右”斗爭,被定為“極右分子”,失去黨籍和公職,回老家當農民,用勞動工分來養活自己和母親。
1962年哲學所所以要組織編譯科學哲學著作,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1959年開始,中蘇關系逐步惡化,隨后展開公開論戰。中國領導人企圖取代主張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赫魯曉夫,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中心。為此,必須批判全世界一切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潮,各國著名自然科學家的有關思想自然是重點批判對象。因此,必須把這些科學家的哲學著作和社會政治思想言論編譯出來,供批判之用。鑒于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他就成為當局第一個關注的對象。讓我編譯愛因斯坦著作,對我是個喜出望外的大幸事,立即全力以赴。
為了解決我的生活問題,他們把我1956-57年譯成留在北京的譯稿《物理學的基礎》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費向生產隊購買工分,換取口糧。隨后我去北京住了4個月,查閱了所能找到的愛因斯坦全部論著,擬定了選題計劃,并于1963年3月同商務印書館簽訂了正式約稿合同。
1963年5月,我回家鄉,帶回由商務印書館幫助借出的十幾種愛因斯坦著作和十來種有份量的愛因斯坦傳記。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1960年剛出版的由愛因斯坦遺囑執行人那坦(Otto Nathan)和諾爾登(H. Norden)編的文獻集《愛因斯坦論和平》,它全面地搜集了愛因斯坦一生的社會政治言論。回家鄉后,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了這批珍貴的文獻。
我首先狼吞虎咽地讀完了700多頁的《愛因斯坦論和平》,對他的社會政治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發現他終生信奉社會主義,雖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但向往計劃經濟,對馬克思、列寧和俄國十月革命都有好感。因此,在政治上,他應該是我們的團結對象,不應該當作敵人來批判。這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編譯他的著作,介紹他的思想了。我日夜埋頭于書稿之間,一天工作14小時以上,每夜點著油燈工作到0: 30以后,沒有休息日,連春節也顧不上。
在北京期間,偶爾獲悉上海科委秘書李寶恒也曾計劃編譯愛因斯坦著作,于是寫信約他合作,他欣然同意。但他工作忙,又未受過嚴格的基礎科學訓練,只分担了小部分翻譯工作。
經過歷時一年半的緊張工作,到1964年10月完成了原定計劃,選譯了200多篇文章,50多萬字。書名《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實際上包括了他有代表性的科學論文和社會政治思想言論。由于國內階級斗爭的氣勢越來越猛,出版進程受阻。利用這段空隙,我寫了一篇9萬字的《編譯后記》,并在此基礎上寫了一部17萬字的專著《愛因斯坦的世界觀》稿。
為了試探外界反應,我把《后記》和《世界觀》兩稿中論述哲學思想部分的要點,寫成一篇25,000字的論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經李寶恒略加修改(在頭尾加上當時流行的套話)后,聯名寄給哲學所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這個刊物是我1956年在哲學所創辦的),發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因為我是“摘帽右派”,不準用真名,只好改用筆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對此文很贊賞,認為學術批判文章就應該這樣寫,要《紅旗》雜志轉載。于光遠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寫的,黨刊不能登右派文章,于是要李寶恒把它壓縮改寫,用他一人名義發表。
當李寶恒興沖沖地寫出準備送《紅旗》發表的文稿時,史無前例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因此成了“閻王殿”(指中宣部)在上海的第一個“黑幫分子”,受到沖擊。頃刻間,好運變成了厄運!
二
“文革”一開始,我恢復了全天勞動。隨后經歷了長期的審查、監禁、批斗,以至死亡的折磨。在生死風暴過去兩個月后,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場風暴,這就是北京和上海掀起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
1969年11月,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陳慶振帶著科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來到我的家鄉,要向我借愛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譯稿,說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已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定為理論批判的重點,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出版的《紅旗》雜志上發表。我告訴他,愛因斯坦著作的譯稿全部在上海李寶恒處。他說上海也在組織批判愛因斯坦,兩地的資料互相封鎖。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資料卡片全部借走。他為人正直,說自己原是學化學的,不懂相對論,要在批判中學習相對論。我坦率地告訴他:愛因斯坦無論在政治上、哲學上、科學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開批判他,會損害我國的國際形象。
1971年10月從報上獲悉商務印書館改名為“東方紅出版社”,并已恢復業務,我即去信詢問《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的出版問題。答復是:立即寄去成稿,以便決定。于是我向李寶恒索要。他告訴我,《愛選》和《世界觀》兩部書稿都于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強行“借用”(留有沈賢銘具名的借條),他們不愿歸還原稿,只允許由他抄一份還給我。我不同意,寫信給沈賢銘和“寫作組”,要求歸還原稿,他們置之不理。以后打聽到“寫作組”的頭頭叫朱永嘉,1972年2月28日給他寫了一封掛號信,告知我將于3月下旬去北京(當時科學院副秘書長秦力生答應為解決我的甄別和歸隊問題出力,主動要我去北京),要求他必須在我路過上海前歸還兩部書稿,否則將訴諸法律。3月23日,他果然把《愛選》書稿交還李寶恒;但《世界觀》稿卻推說“下落不明”,顯然是因為這部書稿對他們正在進行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十分有用。
1972年3月29日,我把《愛選》稿帶到北京交給商務編輯部,一個星期后就得到答復:此稿重要,決定盡速出版;并表示愿意出版未見下落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稿。在北京兩個月,甄別、歸隊全都落空,但發現了不少9年來國外新出版的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資料。于是繼續同李寶恒合作,分頭補譯新資料,并復核原譯稿。所以要復核,是因為原稿被上海涂改得不成樣子,必須一一核對原文才可定稿。我們預定10月交稿,商務也早已把它列入1973年出書計劃。
可是,來了一個晴天霹靂。9月18日獲悉,上海《科技書征訂目錄》上赫然有《愛因斯坦言論集》征訂廣告,所介紹的內容和字數同我們的《愛選》稿完全一樣,但編譯者卻是“復旦大學《愛因斯坦言論集》編譯組”。為了揭露和抗議這種明目張膽的強盜行為,我寫了一篇7,000字題為《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件怪事》的文章,寄給上海市革委會頭頭徐景賢。10月12日我帶了全部《愛選》譯稿到上海找朱永嘉交涉。4天后朱永嘉派代表找我談判。那個代表先向我傳達朱永嘉的四點“指示”:(1)承認《言論集》是以我們的譯稿為基礎的,可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給我稿費;(3)商務那邊的出書問題不要我過問,由他們聯系解決;(4)可考慮安排我的工作問題。這分明是企圖用名利來引誘我就范,我不為所動,堅持由商務按原計劃出書,你們只能出個節本,并要由我負責看改校樣。我看他們毫無知錯之意,批評他們的行為是強盜行為。談判不歡而散。第二天他通過李寶恒通知我,朱永嘉認為他們出書與我無關,不要我看校樣。
為抗議上海寫作組的強盜行徑,我寫信向周恩來總理申訴。申訴信請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和秦力生副秘書長轉。他們征求吳有訓副院長(物理學家)意見后,轉給國務院。這封由科學院出面轉交的申訴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們派上海人民出版社兩位負責人到北京找商務印書館負責人丁樹奇、陳原協商,達成協議,并上報國家出版局。協議規定:上海的書改為內部發行,商務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不受上海影響。
上海的抄稿經過改裝,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書名改為《愛因斯坦論著選編》,原來的“編譯組”不見了,但在《編譯說明》中列了復旦大學12位教師(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說是他們“集體編譯”的,并說“在編譯過程中,曾參考過許良英、李寶恒于1962年至1965年間的舊譯稿。”可是,全書有94%的內容是從我們的譯稿中抄去的,而原稿尚未發表,竟被稱為“舊稿”;強取豪奪被冠以“參考”美名,還要盜用十來位無辜教授的聲譽,來壓倒我這個沒有公職的“摘帽右派”,用心何其良苦。
三
我到北京后,商務把我新擬的選題計劃打印出來向有關人士征求意見。國家科委一個干部對書名《愛因斯坦選集》大加指責,認為“選集”只能用于革命領袖,現在要給“資產階級科學家”出“選集”,用意何在?于光遠建議改名為《愛因斯坦文集》,我也就同意。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萬字)終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個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時發排,在當時是一個奇跡。因為1973年秋冬全國刮起了所謂“反右傾回潮風”,1974年春又掀起了更加兇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一切被貼上“封、資、修”標簽的東西誰都不敢出版。連早已編輯加工好了的黑格爾的《邏輯學》這樣的譯稿,商務也不敢發排,唯獨《愛因斯坦文集》發排了。這要歸功于一年前商務與上海訂的協議。
這個時期,上海寫作組正在通過他們控制的《復旦學報》、《自然辯證法》等刊物公開拋出一系列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付排,正是對這種張牙舞爪的權勢的蔑視。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務越燒越旺,原來的領導人丁樹奇、陳原靠邊站,換了兩個不學無術的打手。他們敵視我這個右派,于11月下驅逐令,但當面騙我,說讓我回老家繼續搞《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證按月寄生活費。可是我回故鄉后不到兩個月,他們就停發了我的生活費。正當我的生活將陷于絕境時,恩師王淦昌先生得到這一信息,主動來信,說我以后的生活費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從四川寄給我30元。王先生從1960年開始參與我國極機密的原子彈、氫彈研制的領導工作,現在居然要包我這個右派學生的生活費,將承担何等的風險!好在幾個月后中國政治風向又稍有轉變,商務恢復了我的生活費。《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42萬字)也于9月交了稿,由范岱年在北京代我處理。
隨著政治氣流的回旋,1975年10月我又回到北京。這次是趙中立要我來的。他寫信告訴我,國務院成立政策研究室,于光遠是主要成員之一。這個室領導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工作,這是我爭取回哲學所工作的好機會。這次來,當地公社(即鄉公所)不給出行證明(當時買到北京的火車票都要證明),商務也不予接待,不得不作為“黑戶口”住在趙中立家,一住就將近半年。剛到北京時,恢復工作確實有希望。可是,一個月后風云驟變,刮起批“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風,一切都成為泡影。本來我又得回老家了,因為商務在接受《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稿后,表示第三卷能否出版是個問題,理由是這一卷全是社會政治言論,會引起麻煩。幸虧我到北京后,于光遠通過出版局局長石西民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11月商務通知我:同意我繼續完成第三卷的編譯工作,生活費發到1976年底為止。由于第三卷內容性質,我約請老同學張宣三參加翻譯。
1976年3月,商務終于讓我回招待所住,在辦公室里工作。半個月后,在我每天早晚必經的天安門廣場爆發了因悼念周恩來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事件。7月下旬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整整一個月只能露宿街頭。人禍天災到了極點,苦難的民族終將重見生機。
四
拿到樣書,我百感交集,而病魔也在步步緊逼。回到招待所后依然咯血不止,第二天半夜一連咯了一茶杯的血。隨后我被送到北京結核病醫院。奇怪的是,住了兩個月院一直沒有查到結核病菌,于是醫生懷疑我患的是肺癌,許多朋友都以為我活不久了,紛紛趕來探望,我泰然處之。可是最后也沒有查出癌變的跡象。事后估計,當初患的可能是急性支氣管炎。在結核病院住了將近4個月后回到商務,編輯室主任高崧和陳兆福很照顧我,讓我住在辦公室里,邊工作邊休養。
1973年商務與上海方面協商并上報出版局的協議中規定,《愛因斯坦文集》按原計劃公開出版。但1976年1月第一卷付印時,商務當權者卻下令改為內部發行,而且規定封面不得用紅色,書名不能燙金。理由是,資產階級不配用神圣的顏色。于是,封面選用素雅的淺綠色。這引出了一篇報告文學《綠色的文集》(作者為新華社記者胡國華,刊于《瞭望》周刊1984年第37期)。第一卷印了25,000冊,1977年1月開始發行。雖然標明“內部發行”,但書店公開陳列,不到半年即告售罄。
1977年7月,商務決定重印《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并改為公開發行,要我寫一篇《前言》。我花了5天時間趕出15,000字的初稿,向周培源等科學家征求意見。一位專管政治思想的編輯室副主任認為此稿是“美化資產階級”,不能用。另一位曾受我尊重和信任的朋友來信說:此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勸我“頭腦不要發熱”,“放任靈魂深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感情冒出來損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這種“文革”時的標準語言,值得讓后人見識)既然阻力重重,我們只好請周培源先生寫序。他欣然答應,但要我們代為起草,說只要把原來的《前言》稿壓縮成5,000字,并參考他本人1955年發表的悼念愛因斯坦的文章。我一一照辦。
刊有周培源序言的《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重印版終于在1978年3月出版了。3月14日,愛因斯坦誕辰99周年,《人民日報》第三版全文發表了這篇序言。當晚,新華社以《中國出版〈愛因斯坦文集〉》為題,用中文和英文向海內外發布消息,介紹了周先生序言的主要內容,特別是對愛因斯坦的崇高評價:“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遺憾的是,這條消息中有一嚴重失實的內容,說《文集》的編譯工作“是由中國著名物理學家許良英主持”,我感到惡心,立即去信要求更正,嚴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學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過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公職的人民公社社員。編譯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們5個編譯者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難的同志,只不過選題計劃是我擬訂的,工作量也較大而已。
五
如今,為文集作序、傳承愛因斯坦衣缽的周培源先生,編譯文集最早合作者李寶恒,以及鄒國興、何成鈞、李澍泖三位朋友,都已作古,他們留下的珍貴文字是雋永的紀念。
《愛因斯坦文集》第二卷1975年9月發排,1977年3月付型,1977年11月出書。第三卷1977年12月發排,1979年10月付型,1980年3月出書。3卷共選譯了410篇文章,共135萬字。
在此之前,國外出過9種愛因斯坦的文集。其中以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觀》,1953年出版的德文版《我的世界觀》,1954年出版的《思想和見解》和1960年出版的《愛因斯坦論和平》最有價值。可惜前3種篇幅過于單薄,最多的不過122篇;最后一種又僅限于社會政治言論。1965-1967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愛因斯坦科學著作集》篇幅最大,有4卷,可惜只限于科學著作,不涉及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言論。相比之下,中文版《愛因斯坦文集》可以說是當時內容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
我們熱切期盼的《愛因斯坦全集》終于在1987年開始出版了。據《全集》編輯部報告,他們已收集到愛因斯坦的文稿約1,000件,書信9,000件。由此估計,迄今尚未發表的文稿將近20%,書信則在90%以上。《全集》最初計劃出35卷,后擴大為40卷,到90年代又改為20多卷。由于人們對《全集》期望值高,編輯人員盡心盡力,戰戰兢兢,主持人已換了4屆,迄今為止只出到第10卷,恐怕20年后才能出齊。這是一項世人矚目的宏偉的歷史工程,我們衷心祝愿它順利進展。
《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在剛結束“文革”噩夢的中國知識界引起不小的振蕩,對由胡耀邦所倡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1977年下半年,在青年工作干部會議上,胡耀邦說自己買到一本好書,叫《愛因斯坦文集》,他通讀了,除了有些部分看不懂以外,凡能看懂的,受到啟發很大。1978年9月我應邀參加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右派”改正問題的座談會。主持會議的同志告訴我,胡耀邦在中組部(他是1977年12月出任中組部部長的)干部會議上曾號召大家學習《愛因斯坦文集》。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開放和虛心好學的精神,也可以說明《愛因斯坦文集》的社會影響。80年代中期,報上曾公布大學生最愛讀的10種書的調查,《愛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
到1994年,《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印了4次,第三卷印了3次,市場上早已斷檔,要求重印的呼聲不絕。鑒于《愛因斯坦文集》成稿于30多年前,當時我尚沉溺于對意識形態的迷信之中。1974年雖然開始醒悟,但依然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在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過程中,凡見到有為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論點,總要在《選編說明》或“編譯者注”中加以批駁。現在重新審視,深感內疚,因為這是對愛因斯坦的褻瀆,是對讀者不負責任的誤導,必須予以更正。現在趁這次再版,把我當初所加上去的這種意識形態的污染一一清除,并在文字上作了適當校訂。同時,把第三卷后面兩個“補遺”全部拆散,其中80篇文章按時間順序分別編入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以求體例一致。此外,兩個附錄也作了必要的修改。這些處理是否得當,是否仍有污染的余跡,懇請批評指正。
2007年10月6日于北京中關村
供稿人:ZS-GJX
許良英 2013-07-10 16:13:03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