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徐志摩的康橋和納博科夫的浴袍 讀藥周刊
 |
>>>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 簡體 傳統 |
6 這個三一學院和徐志摩所在的國王學院同處一條街,相距不遠。兩者之間僅隔著另外兩個學院,圣約翰學院和岡維爾-基茲學院,后者俗稱基茲學院。劍橋大學的主體,與牛津和歐洲其它古老大學一樣,是由幾十座本科生學院——即開明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這是我自己的譯法,因為“博雅學院”的譯名含糊其辭——組成的。至二十世紀初年,劍橋已擁有23個本科生學院,現在擴充到31個學院。本科生生活在各自的學院里,但他們可以在劍橋大學的任何院系選課。我猜想,當年徐志摩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頭戴黑方巾、身披黑披袍的劍橋學生的時候,未必沒有看見納博科夫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走過。我甚至懷疑,在1921年初夏的某一個清晨,徐志摩可能與穿著紫紅色睡袍的納博科夫在三一巷的拐角處不期相遇,但彼此并不認識。 兩人擦肩而過,各自走向一個未知的命運。 人們很難想像,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劍橋并不像今天這么平和寧靜。在那時,這里是一個充滿激烈理念沖突的地方,空氣里充滿了硝煙——思想和思想的交鋒同樣是真正的戰場。從納博科夫的回憶和其他劍橋人的記載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到當時的氣氛,在這里,英國同學柰思畢特的出場尤其關鍵。柰思畢特信仰社會主義,這樣的年輕人在劍橋大學的中間很普遍,他們都想從納博科夫的口中了解一些關于俄國革命的事情。比如,柰思畢特經常找納博科夫聊天。這人身材修長,舉止優雅,顯然來自于有教養的家庭。兩個人聊天的時候,柰思畢特會不停地擺弄他的煙斗,一邊抽煙,一邊耐心地聽著納博科夫對俄國革命的抨擊。 但無論如何,你必須承認列寧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改變了世界,柰思畢特說。 沒錯,他改變了世界,納博科夫激烈地反駁道。你知道他是怎樣改變世界的嗎?英國人孤陋寡聞!你們聽說列寧殺人如麻嗎?你們聽說多少人被布爾什維克扔進牢籠,遭受酷刑,被流放嗎? 柰思畢特倚在壁爐旁邊,把煙斗在壁爐臺上磕了幾下,叩出里面的煙灰,他的兩條長腿換了一個姿勢,又重新悠閑地交叉起來;那兩只手始終不停地動作,他不慌不忙地把煙絲裝好,打火,點燃,深深地吸上一口,這才把煙斗從口中拿開,繼續說道: 你家人的不幸,我說過我很同情,但你別忘了,列寧發動的是一場從未有過的革命,革命能不流血嗎?何況,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封鎖,特務間諜天羅地網,時刻在威脅著它的生存,你說它能不整天緊張,有過激的反應嗎?再說,從前的沙皇統治殘暴不殘暴?列寧推翻的是沙皇統治,還有你們這些白俄貴族,要不然,他怎么能讓工人農民當家作主? 納博科夫寸步不讓,他說:像你這樣整天坐在安樂椅上的社會主義信徒,不如搬到蘇聯去住著,你去親身體驗一下蘇維埃政權的厲害好不好?我敢打賭,列寧會把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全部趕盡殺絕,就像農民捕殺野兔那樣毫不留情,到時你還唱什幺高調?剛才提到沙皇時代,我告訴你,即使在沙俄最黑暗的年代,我們還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是現在呢?現在…… 柰思畢特把煙斗從嘴里拿出來,在空中做了一個優雅的手勢,打斷了納博科夫的話。 他笑著說:恕我直言,自由言論從來就不是貴國的傳統,這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換個話題吧,我一直想問你,你怎么看馬雅可夫斯基? 陰郁 的雨 飛著斜的目光, 電線流著鐵的思想,—— 像鐵窗一樣 清清楚楚…… 柰思畢特一字不差地背誦了馬雅可夫斯基這首詩,納博科夫聽罷,沉默了一會說:馬雅可夫斯基的語言,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很有力量,我承認他的原創性超過魯伯特·布魯克,不過,我本人更喜歡普希金……哎,先不要轉移話題,你們英國人對俄國的了解太過膚淺…… 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是他們兩人共同喜愛的英國詩人,可惜他英年早逝,去世前曾是國王學院的寵兒。納博科夫在大學期間將布魯克的幾首詩歌譯成了俄文,經常和柰思畢特在一起議論他;他們當時還常談到另一位詩人,這人名叫郝斯曼(A.E.Housman),就生活在劍橋。納博科夫是三一學院的學生,郝斯曼是這個學院的院士,教授拉丁文學。晚上在學院的餐廳里,納博科夫偶爾碰到這位教授詩人,郝斯曼面色陰郁地往教員高桌那邊走,上唇的胡須像茅草一般地耷拉在嘴角兩邊,這一類的細節也成為納博科夫和柰思畢特的談資。在當時,布魯克和郝斯曼都是英國最知名的詩人,劍橋本科生喜歡在背后議論他們,是不奇怪的。 7 在英國同學中,柰思畢特最早成為納博科夫的朋友,說不定也是他惟一的英國朋友。有了這個當地朋友的引導,納博科夫才有幸進入劍橋大學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了解并且遵守劍橋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禁忌。本科生的這些禁忌不但繁復,而且讓納博科夫,也讓今天的人覺得怪異。比方說: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況下,見人都不握手,不點頭,不問早安。碰見熟人,包括碰見教授的時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聲就行了。 禁忌之二,無論天氣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這一條其實不易遵守,原因是納博科夫最不喜歡穿英格蘭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 禁忌之三,不得被學校制定的任何規矩所束縛,絕不循規蹈矩,晚上需要翻墻時,就翻墻。 新朋友柰思畢特身上有一種頹勁,這叫納博科夫很欽佩,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學上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兩人可以彼此欣賞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遠不可能與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說在經常的辯論中說服他了。那個時代的劍橋大學,像柰思畢特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有一大堆:費邊社會主義、共產黨、工黨、女權主義、布盧姆斯伯理團體(Bloomsbury Group)、使徒會、邪學社、裸體派等,這些人聚在一起時,總是進行無休無止的思想辯論。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以后,這些英國人全都對俄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注意到劍橋大學新到的幾位俄國留學生,這些俄國學生是尾隨父母,來到西歐國家避難的青年。 一天下午,納博科夫被一個左翼學生團體叫去做公開講演,請他從白俄流亡人士的角度談談俄國革命,為當地的聽眾現身說法。這對納博科夫來說,難度不小,因為他一直不善于在公眾面前講話,也不喜歡卷入政治,更不必說做政治演講和辯論,所幸的是,他有超人的記憶力。此刻,這個特長幫了他的忙:納博科夫的父親曾是沙俄時代的杜馬議員,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論家,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言論,當時就在柏林主編一份由他創辦的俄國流亡人士的報紙。納博科夫找來父親的一篇時政論文,在主席臺上把它流利地背誦了一遍,大意是譴責列寧的一黨專政,指責布爾什維克斷送了俄國的民主前景——我們可以猜想,納博科夫當時背誦完畢之后,定然大大松了一口氣,但當時的場面卻出乎他所料:這番背誦結束后,臺下的聽眾馬上舉手提問,一個接著一個的尖銳問題,猶如萬炮齊轟,不善言辭的納博科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搪塞幾句,倉皇逃跑。 不久以后,劍橋大學右翼學生的一個組織也開始向他靠拢,希望拉他參加右翼團體的活動。但納博科夫很快就發現,這些人向他示好的原因很簡單,純粹為了反共,他對這個淺薄的理由是很不屑的。又過了一段時間,他注意到,這個右翼團體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出于各種不同的動機湊在一起的雜牌軍,他們各自心懷鬼胎,其中既有老牌帝國主義的吹鼓手,有種族主義分子,還有來自俄羅斯的白俄流亡人士。對那些失去家國的俄國同胞,納博科夫尤其感到失望,他們斤斤計較于個人得失,一面為自家的房產地產被剝奪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卻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對克倫斯基,還是反對列寧,納博科夫后來在自傳里寫道: 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始于1917年,但我的不滿與財產之類的事情毫無關系。有些白俄移民“痛恨赤黨”,因為赤黨“偷走了”他們個人的錢財和地產,我對這種人的蔑視簡直無以復加。多少年來,我思念我的故鄉,因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復還,而不是在哀傷一大疊丟失了的鈔票。 納博科夫認為,這些右翼人士狹隘自私、頭腦混亂,如果與他們為伍,那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他也感到很無奈,因為他不得不繼續忍受柰思畢特的列寧主義和他的煙斗。 事實上,納博科夫的家族和沙俄時代所有的顯赫世家都一樣,在1917年的革命風暴來臨之前,一直享受著貴族階級的絕對特權。在孩童和少年時代,納博科夫和他的弟妹們,多數時間都是在彼得堡郊外的魏拉公館度過的,那里是孩子們的世外桃源,家中僱傭了五十多個奴仆,伺候他們的起居。納博科夫從小陶醉于魏拉公館周圍的自然風光,他讀書、下棋,到河邊散步;高興時,鉆進濃密的杉樹林里面,捕捉罕見的蝴蝶標本;稍后,他把自己心愛的姑娘帶到那里去幽會。維拉公館的平靜生活是如此天經地義,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納博科夫十九歲的那一年,所有的這一切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化為煙塵,他自己一下子成為一名落難公子。在一家人顛沛流離逃往外國的路途中,納博科夫首次品嘗到人生的心酸。 《六個字母的解法》/劉禾/中信出版社/2014-0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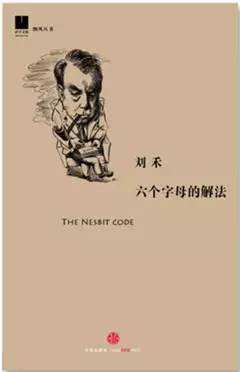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1:3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