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論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之誣
(錄自《追憶吳宓》,李繼凱、劉瑞春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吳宓日記》無張紫葛三字
帶著4000冊書逃難!
關于朱小姐
不知仲旗公之名
《觀且感》真相
死人教沒有出生的人!
《黑夜送別》是捏造
厚誣陳吳二先生之交
顛倒了吳先生
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陳先生之孤懷卓犖、高風亮節。近有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一書,自稱與吳先生為38年的生死之交,是書之作,乃為“以心香之誠,淚酒之悲,紀其實而存其真”,在封底更揭曰:“謹以此書祭奠吳宓,祭奠千千萬萬在中國史無前例的文革劫中,含憤忍冤殞沒的莘莘學者書生;并祈愿,哀慟不再,災患不再,悲劇不再。”果如此,則其用心立志可謂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歡迎了。此書確實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讀者歡迎。以陳吳兩先生之一世深交,以兩先生之思想與共,以兩先生之道德高尚,以兩先生之學術覃深,兩部據實記述二先生之作,應該可成雙璧。然而,細審之下,大謬不然。陸書言必有據,信而可征,根據大量檔案資料、文字記載和訪問筆錄,寫出了真實,寫出了真實可信的陳先生及其時代背景。張書則多向壁虛造,穿鑿附會,虛構了一個吳先生,乃成對吳先生之誣,對吳先生道德人品之誣。雖假托至交,編飭成書,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讀者于一時,畢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吳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時,以其方而時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為人織造了一個顛倒了的形象。但是,罔其非道,則萬萬不能,雖不能起吳先生于地下而辯之,吳先生的友人仍在,吳先生的學生還在,學界人士愛吳先生尊吳先生者多多,辨別是非真偽,大義所在。忝為吳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為辯誣。其已見于季石《〈心香淚酒祭吳宓〉質疑》(1997年5月29日文匯報《筆會》)者,不贅。
吳先生一生寫《日記》不輟,這已是學界所共知。與吳先生熟悉的朋友,看過吳先生《日記》的人更知道,凡與吳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緣,吳先生也在《日記》中記上姓名及因何得見。數年前,吳先生女公子學昭整理先生《日記》,即告我寫一簡介以作《日記》注解,說是《日記》中寫及我。所知,在上海同時被通知寫簡介者,尚有同學多人。我們這些同學,當年都讀了吳先生的教課,男同學且與吳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觸不算是很少,吳先生筆而記之,猶可說。友人王勉,是西南聯大社會學系畢業的學生,在聯大讀書時未選讀吳先生教的課程,只是一次日機空襲昆明,在防空洞中與吳先生相遇,交談數語而已,昨日晤王君,說是也曾得通知寫一簡介,以備《日記》之注。可見吳先生《日記》不漏相識之語不虛。張紫葛先生自稱與吳先生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記》中不見半點蹤影?張紫葛為此在書內精心編造了一個吳先生“改造日記”的神話,說是吳先生為了保護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張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簡單地抹掉,而是徹底地改造,剪裁,重寫,裝訂,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無縫”。此等神話,徒令細讀《吳宓日記》的季石厥倒,季石《質疑》之文詳述其事,人當服其文之可信。《吳宓日記》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寫原樣,將陸續出版,國人得而共讀,張紫葛為此不經之說,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張紫葛在書中《后記》(頁455)有一段話:“至抗戰前夕,他(指吳先生)的私人藏書已逾(按原文誤為愈)萬冊。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長沙時,他選帶了4000 本之譜,其余均寄存在北京親戚家中。經過長沙南逃,過香港,轉云南,所帶圖書少有損失(振常按,不知是否為稍有損失之誤)。于1939年挑了1000余冊贈給了西南聯大圖書館。1944年至成都,鑒于內遷的燕京大學圖書嚴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冊贈給燕京大學圖書館。”按,吳先生于1937年11月7日偕毛子水等離平赴津,乘船至青島,登膠濟火車,到漢口,又換乘粵漢火車,走走停停,于11月19日到長沙(據吳學昭)。路上行程共12天。以一文弱書生(加上陪行的幾位)竟能在交通困難、旅途擁塞的抗日戰火中,攜帶著4000冊書的重負長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張紫葛先生是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他自己能相信嗎?
吳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學之時,我正就讀于燕大,未曾聽說先生向燕大圖書館贈書的事。那時我們圖書館的書,的確少得可憐,小小一間書庫,大約千余本而已。圖書館主任是梁啟超的女公子梁思莊女士,同學和梁女士都常埋怨書少。如果吳先生一下贈書千余冊,是件大事,會傳開來的。張書中沒有提吳先生贈送的千余冊書是自己從昆明帶到成都,還是后來托運到成都的。按吳先生于1944年8月23日自昆明出發,經貴陽、遵義、重慶、白沙到成都,于10月26日傍晚到達成都,時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戰后期,交通情況更壞,所以吳先生行程竟長達兩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帶著1000多本書經此長行。為張紫葛解,好在他沒有說吳先生是親帶千余冊書同來的。吳先生和我們同住在華陽縣文廟的男生宿舍,猶憶吳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行李簡單,書籍無多,孤燈如豆,極為凄涼。此題所談是極小的小事,雖極小之事亦作偽,大事如何,可知矣。
張書(頁269~275)講了一段所謂朱小姐偕其兄于1953年4月自天津遠道來重慶探望吳先生的事。抗日戰爭開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讀書,吳先生在此校兼課,朱小姐是吳先生的學生。吳先生由北平南下,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長陪吳先生南下至長沙。據張書所述,朱氏兄妹此時忽來重慶,實因朱小姐在北平時就愛上了吳先生,此來欲圓舊夢。到渝后,才知吳先生已經和鄒蘭芳結婚,乃向張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去。張書此前寫到吳先生“改造日記”事謂:“1937年冬離開北平一節,刪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護吳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刪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長沙情節。理由:如此情節留于日記中,也被認為汝吳宓處處惹草拈花,實為一‘道德敗壞之徒’。”(頁147)
按,季石所寫對張書的《質疑》,談到張紫葛所謂吳先生刪去有關朱小姐情節,季石文發表在《筆會》時此節被刪,茲引錄季石原稿如下:
“事實上,吳先生現存日記里詳細記述了抗戰開始時離北平南下的經過。如果真有朱小姐隨行,也實不必刪。因為吳先生當日照護同行一路到長沙的女生不是一個,而是三個,其中有陳援庵先生的女兒陳慈,卻沒有朱小姐,也沒有她的哥哥。當年是如何動身的,路經哪里,乘車乘船都發生了什么事,吳宓日記里可說是巨細無遺。當年的隨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歷史豈是可以亂改的。至于朱小姐,確是在北平時吳先生的學生,與她的交往,在現存吳宓日記中也記得很具體。而吳先生日記所記與女性學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記錄自己對她的觀感和想法。這些內容都完整保存,當然也無必要單單刪除有關與某一女學生來往的記錄,何況日記中有關朱女士的內容歷歷俱在,并沒有刪除。”
張書自稱在認識吳先生之前,先認識了吳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為吳先生叔父。吳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與仲旗公為子,稱仲旗公為父、嗣父,稱自己父親為爹。先生終生敬事仲旗公,情過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與吳先生訂交的。張書詳記經過說,1939年他在重慶,時去于右任家或衙署,“彼時,我見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這就是于公尊稱為‘吳公’或‘仲旗公’的貴客。”“既然我們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談。吳公熟悉經史,尤愛春秋三傳,我更少年意氣,喜縱談諸子百家之說,因而一老一少,頗為投機。”一天,仲旗公問張知道吳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吳先生是父子關系,即對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吳先生,愿為吳先生弟子,請仲旗公為之介紹。仲旗公表示愿介紹他們做朋友。“大約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張紫葛應于右任電話召去于府,得見仲旗公偕吳先生在座。仲旗公對吳先生和張說:“希望你們做個兄弟般的朋友。”張表示愿對吳先生執弟子禮,吳先生則以為張是宋美齡的秘書而“不敢高攀”。“吳老太爺頗為不悅:‘你怎么說這些生分話?我斟酌久之,才給你們慎重介紹。豈可說出這些市俗客套話。’”于右任揀出張的兩篇文章給吳先生看,又說張是“后生可畏”,“將來未可限量”。吳先生當場看了文章兩遍,說是“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吳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學問。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張則堅持師事吳先生,還是經于右任一番開導,“就這樣,我們訂了異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不憚辭費,引述張書,凡未讀張書者,當亦從此段引述得見張紫葛說來似是確切可信了。事實并不然,季石《質疑》文已證,檢索吳先生《日記》,不但張書所指之“1939年吳仲旗先生卻根本不在重慶,而是在陜西西安。”又證:“事實上,吳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終就沒有到過重慶。”而張書所謂識吳先生之1939年8月初旬,季石列舉吳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辦的各種事務,亦無緣得去重慶。則張紫葛繪聲繪色描述的與吳先生在重慶于府訂交之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讀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張書既稱屢見仲旗公,“一老一少,頗為投機”,仲旗公并為他介紹吳先生“做兄弟般的朋友”,怎么會在他自稱“寫成《吳宓的第三個28年》(振常按,當即為《心香淚酒祭吳宓》之原擬名),已洽妥,即將出版”之際,于1995年12月3日寫信給吳先生幼女學昭,說是“專函請你協助兩事”,兩事之第一事為“校正我記憶未清的幾點”。其第一點,赫然寫著:“你祖父和兩位姐姐的名字。”天下事的怪異還有過于此的嗎?對于這么一位屢見的“頗為投機”的長者,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親,竟然不知其名?說是一時記不起來了。張先生在他的《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一書中,不是以他的驚人記憶力自負嗎?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齡賞識并得為宋的機要秘書,即由于他的驚人記憶力而起。在這本《心香淚酒祭吳宓》的《后記》中,不是也說他的記憶力絕對可靠,所記“絕對準確”嗎?此事有待于張紫葛先生指教。
據張書所述,吳先生于1956年給他看了先生從1956年6月24日至1956年10月4日所寫札記一冊,共30則不到。張自稱印象最深的是兩則,一則題《茍不教,性乃遷》,藉為J女生補習古文事,闡發有教無類思想。一則題《觀且感》,述吳先生于1956年9月30日晚參加中共重慶市委國慶招待會及10月1日參加國慶觀禮情況。(張書頁310~321)
張文詳述《觀且感》的內容及吳先生的感想。張文寫得有聲有色,長達四頁,謂吳先生于9月30日下午乘市里派來的專車,自北碚乘車入城。“市委的國慶招待會,富麗堂皇。陳設華貴,宴饌豐美。宴席連綿,琳瑯滿目。首尾宴桌之間,遙遠難辨人貌。濟濟多士,其盛大有似歐美之國宴。……一省轄市之國慶招待會都有如此規模,亦可概見今日中華繁榮之一般矣。”“宴罷,接以盛大的舞會。……場內如云之美女,衣履華麗美艷。有短裙半襪,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爭奇斗媚,卻是絕無藍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著脂,香氣四溢,余乃大為快慰。”當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甲級房間,衾枕清潔。”次日,乘車至市中心解放碑觀禮,又是大篇描寫,大段感想,無非夸游行隊伍之雄壯,堂堂中華之氣象萬千。且勿論孤懷卓犖、憂道憂世之吳先生能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現出如斯受寵若驚之狀態與否,從事實看,1956年中共重慶市委的國慶招待會、重慶市國慶游行,都只是張紫葛先生的虛構,吳先生參加而發抒感想之說,更是張先生的想象。
今據吳先生《日記》,1956年9月30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沒有進城。沒有什么人送來請柬,自沒有什么入城參加國慶招待會的事,而是在學校宿舍內“終日整理書物函稿”,“至深夜始寢”。10月1日先生倒是去參加了國慶慶祝會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區,規模并不盛大,如先生10月1日《日記》所述:“今年國慶節之慶祝游行,一切從簡。”所以沒有什么招待宴會,也沒有所謂的吳先生“登觀禮臺”,而是:“宓今日攜綠帆布鐵架義凳(又俗名馬乍子),在會場得安坐,免席地。”這一天的《日記》又記著:“晴,熱。國慶節。晨7∶30在操場集合,宓偕豫往。入隊,與史地系平、陶及呂烈卿(外文系)同列,隨校隊至北碚體育場。9∶00開會,11∶00畢。從平勸,宓與豫、陶徑歸,未參加游行。比宓等正午歸抵校,游行隊亦已散歸矣。”
事實就是這樣明白。張紫葛公然作偽。他為什么要作偽?看他書中寫1956年前后的吳先生,簡直活躍已極,對形勢極為樂觀,屢作“擁護”、“高呼”之談,盡是趨時媚世之調,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吳先生,也高呼“為……而干杯”。(按,張書杜撰吳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說,實則吳先生是喝酒的。)《觀且感》只是其一。1956年前后,階級斗爭的調子唱得少一些,形勢呈現緩和,確有不少知識分子為之歡呼,吳先生卻不是這樣的人,他始終是個遠離政治的學者,頭腦冷靜如初,厭惡政治如初,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如初。《觀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吳先生。不多舉,只引《觀且感》中一句:“今社會主義改造業已完成,實應舉國上下,萬眾奮發,致力于科學技術之精進,力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突飛猛進。”這就完全不符吳先生的思想。吳先生誠然贊成和擁護要搞經濟建設,但自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初識陳寅恪先生,多次傾談,即得共識:“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于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9~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華優良文化,維護中華優良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學技術與經濟建設,非先生之意也。張紫葛自稱與吳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顧吳先生一貫的思想,做此偽托,膽可謂大矣。
張紫葛確實膽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個死人來作他的老師。請看下節。
張紫葛記他經張季鸞推許,拜見于右任。其書第三頁這樣寫著:
于右任問及我的家庭和求學經過,嘆為苦兒困學。復問師承,我答:曾拜門于清進士吳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吳之英師與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贊吳師道德文章。又問先師授我何業,執何經。我簡單回答了幾句,說:“我拜門時先師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學無根底,有玷先師門墻。”
以上所舉,已經超越神話,只可于侯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得之,或者與近年為氣死歷史學家而編制的“戲說”的所謂歷史題材電視劇相近。奇怪的是,編造此說之時,或寫作這本“事實可靠”的《心香淚酒祭吳宓》之時,張紫葛為什么不去查一查書?
按,吳子英,字伯朅,吳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1957年(三秦記注:原書校誤,應為1857年),卒于1918年。四川尊經書院畢業。1887年后任通才書院主講、尊經書院都講、蜀學會主講、《蜀學報》主筆,推動戊戌變法。入民國后,任國學院院正。著有《壽櫟廬叢書》,是一位“熟精選理,尤好誦說司馬相如、揚子云之文”的人(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他是反孔健將吳虞(又陵)的老師,吳虞從他“問卿云之學,窮文章之奧”(《吳先生墓志銘》)。據香港90年代雜志社出版的張紫葛《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所載《作者簡介》:“張紫葛,1920年生于湖北松滋縣。”
這就奇了!一個1918年已經死了,一個1920年才出生,死了兩年的人怎么去收一個還沒有出生的人做學生,或者說一個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個方呱呱墜地的嬰兒做學生。此事之偽,不辯而明。
謊話還有。吳伯朅并無功名,不是什么進士,也不是與章太炎同窗同為俞樾弟子。四川尊經書院是張之洞為四川學政時倡辦的。主講為湘潭王闿運,吳之英為尊經書院學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學生。章太炎執贄俞樾是杭州的詁經精舍,非蘇州的春在堂。還有一層,吳之英所長是文章之學,由上引文可明,也就不會有于右任“又問先師授我何業,執何經”的說話了。開口便假,張君何以解釋。此事無關于張紫葛之記吳宓先生,讀之可作參考。
張書有《黑夜送別》一章(頁423~436),寫1976年11月吳先生將回老家陜西涇陽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劉尊一前來向張紫葛告別。張自稱于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滿后送回重慶北碚接受“群眾管制”。吳先生來向他告別時,他方被斗爭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吳先生和劉尊一叫住了,他們就是這樣在路邊告別的。書中(頁433~434)是這樣寫的:
今日吳宓收到陜西他妹妹吳須曼來信,打算叫她兒子(吳宓的甥兒)來北碚接他歸老家度晚年。吳宓決定今晚在這兒和我說幾句話。
吳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陜西老家,……我視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告別吧!”
后來,劉尊一告訴我,就在這黑夜送別后的第三天,吳宓的甥兒——他妹妹吳須曼的兒子突然來了。小伙子辦事伶俐,先找西南師范學院革命委員會辦好交涉,革委會同意他領吳宓回原籍去贍養后,他才來到吳宓的宿舍,見他舅舅。
張書又說,吳先生走時,有劉尊一送行。
這里有幾件事實須要辨清。一是吳先生被接回涇陽的時間,是在1976年12月。吳須曼在“文革”中,曾三次從涇陽來重慶探望吳先生,最后一次是在1976年12月來的,而非11月。這或許可說是張紫葛記錯了,那么,二,吳須曼是在12月到西南師院看見吳先生后,決定接先生回家,經先生同意,并得校方同意,同時電召其子王玕、女婿魯予生來渝接先生。其事極為倉促,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張告別?三,吳須曼之所以決定接吳先生回家,是因為她發現先生眼盲腿折,重病臥床,不能行走。吳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去向張紫葛告別,且是“黑夜送別”?四,書中所寫劉尊一女士,是張的老朋友,張書多次寫《日記》記及劉尊一,說是“素不喜其人”,從不來往。據吳須曼回憶,她接吳先生回鄉時,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無劉尊一其人。五,同據吳須曼回憶,三去重慶,從未見過張紫葛,也從沒有聽吳先生提起過張紫葛。這一點,只能留待張先生本人思考了。
張書《淡淡的悲哀》一章(頁348~353)厚誣吳先生,厚誣陳寅恪先生,厚誣陳吳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詞而辟之。
張書此章寫了吳先生1961年9月專程去廣州探望陳先生之行,開端似為陳吳二先生晤談做一總結,說是“兩人意見一致的是”,這已經夠怪了。兩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暢敘別情,切磋學問,哪里用得著類如發表公報一般的形式,標舉一致的意見?而所謂相一致意見的第一條是:“都希望神州大地像1956年那樣發展下去。”吳先生未曾對1956年有過幻想,已如上文《〈觀且感〉真相》所述,陳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學問,撰述名篇,絲毫不為外界風雨所動。管它什么東西南北風,吹不皺一池治學的春水。既寫兩人意見之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見,接下去,果然出現了“卻也小有分歧”的字樣。
“分歧”云何?張紫葛舉出1952年7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的吳先生關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標題為《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張居然說是,吳先生帶去了這篇文章,念給陳先生聽了。于是有如此一段妙文:
陳安靜地聽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詢問:“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無造作之詞?”“是的。”“秉筆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將刊之報端乎?”“當然知道的。”沉默。吳宓折疊收拾好文章,陳寅恪才說:“他們沒叫我寫這樣的文章。當然,如果叫我寫,我也是不會寫的。這一點,你比我強。”吳宓默然,未置一詞。內心卻對陳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贊成。但他未對任何人說過。(振常按,張書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為省篇幅,我把它連寫如上)
以上所謂“分歧”,全是捏造誣陷。據所知,吳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屢次檢查,未能通過,后在領導和同事“多方幫助”下,勉強再做檢查,文章乃被校方拿去公開發表,刊于重慶《新華日報》,相繼為《光明日報》及上海《大公報》全文轉載,吳先生對自己的違心之言和此種做法極為痛苦,時有自責之語。至同年10月2日有友人告訴吳先生,說是當局已將先生這篇思想改造文章譯為英文,對外廣播,“以作招降胡適等之用”,先生在當日《日記》中于此語之后,記下了“此事使宓極不快,宓今愧若人矣!”的痛心語言。《日記》中,同年10月3日陰歷中秋節,有《壬辰中秋》一詩,寫先生自責被迫寫思想改造文的違心,詩中有句云:“心死身為贅,名殘節已虧。”末句重申素志:“儒宗與佛教,深信自不疑。”此詩可以為先生作證。再引一事以為參證:吳先生是紅學大師,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時,吳先生自不能免被強令寫文章批俞。這一回,吳先生是頂住了,堅決拒絕,然對此深感內心痛苦,同年11月19日《日記》云:“自恨生不逢辰,不能如黃師(按指黃晦聞)、碧柳(按為吳芳吉)、迪生(按為梅光迪)諸友,早于1954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對于“批俞”之事,尚且感到如此痛苦,何況是切身所關的“思想改造”之自污乎?對于這樣一篇極感痛心的文章,還能加以張揚,講與人聽,又是讀給幾十年心靈共通的陳先生聽嗎?其事之荒謬編造,人共識之。再舉一例。《吳宓與陳寅恪》頁145,引1961年8月31日《雨僧日記》述陳吳二先生是日談話內容,在“其間宓亦插述宓思想”后,出版時刪去數字,意義大變,應為“其間宓亦插述宓思想改造、教學改革經歷之困苦與危機”,原意甚明,對于思想改造與教學改革不滿也。
張紫葛的編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層的對陳吳二先生的誣陷,接踵而至。緊接前文,所謂吳先生對陳先生的“壁立千仞”很不贊成而未對任何人說過的話,“直到1974年吳宓在本書作者的那間小屋里和作者敘述這段往事時,才一一引舉如下。”按張書所述,吳先生所不贊成于陳先生的事是,陳先生對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很欠明智”,“只可解釋為故意激惱對方”;紅專大辯論,大字報貼到陳先生家門外,陳先生不該生氣,不該詢問領導,不該提出辭職,不該提出搬出中山大學。如此等等,難于想象張紫葛是如何編織以陷陳吳二先生的。陳吳二先生已逝,說自由我說,但是,張紫葛忘了一條:吳先生廣州之行,留下了兩萬多字的《日記》。《日記》正在整理,陸續發排、出版以后,張紫葛何以對天下人?
張紫葛筆下此事未完。吳先生既有上舉“這么幾條(對陳先生)不以為然,卻是秘而不宣,這豈不是腹誹?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誹,大非朋友之道。別后,吳宓越想越覺不爽。”于是,吳先生便擬再訪陳先生,“俾得坦率直陳,討論討論這些不以為然之處。”其實,吳先生計劃再到廣州,完全是為了視陳先生折膝之傷(陳先生于1962年7月入浴時跌倒,右腿骨折斷),吳先生于1963年10月得知此事,因而計劃去看望陳先生。幾次計劃出發,均因故未成。此中過程,詳記于《吳宓與陳寅恪》中,此書連同《吳宓自編年譜》,吳學昭曾寄贈張紫葛。張紫葛只顧抄錄于他“有用”之處,不惜歪曲和編造其他事實。
吳先生確實對于陳先生說過“壁立千仞”的話,那完全是對陳先生崇高的頌揚。1961年9月3日,在廣州,中山大學陳序經先生及夫人請吳先生在陳家早餐,相對暢談,陳序經先生又談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習慣且安定矣。”(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頁146)則“壁立千仞”之語,可能是陳序經先生的原話,更可能是吳先生聽了陳序經先生對寅恪先生情況簡介后所作的概括,無論是前者或后者,都顯然是對陳先生的最高頌揚。“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試問,此種境界,不是對陳先生學問、道德、人格的頌揚是什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種境界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達到這個地步。而張紫葛卻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吳先生,以為是吳先生加于陳先生的微詞,何其妄也!
1961年9月,吳先生自廣州到北京,賀麟告訴吳先生,周揚曾主張調吳先生進京為中央文史館研究員,賀麟表示愿陪老師去見周揚,先生拒絕了。先生手訂的《吳宓自編年譜》(頁231)這樣寫著:“宓懼禍,辭未往。(若竟從之,后來周揚得罪,宓必致牽連。然謹慎不往,伏處西師,1968年以后仍受種種之懲罚與斗爭,則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論,周揚實為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到了張紫葛筆下,竟又拉扯上陳先生,顛倒為吳先生之拒絕訪周揚,是為了和陳先生比高低。張書(頁352)如是寫:周揚擬訪陳先生,陳先生先是拒絕,后經陳序經反復勸說,勉強同意。“到陳序經陪同周揚來訪,周揚態度謙遜,而陳寅恪卻很為矜持,并且主動問難。說有關領導人說話不算數,‘言而無信’。周揚耐心解釋,陳寅恪卻一再責難。然而周揚始終彬彬有禮。”(振常按,周揚后來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他那次“不該激怒陳先生”。張紫葛何以解!)張書接著說:“陳寅恪以周揚來訪,矜態相見。吳宓上訪周揚,還請賀麟先容。我吳宓與陳寅恪情同手足,學問雖自愧弗如,品格歷來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揚名下高下差別如此?兩相比較,能不自愧?”這是張紫葛論定吳先生拒訪周揚的一個理由,只能說是以己之心度君子。
陳吳兩先生一生的友誼,吳先生對陳先生的佩服尊重,兩先生心靈相通,患難與共,世所共知。張紫葛先生只顧自做文章,全不考慮。為了提醒張先生,于此稍加摘引陳吳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證明。1919 年哈佛初識,傾談定交,終身皆秉初旨。《空軒詩話》有文述:“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陳吳兩先生哈佛對談的內容,陳先生所談對于吳先生影響之深,具見于《吳宓與陳寅恪》一書所引《雨僧日記》,可為佐證。此后,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兩先生所談更廣更深,關系于中國文化之前途,立身處世之道,以及立學之本,亦可覆按。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對于兩先生影響極大,陳先生以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王觀堂先生挽詞·序》)陳先生在寫成此文前,對吳先生談了以上觀點。吳先生謹受教,而表示:“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范圍,惟有大小輕重之別耳。”這是兩位大師、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愴壯烈之語。吳先生讀王靜安先生臨歿書扇詩,有感寫成《落花詩》八首,痛陳文化衰落之苦,可參。因而,吳先生乃有王靜安先生靈前之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靈,他年茍不能實行所志,而淟忍以歿,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茍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吳宓與陳寅恪》,頁43)到了“文化大革命”,陳吳兩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陳吳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認識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便兩心相通,至死不泯,況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過爾爾,是以才有彼此間的關切。1961年,吳先生有廣州之行,后又多次計劃再去廣州,是一例。而在1971年9月8日,吳先生還戴著“牛鬼蛇神”帽子,在四川梁平勞動改造之時,竟以無畏的勇氣,寫信給中山大學,探問已經逝世兩年的陳先生下落。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靈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辦。小而至于,1944年吳先生之離開西南聯大到成都燕京大學授課,就是因為陳先生到燕大去了,“遂決即赴燕京,與寅恪、公權(按為蕭公權先生)共事共學。”(《吳宓與陳寅恪》,頁110)甚而夢寐之間,吳先生亦念及陳先生。如1952年12月30日,《日記》記:“28日未曉,夢與陳寅恪兄聯句,醒而遺忘。”(《吳宓與陳寅恪》,頁133)1971年1月29日《日記》記:“陰,晦。上午身體覺不適,心臟痛,疑病。乃服狐裘臥床朗誦①王國維先生《頤和園詞》,②陳寅恪君《王觀堂先生挽詞》等,涕淚橫流,久之乃舒。”(《吳宓與陳寅恪》,頁154)1973年6月3日《日記》記:“陰雨。夜一時,醒一次。近曉4∶40 再醒。適夢陳寅恪誦釋其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枝雁’,莫解其意。”陳吳二先生作詩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備載二先生集,不引,只轉介未曾發表的吳先生一首詩之數句。上引1952年12月30日《日記》“夢與陳寅恪兄聯句,醒而遺忘”后,緊接“乃作一詩懷寅恪云”。其詩前四句為:“兩載絕音響,翻愁信息來。高名群鬼瞰,勁節萬枝摧。”第二句云“翻愁”,當指當時“思想改造”運動,可為前述對“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證。后二句自指肖小之徒對陳先生的攻訐。末二句為“昆池嗚咽水,只敬觀堂才”。自是言陳先生獨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靜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吳先生以陳先生比王先生,而獨佩之。吳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陳先生為榮,吳先生1959年7月29日《寄答陳寅恪兄》詩“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證,吳先生結識陳先生后之行事可證。
本節文字寫來較長,竊以為陳吳二先生之素志未必為人所盡曉,而二先生畢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篤,實是古道不泯,乃竟為妄人所歪曲和偽造。辯之,不只為止妄人之口,且為明正道、正人心也。
吳先生一生為保衛中華優良文化,獻身學術,樂道,明道,衛道,遠離政治,與現實政治無涉。先生早年有“二馬之喻”,即一面欲圖事功,一面欲“寄情于文章藝術,以自娛悅,而有專門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先生曾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為“譬如二馬并馳,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面摯之,又以二手緊握二馬之韁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韁不緊,二馬分道而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1927年6月14日《雨僧日記》,據《吳宓與陳寅恪》引)先生所謂事功,不是入世謀政治上的事業,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組織人謀學術文化的發展,那就是先生與志同道合者創辦《學衡》,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獨力主辦《大公報·文學副刊》,籌辦并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等等。這一方面的事業,和先生畢生研究學問,培育青年相并進。先生是以學人而兼為中國學術文化的組織者、倡導者與保衛者。先生畢生樂此,對現實政治不只遠離,而且厭惡已極。“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時,先生甘冒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大不韙,而反對批孔,即是反對政治干預學術。與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談學術。在張紫葛筆下,吳先生變了一個人,不但熱衷政治,分析形勢,趨時媚世,樂在其中;對于他在解放初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極感自得。還樂于“見大人”,如書中所謂的求見鄧小平(盡管不是為自己)。甚且杜撰給毛澤東、鄧小平算命這樣厚誣先生的不經之事。甚至于說,1956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聯想到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一定會緊起來,這在一個純然不懂政治的吳先生身上,絕無可能。
吳先生為人光明磊落,方正純樸,心口如一,從不作謊語,不知如何應付人事,或可說是迂,或可說是書生意氣。因此,一生做過不少在旁人看來是傻事,在先生看來,則是道之所在、義不容辭的事。可是,在張紫葛筆下,吳先生是個工于心計的人,庸俗的人。這又是厚誣吳先生。
甚而在戀愛上,吳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觀。熱戀毛彥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經卷入,光明正大,從不隱晦。張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個朱小姐千里尋先生,而先生呢,張書把先生寫成一個庸俗的人,一個鬼鬼祟祟的人,與朱氏兄妹分別,先生對張“輕輕嘆了一聲,念了一句仿《西廂記》崔鶯鶯的道白:‘嘆人生,煩惱填胸臆!量這般大小的車兒怎生載得起!’又轉頭對我說:‘此詞難諧我意。你別誤會,我并沒和朱某戀愛。過去不曾,現在更沒有。’”(頁275)先生不管是否戀愛朱小姐,都不會這么說。當年戀愛毛彥文,先生公開發表詩,有句云:“吳宓苦愛□□□,三州人士共驚聞。”何其襟懷坦白。這種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張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書寫吳先生日常說話的語言,簡直是不堪卒讀。無論何時何地,書中的吳先生,一開口便是腐朽惡劣的文言,沒有半點活氣。吳先生無論講課,還是日常交談,從來是現代語言,沒有書里這種怪腔濫詞。張紫葛自稱與吳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對于吳先生的語言竟全無所知,也就夠奇怪了。
讀過全書,寫成此文,期待張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年6月8日至10日深夜
唐振常 2011-04-11 20:21:15
 |
相關閱讀 |
 |
推薦文章 |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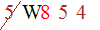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