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思享】同一個諾獎,不同的命運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作者:陳為人,山西省作協前副主席 帕斯捷爾納克獲獎后 早在二戰后的1946年,英國幾位作家就建議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此后,每年都把帕斯捷爾納克作為候選人,年復一年討論達五次之多,但一直未最后決定。盡管諾獎評委會對評選嚴格保密,“不到火候不揭鍋”,但仍有風言風語傳出。國外有文友求證于帕斯捷爾納克,他回答說:“我們這里也有這樣的傳聞,我知道的比大家都要晚……與其說我期望,還不如說我担心這一流言會成為事實。”帕斯捷爾納克還說:“比利時、法國和西德的報刊上都曾談及此事。人們看到、讀到那些消息,也就談論開來,后來人們從‘BBC’電臺聽說,似乎本來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慮到當時的世情,便請求提名機構同意讓肖洛霍夫替換我作候選人。委員會否決了該項請求后,提名海明威為候選人,也許獎金會授給他……” 向來公允的諾貝爾獎評委會畢竟也是“地球人”,也受到當年兩個超級大國“冷戰”思維的制約和牽累,作為非藝術的考量和政治上的權衡,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傳言成真”,授予了美國作家海明威。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一書在蘇聯境外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瑞典皇家科學院重新考慮把諾貝爾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當時蘇聯駐瑞典大使館發言人話中有話地說:“帕斯捷爾納克作為翻譯家比作家更知名。”蘇聯文化部長則明確表示,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肖洛霍夫更為合適。 幾經戲劇性的山重水復柳暗花明,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還是授予了帕斯捷爾納克。 對于帕斯捷爾納克的獲獎,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訊社、新聞報刊,蜂涌而起予以熱捧,進行了大量政治性宣傳,把《日瓦戈醫生》一書的問世,稱作是“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日瓦戈醫生》是一本“關于人類靈魂的純潔和尊貴的小說”,但冷戰時期這種具有濃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思維模式,硬是把帕斯捷爾納克強行推上了政治舞臺。帕斯捷爾納克為自己的作品辯解說:“從七百多頁書中僅僅引用那么三頁”,就武斷地認為是“揭露出專制王國鐵幕的‘杰作’”,這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的熱捧實際上是給帕斯捷爾納克幫了倒忙,使蘇聯當局大為惱火。1958年10月25日的蘇聯《真理報》上,發表了著名評論家薩拉夫斯基的文章:《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10月25日的蘇聯《文學報》上,也發表了《國際反動派的一次挑釁性出擊》一文,光從題目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火藥味。 1958年10月27日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鑒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對蘇聯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和平與進步的背叛行為”,決定開除他的會籍。 1958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權聲明,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到瑞典領獎后不再回國,蘇聯政府決不追究,實際上是發出了“驅逐令”的威脅。迫于這種形勢,帕斯捷爾納克于l2月29日宣布拒絕同一個諾獎,不同的命運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并致電瑞典科學院:“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因我自愿拒絕而不快。” 帕斯捷爾納克在《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寫道:“我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在俄羅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開的,離開它到別的地方去對我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檢討:“《新世界》雜志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聯制度的基礎。現在我很后悔,當時竟沒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都歷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正宗知識分子遭到毀滅。”帕斯捷爾納克請求赫魯曉夫,不要對他采取極端的措施,不要把他驅逐出境。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反而使帕斯捷爾納克因福獲禍,在隨后的日子里,是一個接踵一個的災難。他此時寫的《諾貝爾獎》一詩,頗能反映他的心境:“我算完了,就象被圍獵的野獸……我可倒底做了些什么壞事,我是殺人犯,還是無賴、潑皮?我僅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為我美好的家鄉俄羅斯哭泣。” 1959年3月14日,帕斯捷爾納克在散步時,被從住地別列捷爾金諾傳喚到莫斯科接受審問,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威脅道,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再不停止與外國人交往,將追究其刑事責任。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不久,就在痛苦和壓抑中死去。 肖洛霍夫獲獎后 與帕斯捷爾納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肖洛霍夫的獲獎。 1965年,肖洛霍夫終于如蘇維埃政權所愿,獲得了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僅僅事隔七年后的這次獲獎,卻在蘇聯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宣傳和熱捧。報紙刊物上幾乎一個口徑地說:“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七年前因把諾貝爾獎授給帕斯捷爾納克時對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攻擊,改口說:“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靈已經照亮了諾貝爾文學獎而獲得了世界的公認。……瑞典文學院終于以公正的態度對待一位偉大的蘇聯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學院的這一崇高決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 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出版后,曾遭遇過與他的同伴帕斯捷爾納克相似的命運。馬上遭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批判。當年許多著名的作家、評論家抨擊小說歪曲了國內戰爭,偏離了蘇聯的革命文藝路線,是“為白衛軍說話”。只是由于得到了高爾基的鼎力支持,小說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時,蘇聯評論界再次產生激烈的爭論,有許多“上綱上線”的批判意見,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說有“非蘇維埃傾向”,“肖洛霍夫犯了嚴重的錯誤”。 面對當年所有蘇維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現出了“過人的聰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筆下的作品,既有屬于主流文學的頌揚傾向,又有反映邊緣文學的批判特征,處于主流文學和邊緣文學的模糊地帶。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邊球”“見了紅燈繞著走”的生存策略和寫作策略。他極善于對領袖察言觀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領導人對他的青睞,成為“三朝紅”;他極善于對現狀審時度勢,在一個接一個針對文化領域的運動中,能有驚無險地“安全著陸”;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么時候該冒尖,什么時候該縮頭;他很懂以退為進以守為攻,什么時候該激昂發言,什么時候應沉默不語,什么時候說話可表現作家的個性棱角,什么時候說話必須罔顧左右而言他;他深諳“石油換大米”的交換原則,以某種妥協得到出版的機會,以局部的犧牲獲取關鍵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驚人的聰明才智贏得了人生的大成功。肖洛霍夫是蘇俄文學史上唯一一個既獲列寧文學獎、斯大林文學獎,又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既能為對蘇聯持批判觀點的西方知識界所稱許,又能被本國統治階層所接納,什么好事都讓他趕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謂左右逢源。 蘇俄文史學家提出有“兩個肖洛霍夫”的觀點。一個是作品中所顯現的肖洛霍夫;一個是蘇聯文壇上所表現的肖洛霍夫。一個是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事業搖旗吶喊,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肖洛霍夫;一個是進入自己文學世界,作為民眾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尋道者的肖洛霍夫。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這樣高度贊揚肖洛霍夫:“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心靈深處對人性的崇高敬意。”然而,肖洛霍夫并未“文如其人”,與作品中展現的形象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蘇聯文壇的口碑很不好,留下了許多劣跡: 肖洛霍夫嘲諷地稱帕斯捷爾納克是“寄居蟹”,不言而喻就是誹謗帕斯捷爾納克是寄居在蘇維埃紅色政權內的異端分子。肖洛霍夫還攻擊蘇維埃另一個諾獎得主索爾仁尼琴:“這是個瘋子,不是作家,是個反蘇的誹謗者。”當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國外發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蘇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上,公然指責索爾仁尼琴是“吃著蘇聯面包,為西方資產階級主子服務,并且通過秘密的途徑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爾仁尼琴是“蘇聯作家們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當政者要對兩位作家達尼哀爾和辛雅夫斯基(筆名阿爾夏克、杰爾茨)進行公開審判,理由是他們用筆名在國外發表了作品。這次公開審判激怒了許多作家,62位作家聯名發表抗議信。許多人要求旁聽,不能旁聽的就坐在法院門口抗議。而時任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肖洛霍夫在蘇共二十三大上卻說:“這兩個黑心的壞小子要是落到難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時并不按刑法典嚴格劃分的條款判決,而是遵從‘革命的法治意識’判決,哎呀,這兩個變身有術的妖怪恐怕不會判得這么輕。”并且直言不諱地干脆要求“槍斃這兩個敗類”。肖洛霍夫扮演了一個為虎作倀的角色。 對肖洛霍夫如此公開的賣身投靠,以至84歲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兒,詩人利季婭憤然寫信給肖洛霍夫說:“您和我們大家都同樣清楚地知道,俄國詩人始終是站在被壓迫的人民一邊的。您的發言把您置身于俄國傳統之外。可惜我們不能懲罚您;不過您已經受到足夠的懲罚了,罚您多年來創作力枯竭。” 國外的媒體甚至向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提出:對于這種違背諾貝爾設獎本意,迎合專制獨裁政權的主流話語,喪失一個作家人格的獲獎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諾貝爾獎金。 但是,從斯大林時代血雨腥風中的過來人,對肖洛霍夫給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杜勃羅留波夫曾為俄羅斯作家筆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義為“一群退出戰斗的妥協者”。并有這樣一段精彩論述:他們“否定了跟壓迫著他們的環境做殘酷斗爭的必要”,“走進了一座郁蒼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們攀援上樹原本是想尋找一條新路,但上樹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顧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軌跡,為俄羅斯文學史活生生勾勒出一個“多余人”的形象。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比較是最好的鑒別。從帕斯捷爾納克和肖洛霍夫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不同經歷和命運中,我們感悟到什么是一個作家應該持守的人格立場和道德底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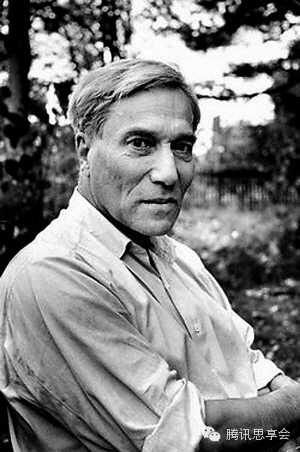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1:00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