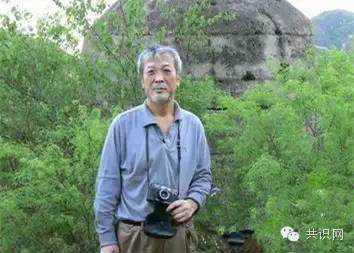|
相關閱讀 |
【人物】馮其利:經歷了多少苦,草根熬成了大學者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共識君按:本周【人物】欄目,共識君給諸位推薦一位“板凳甘坐十年冷”、為學術上的志業風餐露宿、忍疾耐勞終至身死的民間學者——馮其利。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里,馮先生的人生故事與學術精神能為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和感動呢?請看本文。
人物:馮其利,1949年生于北京,當過工人,熱愛歷史,對清史尤有研究。北京史研究會會員,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常務理事。被譽為“中國研究清代王爺墳第一人”。著有《清代王爺墳》、《尋訪京城清王府》等作品。2014年11月24日因腦梗去世,享年65歲。
馮其利先生
馮其利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學者,并沒有耀眼的專業教育背景。1968年初中畢業后,他被分配進北京電冰箱壓縮機廠當了一名工人。那個年代能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不知羨煞多少人,但馮其利卻似乎總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跟馮其利一個車間的崔平很快就發現他“不務正業”。上班時間他只管按一個按鈕,領導讓他松個閥門,他就老老實實回答:沒學過,不會。他確實不會,直到提前退休,他也沒把鉗子、扳手摸熟,惹得廠領導不止一次挖苦他:馮其利啊,你是真不適合在我們廠子工作!
八小時之外,馮其利沉迷于抄抄寫寫,一手硬筆小楷字非常漂亮,后來還經人介紹幫學者鄭公盾抄寫了多年的文稿。他能一筆一畫手繪北京地圖,而且每到周末休息日,就帶上干糧鉆進荒郊野外,沒人知道他在搗鼓什么。
與馮其利志同道合的文史愛好者、北京史地民俗協會的副會長常華回憶,“文革”后期,老百姓的業余生活很貧乏,廠子里的工人下了班沒事干,就聚在一起喝酒、打牌,但馮其利“不好這個”。
原來,在為鄭公盾抄稿的過程中,馮其利漸漸迷上了歷史,尤其是清代史,并花四年時間讀完了500多卷的《清史稿》及其他大量的清史專著。讀書的同時,馮其利還特別注重實地考察,只要聽說哪里有一處古跡,就要趕過去看一看。這種研究方式和習慣一直堅持到他躺倒在病床之前。
就是在野外考察的過程中,馮其利結識了有相同興趣的常華和京城其他文史愛好者。荒郊野嶺里一塊墓碑究竟為何人所有,丈量完尺寸、拓下碑文,接下來就需要查閱史料尋找蛛絲馬跡。當時有關北京的地方志沒有發行新版本,只能去北京圖書館翻民國年間的版本,難度很大。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北京晚報》復刊后開辦了一個《談北京》的小欄目,幾百字的“豆腐塊”文章,吸引了一批史地、民俗的業余愛好者踴躍投稿。一天,已經結婚有了兒子的馮其利對妻子崔平說:“將來我一定要在《北京晚報》上寫上我的名字。”
幾十年過去了,崔平還記得自己當時的反應:“真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你就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怎么能在《北京晚報》上寫上你的名字?”
讓崔平吃驚的是,1981年,丈夫的“豆腐塊”真的登上了《北京晚報》,而且此后“馮其利”這個名字時不常就見諸報端。快80歲的老岳父只要聽說有女婿的文章發表,就樂呵呵地趕到菜市口大街買上5份。廠領導似乎也逐漸意識到強扭的瓜不甜,趁廠子搞“社會教育”將他調進了教育科,主講近代史。
一個來自民間的學者被譽為“中國研究清代王爺墳第一人”,似乎有夸大的嫌疑,但在北京的文史圈里,提及馮其利,沒人會認為他有辱這個稱號。常華說:“清代王爺墳、王爺府,在他之前沒人做過系統的研究,現在也沒人能超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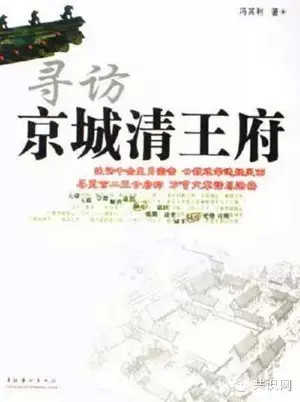
馮其利先生作品
相比其他領域,“清代王爺墳”是個冷門,資料少、野外調研量大、還難出成果。但也正是這個“冷”字,讓追求功利的人遠離,給了馮其利填補空白的機會。
1982年,《北京晚報》上刊登的一條消息引起了馮其利的注意。消息報道遼寧撫順的薩爾滸古戰場開放,其中展出的62件明清石刻都是從北京西郊的隆恩寺運過去的。隆恩寺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明清石刻,癡迷歷史的馮其利決定赴實地一探究竟。
休息日,背著干糧的馮其利先乘公共汽車到達郊外,然后再徒步前往隆恩寺。不料一番周折后,出現在眼前的隆恩寺已經變成北京軍區某部的駐地,禁止老百姓入內。不甘心的馮其利在四周轉悠,忽然發現附近有一座清代王公墳墓的遺址,好奇之下,他詢問了當地幾位老人,但誰也說不清墓主人到底是誰。
回到城里,馮其利沒有查找到任何相關史料,這更激起了他那股追究到底的擰脾氣。雖然不擅社交,幾經猶豫,他來到護國寺敲響了溥杰的家門,以求得到指點。后來馮其利告訴常華,那天開門的恰巧是溥杰本人,聽說了自己的來意后,素昧平生的老人非常感動,將他引進屋內詳談。隆恩寺的王墳究竟為哪位先人所有,溥杰也并不清楚,但他鼓勵馮其利大膽探索,并親手寫了字條為他引見兩位專家。
不料專家也未能解答馮其利的疑問,他們告訴馮其利,清代宗室王公墓葬研究是塊空白,過去一些地圖上標的地名不準確,有的又只標出墳冢沒標名稱,如果他能把這些墓葬一一理清,將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聽了這番話,一直在尋找主攻方向的馮其利大受啟發。又一個休息日,他再次來到隆恩寺,經過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當年看墳人的后代趙成德,老人的回答振奮人心:“墳主的后人姓曾,是個大夫,就住在福綏境胡同。”
馮其利立刻返城馬不停蹄地找到曾大夫,曾大夫取出家譜,真相水落石出,原來隆恩寺的王墳遺址是努爾哈赤的第七子阿巴泰——清初饒余敏親王的家族墓地。
成功的喜悅堅定了馮其利的信念。清朝前后共十二代皇帝,皇子近百位,親王、郡王也有百余名,他們死后大多葬在京郊風景秀麗的山區。但由于年代久遠,絕大多數墓葬都遭到嚴重破壞,有的連墓碑都遺失了。而皇室的后人在歷史的更替中也逐漸散落于民間,有的沒落后把姓氏都改了,捱過十年浩劫的,對自己的身份更是諱莫如深。
這些都成為清王墳研究的重重障礙,但馮其利決心要在這條學術道路上一走到底。
圈里人談起馮其利對研究的投入都用到一個“癡”字,為了研究,風餐露宿、忍饑挨餓他都在所不惜,常年遭高血壓、糖尿病的折磨也依然心無旁騖。
崔平經常聽鄰居招呼她:“哎,快看,你們家馮其利回來了!”在小區里,自己的丈夫絕對屬于一怪。“他穿羽絨服從來不系扣,就這么敞著,再拿根繩一勒,手里提一個大紅尼龍袋子。有一次我姐上家里來,說其利,你那羽絨服是不是該洗一洗了,怎么后面背一幅地圖啊?然后又說,我覺得你整個人都應該擱洗衣機里洗一洗。”
對于丈夫的不講究,崔平無可奈何。每天一早5點馮其利就背著書包出門了,直到晚上六七點鐘才回家。進門包一放,先直奔小陽臺改造的所謂書房,抄個不停,中途花5分鐘吃碗飯,再繼續寫,話都顧不上說一句。
有時崔平睡到半夜醒來,發現陽臺的燈還亮著,忍不住埋怨“不要命啦”,馮其利就頭也不抬地回一句“你不懂”。自己買給他的皮鞋,他也從來不穿,只穿松口布鞋和旅游鞋。整天“鉆墳圈子”,怎么舒服怎么來。十幾年里,因為要伺候相繼癱瘓的雙方老人,崔平實在沒有多余的精力,也就任他去了。
研究清王墳,馮其利一直恪守“實地勘察、采訪親聞者、與史料相互印證”三條原則,絲毫不肯馬虎。為此,他的足跡踏遍了北京郊區,甚至還走訪到天津、河北。借助交通工具抵達的地方畢竟有限,剩下的路,馮其利全靠一雙天生平足的腳和一副吃苦耐勞的精神。
沒用電腦之前,所有實地獲得的數據、采訪口述加之參考資料都靠馮其利一筆一畫手寫,圓珠筆芯一捆一捆地買回家,密密麻麻抄了無數本。
等有了電腦,雖然還是用手寫板,總算可以存儲了,手邊500G容量的硬盤至少二十個,大大小小的U盤則不下百八十個。馮其利多年的好友楊海山幫他估算:“手寫內容絕對不少于上千萬字,我的床底下有半床都是他當年手抄完又復印的資料。”
馮其利去世后,楊海山經常睡不著覺,耳邊總回響起老友多次跟他說過的話:按照我的水平和速度,我需要的東西、我喜歡的東西和我必須整理的東西,沒有兩百年完不成。人生有限,我得抓緊每一天,活一天就得干一天。
在老北京人眼里,“鉆墳圈子”是件不吉利的事,十幾年跋山涉水,馮其利大都是只身上路。他曾因為迷路在荒郊野嶺的破廟露宿,身上帶的干糧吃完了,就擼柏樹種子充饑。第二天下山后,老鄉聽說了他的遭遇都替他后怕:“那山上可有狼啊!我們都不敢在里面過夜。”
危險阻擋不了他的腳步,病痛更是。年輕時馮其利得過一場腎病,身體底子不好,之后又出現了“三高”癥狀。有次楊海山和馮其利一道出門,路過社區醫院,他硬拉著馮其利去測了測血壓。
“當時大夫就驚著了,說您高壓都200多了還出門哪!馮其利笑笑不說話。”
有時腿疼得實在厲害了,他就隨身帶一張小馬扎,公共汽車沒來前坐一會兒,路上走累了也坐一會兒。大夏天里奔波一天進了家門,崔平看他臉上的白癜風都被曬得通紅,拉開冰箱門就找冰棍嚼。“他血壓那么高難受啊!我說看把你累的,你太苦了!他就說我沒時間,我能又活30年知足了!”
1996年11月,凝結了馮其利十幾年研究心血的《清代王爺墳》一書出版了。書中收錄了他勘察的83處王墳,范圍涉及北京、天津薊縣、河北易縣、淶水等地。他走訪了數以百計的村民和健在的舊時看墳戶后代,由清代宗室封爵制度入手,附以碑記、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等各項調查,為這個空白領域填補了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溥杰生前曾向愛新覺羅家族鄭重介紹過馮其利,并囑咐他們要多多善待,“一個漢族人做了我們本該做的事,太不容易了。”
由于常年浸染,馮其利對皇族譜系了然于胸,尤其是愛新覺羅氏。他的通訊錄上記錄了近千名愛新覺羅氏后人的姓名、地址和電話,哪家祖上的根兒是誰,分多少支,沒人能比他更明白。經常有皇族后人慕名而來,向他尋根問祖。圈內人凡是涉及這個領域,也只有向他求教。
年滿60歲后,出于健康方面的考慮,檔案館終止了與馮其利的聘用關系,但馮其利不愿意過普通退休老人的生活,又受聘到首都圖書館檢索摘抄沒有對外開放的老報紙。
對王墳、王府的研究已經暫告一段落,可強烈的緊迫感卻依然如影相隨。此時,北京的老井蓋文化又引起了馮其利的興趣,老朋友常華得知后一聲嘆息:“又是一件苦差事!北京有多少井蓋啊,十米八米就一個,只能靠走。”
超負荷的工作強度終于讓這個渾身是病的老人有些支撐不住了,2013年7月底,常年血鉀低的馮其利破天荒聽醫生的話住院打點滴。因為平時從來不去醫院,崔平趕緊趁這個機會讓丈夫好好做個全面檢查。
腦科和心內科的會診結果出來,大夫告訴崔平馮其利的大腦上有一塊腔栓,腦干上也有一塊,腦子通往中樞神經上還有一根血管閉塞。8月12日,還在住院中的馮其利早上起來突然不會說話了,也無法坐立,醫生預言的“爆胎”癱瘓就這樣發生了。
崔平忘不了丈夫瞪著眼睛看她想說說不出來的樣子,“我趕緊把家里兒子的小黑板拿來讓他寫,他還寫‘我想上圖書館’!”
“去首圖”成了馮其利心頭咽不下的鯁。出院后,又能說一些話的他總纏著崔平帶他去圖書館。
“他告訴我還有很多事沒做完,就是每天這么拍照可能還要照五年時間。我就說他,生命不是自己的?他又說你不懂。我確實不懂、不理解,你都這樣了,還上圖書館?那天我出門辦點事,到家看見他妹妹站那兒直哭。我問干嗎呀?她說我大哥說什么都不吃飯,你前腳走,后腳就拉著我要上圖書館,我哪兒弄得了他,怎么去啊?”
姑嫂兩人相對流淚。
從前總是風塵仆仆的丈夫一天比一天沉默了,也一天比一天更加衰退。
崔平嘴上數落著他:“后悔了吧?站不起來了,沒人領著你,一步都走不了了,你就不折騰了!”內心卻翻江倒海:“他這輩子太苦了,不講吃,不講穿,沒看過電視劇,沒出去玩過,我們倆連一張合影都沒有。
他病了以后,我給他洗身子,摸著尾骨那兒出來這么大一塊骨頭,那是腰椎間盤突出露出來的!怪不得他每天走著上班,坐壞了六個小馬扎,褲子也老是磨破,他從來不說!”

2014年11月26日清晨,在同仁醫院的太平間,65歲的馮其利向親友們做了最后的告別。他面容平靜,化妝以后臉上的白癜風不見了,也少了幾分蒼老。苦行僧般的人生已經終結,舍與不舍,都是該好好休息的時候了。
(本文原載微信公號“北青天天副刊”,歡迎關注!)
共識網 2015-08-23 08:47:26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