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人物】史家楊奎松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機緣巧合,我和著名學者、華東師大教授楊奎松兄認識很早。說起來,我經常有這樣的機緣,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接觸到比我年長的學者——盡管那時他們還沒有爆得大名。 20年前,我剛過而立之年認識楊奎松的時候,我就覺得他的學問非常深。 那時,社會上是個全民經商的浮華年代,學問不被人推崇,對于歷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這樣關注。楊奎松雖然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認識奎松以后才知道他學問很深的。我把他的學術文章,或者改一個通俗性的標題;或者改個開頭結尾(是敦促他改),在《炎黃春秋》發表。印象中,我把他寫的關于“延安整風”的文章分三期連載,曾經大得好評。現今說起來,對于延安整風那段歷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個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創辦一份雜志——又是機緣巧合,關系更進了一步。此后,我和他相繼離開這份雜志。再此后,他成了著名學者,我還是一個編輯。偶爾在會上見面,還是非常親切。 當“清道夫” 讀楊奎松的書,常常讓我想起“清道夫”這個詞。 這個詞是從南美洲的一種魚的名稱而來。被命名為“清道夫”的這種雜食性魚類,因以各種水底垃圾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從足球場上的職責來說,還是從那條整天在海底游來游去的魚兒來說,用以比喻楊奎松的學問,都很貼切。 在中共黨史學界,做學問的人很多,號稱學問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楊奎松這樣的人卻很少。他的學問涉獵面廣——像雜食的魚兒,舉凡國共關系、中共與共產國際、與美國的關系、中共領袖如毛澤東本事的研究,都有著作問世;他的學問又作得非常扎實——像足球場上拖后的中后衛,如同吸食垃圾的魚兒,對于中共黨史學界研究中出現的史料上的模糊,學風上的浮漂等,都給以清除。 所以,在這個領域里,很多人怕楊奎松。因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來,大多數人如果不想顏面盡失的話,只好緘口不言。楊奎松批評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就是一例。無論寫書還是講話都洋洋灑灑的金教授,對此則毫無回應——關于這一點,下面再說。 以楊奎松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來說,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 西安事變發生七十多年了,鑒于這場事變對中共命運的轉折性意義,研究的著作可以說汗牛充棟;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大主角張學良,鑒于他在事變后被囚禁的命運,以及他在海外的影響力,海內外對他進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說與他10個“等身”還富裕。楊奎松敢在自己的著作用“新探”兩個字,確實需要一番勇氣,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有浪得虛名之嫌。 “新探”新在何處?從開篇序言中讀者即可領略到。 要探討“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繞不過去的問題是,張學良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這是一個海內外學者都關注的問題,因為這直接涉及到張學良為什么會把自己的領袖蔣介石囚禁起來而幫助中共,張學良到底與中共的關系如何;也是學界好像有定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問題。 關于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于參與這段歷史、同時與張學良有過交往的兩位人士呂正操和宋黎。呂正操當年是張手下的東北軍將領,2001年他在參加張學良葬禮時對閻明復(當年東北軍將領閻寶航之子)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宋黎當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據他回憶,他是從在西安事變前后曾代表中共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那里得到肯定答案的。呂、宋兩人說法,在黨史學界至今盛行。 但在楊奎松看來,這種說法卻不靠譜。他認為,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年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持上述說法,更不要說以此來探討張與中共雙方關系的改變了。 在本書中,像這樣扎實的考證比比皆是,很多結論顛覆了既往學界流行的觀點。 臺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在序言中說:“此一新著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而有新的發現,同時對于西安事變若干史實作了新的探索。書名定為《西安事變新探》可謂名副其實。” 這不是一般的客套,應是蔣先生的由衷之言。 打“筆墨官司” 說楊奎松打“筆墨官司”,就是上文提到最近一次與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路頌揚、一路飆升之際,楊奎松的一篇《“輝煌”莫建沙灘上——對<苦難輝煌>一書的正誤與批評》的書評,讓學術圈外的有些讀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驚訝:原來這本書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錯‘抄’”、“不可接受的誤‘讀’”、“不可理喻的編造”、“不可容忍的剽竊”四大軟肋。 當然,也有的讀者對楊奎松的批評很憤慨,認為他“尖刻”,是“學霸”。一場“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收場。 不過,楊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后出版的的《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札記》一書中,特意收錄了這篇書評,可見他對“尖刻”、“學霸”等指責并不在意。 這本《讀史求實》,是楊奎松多年來學術論文的匯集。副標題說是“讀史札記”,多半有些謙虛。譬如,論述戰后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中共也曾試過“和平土改”》,考察共產國際對中共財政支援問題的《政治獨立的前提》,從俄國歷史視角解讀“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命運的《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等等,一是涉及到的問題都是中國現代史上眾說紛紜的大問題,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兩萬字以上的篇幅,稱為“札記”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實? 而就所論證的問題來說,楊奎松在這個領域苦心孤詣30年,厚積薄發,視野極為開闊,一個個極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細節,在作者開闊的視野中,一旦拎起來成為論述一個大問題的索引,而這些大問題,都是關乎中國現代史不同時期的節點。這怎么能是“札記”所涵蓋的? 即以批評金一南的書評來說,楊奎松所指出該書的四大軟肋,既不是“札”,也不是“記”,而是實實在在從學理上闡發的。 因為批評了“各方忽然齊刷刷力推起《苦難輝煌》一書來”,楊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謂的“尖刻”、“學霸”的責難。其實,熟知楊奎松的人都知道,就為人來說,他非常低調,既不“尖刻”又不“霸”。 前面我說過,1996年,我和楊奎松曾一起辦雜志。那是已故的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學者鄭惠先生創辦的。鄭惠特意邀請楊奎松來當主編,可是他卻認為自己學識不夠,又推薦了另一個“楊”——楊天石——來當主編,自己則屈居副主編。這樣的人,怎么能和“霸”連在一起? 不過,就學術研究來說,楊奎松倒是少有的較真,他身上多少帶有一點二三十年代學者那種書齋求學的特點。記得不止一次聽他說過:“研究中國現當代史,如果不去意識形態化,那是做不出好學問的。”他從在這個領域篳路藍縷到現今的著名學者,始終恪守這一點。 早在1980年代后期,楊奎松就與將歷史作為報告文學來寫的作家黎汝清,有過一場“筆墨官司”,就皖南事變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尖銳的批評了已經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后期我和他一起辦雜志時,他針對葉永烈等人紀實文學書寫歷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詞,力主在雜志上發起“紀實文學與歷史”的討論。這場討論中,楊奎松不但組織座談會,組織稿子,還親自寫文章闡發觀點。 與有人愛與名人打“筆墨官司”不同的是,楊奎松純粹是學理上的較真。他在書中闡述為何批評金一南時說:“如果沒有人出頭對這本書提出尖銳的批評,以這本書被熱炒和受推崇的情況,一定會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類似不顧歷史真實的所謂歷史作品跟風而已起。這注定會使人們對歷史的認知變得更加混亂不堪,使真正的史學研究成果陷入及其尷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為一些主觀先行、生吞活剝的文學作品的墊腳石。” 從這個出發點來說,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期待:楊奎松有更多的“筆墨官司”纏身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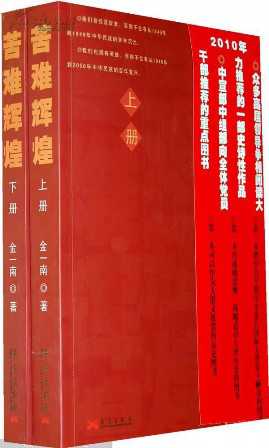

觀察中國 2015-08-23 08:49:27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