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周末人物】說儒小記——辜鴻銘、馮友蘭與錢穆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儒學取代宗教,造就了一種真正的中國人,那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它也決定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最美妙的特質。 說儒小記——辜鴻銘、馮友蘭與錢穆 作者 | 李冬君 晚清社會,有一位來自西方,卻以儒教安身的人,他是辜鴻銘。他腦后留著一根辮子,形似阿Q的Q字。國人目之為“怪”,譽之者,稱道為“怪杰”;貶詆者,抑其為“怪物”。他的形象,除了腦后那根辮子,很有點像八大畫的鳥,高視闊步,白眼朝天。如果將魯迅筆下的“鳥頭先生”的綽號,從顧頡剛身上移植到他的頭上,或許會更加惟妙再加惟肖。 學者把他當作笑料,茶余飯后,隨便談談,就把他解構了。他的思想,對不起沒興趣,那是西方學人的話題,誰叫他不用中文寫作?可他的瑣事,就像花生米,總是被人放在嘴里咀嚼。 什么茶壺啊茶杯啊小腳啊,還有皇帝,中國人哪能沒有皇帝?皇帝皇帝,天經地義,沒有皇帝,那還算什么中國人!他嘻嘻哈哈,東拉西扯,一下就抓住了中國文化的質:皇帝。他感到奇怪的是,大家都在罵皇帝,可又都自命為中國人,這樣的中國人,是不是有毛病? 他堅信自己是真正的中國人,因此,他要贊美皇帝,忍不住就要彎下雙膝,五體投地,可惜他那時中國已沒有了皇帝。若還有皇帝,他會怎樣呢?有人說,也許他的膝蓋比誰都硬、都直。因為,在他看來,這就是仁義。中國文化,一要有皇帝,二要有仁義,而他就是標志。 俄國的托爾斯泰曾與他通信,英國的毛姆專程來拜訪過他,印度的泰戈爾同他交流思想,甘地稱他是一個“可敬的中國人”,在德國和日本,他更是風靡一時,還有“辜鴻銘研究會”問世。那時,有幾人能享此殊榮?說絕無僅有,可能有些過分,說鳳毛麟角,或許可以這么比喻一下。 蔡元培辦大學兼容并包,把他請到北大,請他邊教英語邊講中國文化。可當時國內,能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的著作多用英文寫成,他的英語寫作能力,連林語堂也嘆服,譽為“中國第一”。不僅在中國,即使在母語國,他的英語寫作,也讓老外大跌眼鏡。 1914年6月,他在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上發表一篇論文,中文名為《春秋大義》,英文名為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直譯作《中國人的精神》。這是他在北京東方學會上宣講的論文。1915年,該文和“中國婦女”等文章一起編成論文集,由“北京每日新聞社”首版,書一出就滿堂彩。 時至今日讀之,它仍使人新鮮,他說自己是用心寫的,不是用大腦寫的,心想是直覺的,腦思維是邏輯的,他自命為中國人,而往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圈子里鉆,有意將他的西方學養擱到一邊。 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儒學取代宗教,造就了一種真正的中國人,那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它也決定了中國歷史的一個最美妙的特質:即歷史悠久,而又永葆青春。儒學能取代宗教,證明它具有宗教功能,辜氏認為,儒教對于全能皇權的絕對信仰和忠誠,給予中國人安全感和永恒感,它構成中國文明的真正基礎。所謂“春秋大義”,無非“忠君”而已。 東西方文明的基礎是如此的不同,西方文明以對上帝的信仰為基礎,中國文明則以忠君為基礎。正如信仰上帝需要教堂,忠君也需要教堂。儒教不專設教堂,儒教的教堂,是學校,是家庭;儒教的培養目標是君子;儒教的教育方針,即君子之道,只包含了兩項內容:忠于君主和孝順父母。 辜氏聲稱,要用君子之道,復興中國文化。他從世界主義出發,反對中國西化;他批判西方文明,與托爾斯泰等人有著共同話語。不過他認為,托氏對西方文明所持的觀點過于消極,頗似老子,而他則像孔子,要給世界文明找到一個真實的基礎,為現代社會規劃出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 以此,他在西方獲得了“哲人”桂冠,在中國反而不合時宜,專門與新文化運動唱對臺戲,于是乎唇槍舌劍,口誅筆伐,結果便是辜氏的思想被貼上倒行逆施的標簽,封存入庫。 讀中外文化史,我們發現,一種文化衰落時,常有兩類人物出現,一是喜劇性的,如堂吉訶德;一是悲劇性的,如賈寶玉。晚清社會也有這樣兩類人物,他們的代表人物:悲劇性的是王國維,文化與他生命交融,文化衰落,他便以身殉之;喜劇性的,便是辜鴻銘,他眼見著安身立命的文化衰落了,便以“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氣魄,起而扭轉乾坤,他不僅向世人闡述這種文化的特質,宣講他的價值,而且他還要用已經沒落了的思想,來拯救他認為早已衰落了的世界,并為世界文明提供新的思想基礎。 歷史的選擇是殘酷的,然而人類的良知卻充滿了溫情。當堂吉訶德手持長矛沖向風車的時侯,我們微笑之余,便肅然起敬,他的瘋狂之舉,讓我們感受到了人類精神的崇高。當這位老人拖著辮子,走上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的講壇時,引起學生一陣哄笑,他便猛喝一聲:摸摸你們的腦后,看看有沒有辮子!今天我們批評這位老人,要記住這一聲猛喝,先摸摸自己的后腦。 富于哲理性的民族,不一定善于構造哲學體系。 如果我們將中哲史和西哲史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中哲史上的兩個特點:一是哲學體系的貧乏,二是哲學的大眾化傾向。此兩點一以貫之,直至今日,并無大變。 現代中國,寫哲學、談哲學的人很多,能構造體系的人,卻少得可憐,而已經具備體系的哲學家,就更為罕見了。馮友蘭先生,就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構造了體系的哲學家。 馮先生將其一生的哲學活動,分為四個時期。從1919-1926 年,為《人生哲學》時期;從1926-1935 年,為《中國哲學史》時期;從1936-1948 年,為《貞元六書》時期;從1949-1981年,是尚未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時期,前三個時期,碩果累累。 《人生哲學》作為中學教材,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國哲學史》獲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好評,并被譯成多種文字;《貞元六書》構造了一個哲學體系,確立了他的哲學家地位。第四期是他哲學體系的改造和學術生涯的懺悔期,時始于1949年。 中國革命勝利了,革命的真理似乎昭然。面對真理進行懺悔,不僅是形勢的需要,還是哲人良知的需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可以不畏強權,可以蔑視富貴,卻不能不服從真理。 “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求道的“座右銘”。然而,為真理而舍生忘死,固然表現了人類的理性的崇高,但它同時含有某種固執、偏見和迷信以及放棄自我的悲哀。對真理的追求,是人類所獨有的理性情結;然而對真理的崇拜,卻往往會扼殺對真理的追求。 1949年10月,馮先生寫信向毛澤東表態,是他懺悔生涯的開始。 信中表示,他要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并在5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這種熱情的態度,無疑是真誠的。向真理投降,接受真理的制裁,他心悅誠服。但是,這種真誠,與其說是個人的自覺,不如說是受了歷史使命的感召。 可他把思想改造看得太簡單了,毛主席回信了,回信語重心長,告誡他:“總以采取老實的態度為宜。”起初,他以為毛主席言重了,經過30多年的鍛煉,他終于理解了這句話的份量。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0年來,天翻地覆,他終于悟出的“真意”,就是“不老實”三個字。這是一個習慣于自我批判的人. 所能采取的唯一態度一一“無我”的自虐。 在30多年的懺悔生涯中,他不停地拷問自己的靈魂,訴諸文墨。 1957年l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文章提出,對于中國的哲學遺產,可以“抽象繼承”。這一觀點,很快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尤其以陳伯達的批判最具權威性。平心而論,“抽象繼承”法,的確留著他原來體系的尾巴,在“抽象繼承”的名義下,他原有的思想體系多少可以保留一些本來的面目,而不必作脫胎換骨般的自我革命的手術。 可陳伯達不放過他,且當頭棒喝,逼他與自己的思想體系決裂,不決裂,就是不老實。他當然不服,事過20多年,他在《三松堂自序》中,仍然說他的“抽象繼承”,與毛主席的“批判繼承”,可以并行。其實,“抽象繼承”,重在繼承,“批判繼承”,重在批判,兩者的差別,一目了然。他那么執著地用毛主席的觀點為自己辯解,說明他在認同權威的同時,多少還想恢復一點自我。 文革初期,他挨批斗、被抄家、住牛棚。文革后期,他在窮途末路、瀕于絕望時,得到毛主席的關懷,從此峰回路轉。感激之余,他賦詩一首,轉達毛主席。詩云:“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賴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這首詩,是他徹底放棄自我的一個宣言。 在隨之而來的“批孔”運動中,他便開始自覺地走“群眾路線”了。他說:“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哲學家放低了身段,在這種思想的姿態下,他寫了兩篇反孔文章,先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后由《光明日報》轉載,轉載時加了編者按,在當時是最具權威的傳播,叫“大肆宣傳”,馮友蘭因之而名噪一時,居然在群眾運動中咸魚翻身、枯楊生花了。 從尊孔到批孔,這彎子是怎么轉過來的?僅僅是環境壓迫所致,還是有更為深刻的思想原因。其實,尊孔與反孔,正如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都可以從他的思想體系中找到答案。 上世紀50年代,他主張對孔子還是“抽象繼承”,那是他想調和儒學與新的官學,試圖在新的意識形態中為孔子爭一席之地,當然,結果必然是以他被批判而告終。1970年代,當批孔成為現實政治,逼著他在孔子與國家之間作出選擇時,他無論從現實需要出發,還是從儒學傳統出發,都只能選擇國家,這是儒學的最高目的。 國家高于孔子,也高于自我。而說到底,在他的體系中,孔子是自我的對象化,這正是中國傳統儒生的集體潛意識。批孔,實質上是自我批判的一種哲學化形式。他的哲學,重共相輕殊相,重抽象輕具體,重大全輕個體,歷史觀難以超越大一統的拘囿,價值觀為國家至上,他的“天地境界”的實現,是以無我為前提的。他的自我,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本己“損之又損”,以這樣一個“損之又損”的自我來面對復雜的現實政治,當然不堪一擊,魂飛魄散。 他徹底放棄自我,結果反而鑄成大錯,“四人幫”利用他制造輿論,欺騙群眾。對此,他自責頗深,常說自己有嘩眾取寵之心,哲人其萎矣。他給我們留下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即使在真理面前也不能放棄自我,哲人放棄了自我,哲學就會異化,真理也會異化。 在臺北東吳大學里有一處宅院,朱門上綴著小黑牌,金書“素書樓”,是故居主人錢穆手書。 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就在這個“素”字上了。據說,宅第落成之際,夫子思念先慈,遙憶當年太湖之濱“素書堂”弦歌盛景,那可是無錫七房橋一帶的文華淵藪,是母親把他教養成讀書種子。如今老大鬢衰,浪子歸心無所托,便托名于此為“素書樓”,“素”是儒術的底色。 中國文化愛吃“素”,孔子作為“素王”,安之若“素”二千余年,而王朝在家天下里走馬燈、跑龍套,最多不過兩三百年,所以,帝王要向“素王”看齊。“素王”非虛,為王立道,為國制禮,雖非王權之王,卻是王道之王,是關于王的理念之王,是關于王權的標準之王。 孔子本人也很喜歡“素”,他說“繪事后素”,絢爛的繪畫,要在一款素帛上展開,喻意如云在青天,月印萬川,與老子所言“見素抱樸”,一起打造中國人精神結構的底子。圣人是人民的老師,教化百姓,就是在素帛上繪出圣人之道。古漢字里,“繪”字與“紋”字通用,紋又與“文”字通用。 有一本《素書》,由黃石公傳授張良,張良到死也沒找到可傳之人,便帶到棺材里當枕了。西晉時,被盜墓的挖出來,才見了天光。一千多字,講的還是“道、德、仁、義、禮”。如果就這么點人云亦云的東西,還不至于神乎其神地找不到傳人吧?也許“素”的奧妙不在字面,而在字里行間。 《素書》要從無字處讀,就像讀中國畫,不僅要讀線條和色彩,還要于空白處讀留白。明乎此,霍去病才向漢武帝說“何必學兵法”,因為他已見兵法之“素”,對馬上的匈奴人用漢家兵法沒用,就不必再求“繪事”多此一舉了;漢宣帝說得明白,他說“漢家自有法度”是“霸王道雜之”,王道是寫在字面上的,如《素書》所言“道、德、仁、義、禮”,這是“繪事”;霸道在無字處巡,要從“道、德、仁、義、禮”背后看,這就是“素”了,是《素書》的微言大義。 其實,《素書》并非沒有傳人,張良傳給劉邦,潛移默化,劉邦深得其意,張良才說“沛公殆天授也”。鴻門宴上,兩人的唱和,可謂天作之合。《素書》之本在“素”,“書”與張良陪葬,而那“素”字,早在鴻門宴上就被劉邦帶走了,從此,張良再無傳人。 近代康有為,自號“長素”,意思是比孔子還高。可他的抱負,略一施展,便連累了光緒。敢以“長素”自命,還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本書,想在“素王”那“一張白紙上”變法,畫出他心中“最新最美的圖畫”,但失敗了,可見他還不知“素”的底蘊。但他已開了新儒學的先河,儒家內圣外王的分寸,真的不好把握。 1966年,錢穆先生攜夫人從香港到臺北,蔣公禮賢下士,安頓了他的“素王”懷抱,蔣經國還親自促成了“素書樓”從圖紙到施工。而錢穆則在復興儒學的懷抱中,居然也就受之無愧,安之若“素”了。 素書樓的宅院里,梅花遍植,那是一個儒者的寄托,在梅的朵瓣上,他看到了儒者的君子風骨,還看到了儒學復興的希望,在現代儒學即將衰落之際,他卻看到如梅花重新綻放的儒學命運之光。他把儒學比喻為“雪后老梅”,雖不免有凋落之時,但凋落之后,必有繁花似錦、開滿枝頭一日。于是他自命為“拾起地下墜花,來揣測枝頭新葩”的園丁,“發愿將中國二千年來儒家思想之內蘊”開顯出來。 他要堅守這份道統園丁的職業,在春天來臨之際,披德風,化道雨,潤民生。看得出,素書樓里寄托了錢穆先生的抱負以及晚年的鄉愁,這里是他們身心的領地。素書樓的園林栽植也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格物精神。大門內,正對的是坡體立面,臺階式錯層,被綠植線分割為“之”字形的浪漫,在減緩坡度的體貼中,“格物”著梅楓竹松的不同,想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應該比“之”曲折得多,格物走“之”字形,不過是剛剛起步,這才是素書樓的魂。 錢穆先生說過的一段話,與素書樓是恰接的。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專制,而是中國式民主制。西方民主政府像一家商鋪,中國式民主政府則更像一所學校;西方民主制下國家首腦像商鋪經理,必須聽命于股東,受制于民眾,而中國式的民主制,卻使其政府官員如教師一般,教誨護導民眾。所以,主權在民和三權分立,就在中國傳統政治和儒家思想中,只是表現形式同西方不一樣。 要對歷史懷有溫情與敬意,這是先生勸導青年的名言,他說不要去追求什么平等、自由、獨立、權利,而是應該“入則孝出則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子,青年之楷模;論語,青年之寶典”。復興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其實,這種溫情與敬意,還是停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樊籬中,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應該是文化江山里的事兒,與王朝無關。 本文選自經濟觀察報,轉載請注明來源。儒教辮子

▲“狂士怪杰”辜鴻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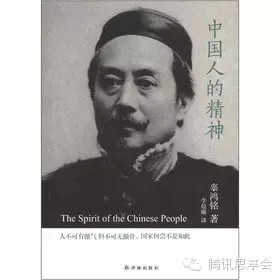
儒學失足

▲馮友蘭
▲馮友蘭與毛澤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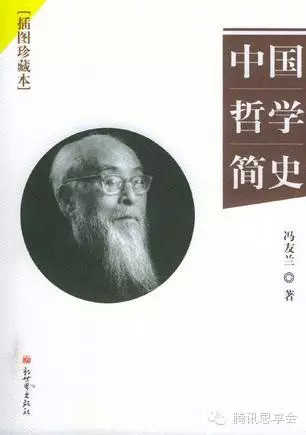
儒門吃“素”

▲錢穆故居“素書樓”
▲《素書》
▲錢穆
騰訊思享會 李冬君 2015-08-23 08:53:44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