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于建嶸:中國農民問題的困境
 |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 簡體 傳統 |
今年3月28日,于建嶸與秦暉、馮興元、王度、朱學勤(担任主持)等人在北京言幾右書店參加《訪法札記》讀書沙龍。通過“觀察中國”,于建嶸先生希望能與讀者分享他們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省思。由于全文較長,觀察中國擇其精要刊發。 感謝于建嶸先生對“觀察中國”的熱心支持。 于建嶸:今天非常高興到這里來。特別是秦暉老師以及王度先生、馮興元先生都過來,朱學東做主持人,應該參加這個活動,而且很高興參加這個活動。 這本書已經寫了6、7年,這與我的工作習慣有關,我做社會學研究,到了什么地方喜歡寫日記,包括今天也會記下來。很多日記寫下來后,很多年后翻出這些日記,當時的思考在今天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很有意義。 這本書是工作記錄,寫作與法國使館有關,早些年他們找我做了一次訪問,按照我的意見去訪問,我說要訪問什么人就訪問什么人,全部是按照我的構思去做,他們沒有指派主題。我當時的構思主要想了解法國的工會和農會,那時候每天找這樣的人,如何談話如何了解。 這本書我想表達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和諧社會必須有明確的法定權利。法國人對自己的權利非常明確,知道什么東西是他的,什么東西不是他的。這點非常重要。 第二個問題,一個和諧社會,當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有一個救濟渠道,必須有司法、有組織、有人幫他。那為什么法國一個工人和一個農民參加了許多組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組織保護他不同的權利,一個農民參加了幾個工會,這個工會管這一塊,那個工會管那一塊,而且工會之間有競爭性,工會保護我的利益就加入,不保護我的利益就不加入,這個工會自然而然就沒有生命力。 所以我訪問了很多工會的領導人告訴我,我們必須為會員服務,否則我們沒有辦法生存。一旦權利受到侵害,有利益的表達,還要有開放的媒體。 書中間有一段話,關于法國共和國宣言。他們說共和國宣言類似于中國的信訪制度。其實完全不是,我問他們一個問題,你們沒有權利,《共和國宣言》調查完之后,怎么發揮作用?他說我們有核武器。什么叫核武器?他說可以通知媒體。什么意思?我沒有辦法對付你,但我可以把你公布到媒體上去。所以有議會,有代表他的組織,有開放的媒體。 我想寫這些東西,根據我的觀察、根據我的想法。當然這本書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考察農會和工會,沒有對法國進行全面的考察。原來我的書的題目是“尋找法國社會和諧的基礎”,因為當時法國發生了動蕩,05、06、07年我都去了,所以這本書也不算什么書,就是一個工作日記。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中國或者對未來社會影響很重要的力量是第二代農民工。 現在大家知道講農民工,從數字來講一億五千萬,真正的農民工第二代是一億二千萬。還有一批人是在城里生長出來的農民工第二代。這兩個農民工跟第一代農民工有區別:第一代農民工是種過地,再去城里打工的,目的非常簡單,是賺錢回家建房子、討老婆、送孩子讀書。 第二代農民工很大的問題是都從學校里出來,這批人有一個特點是對農村、農業沒有多大真正的認識。 我去法國后,跟Jean-PhilippeBEJA有一個對話,書里有寫。到深圳問那些農民工,就問他們對未來怎么構想。基本結論是,我不知道我的未來,但我肯定不會回去。我問那怎么辦?有些人說,假如我想的話,我現在賺的錢,將來找一個老婆,在縣城里買個房子,開個小鋪面。 所以我寫了一本書,叫“漂移的社會”,對農民工第二代的思考,這跟法國社會騷亂的一批移民第二代有關。當時我寫了一個內參,發表在《改革內參》上,我非常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沒有完全得到解決,但有一些分解。今年過年期間我跑了五個市,采訪了農民工第二代的問題。現在看來,這些問題有一些地方都存在,有一些戶口改革后,小城鎮可以隨便進去。 今年調查我發現,有一些農民工在小城鎮買一個地方,開一個小鋪子,逐漸往外面轉移。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認為是一個可以避免的問題,這個過程一直存在,因為社會大轉移,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移,鄉土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移。 不過法國有一個經驗很重要,要不要把這些人聚在一起?我到法國訪問的時候,警察局講了一個問題,把這些移民二代聚集在一個地方是不對的。所以當時我想了一個問題,假如大學生全部聚在一起是一個大問題。所以農民工問題,將來安排移民的時候,地方不應該把他們太分離。 我是反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我非常希望農民工的子弟上學,但我反對建單獨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他們應該跟其他學生融合在一起,而且我反對把那些人都聚集在一起,因為每個人都緊張地工作,那些連擺攤的地方多沒有。當年我訪問安源煤礦的時候,他們說我擺地攤都沒有人,為什么?因為那些人沒有錢。他們應該交叉生活,融入社會。 這個問題的思考,我現在還沒有一個完全的解答,中國這么大規模的移民、流動人口的問題,所以我說在漂移的社會中進不了城市又回不到農村,在城市和農村邊緣漂移,對中國將來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最近幾年我一直呼吁要高度重視農民工第二代和農民工第二代的未來,要重視農民工第二代的未來,也要重視農民工第二代的權利問題。 當然今天也有很多不是農民工的人也在漂移,我們在北京漂移,沒有北京戶口,將來怎么辦?北京買不了房子,可能很多年才能買到房子,這都是問題。這個社會漂移的過程中,會帶來什么問題我認為要觀察,今天誰都難以得出一個完整的結論。 當年廣東發生兩起騷亂時,我趕到廣東,騷亂發生的時間分別是11年6月1日和6月11日,全是第二代四川農民工。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嚴重。但是我的看法是,可能目前又有緩解,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秦暉: 首先祝賀于建嶸這本書的出版,于建嶸走了很多地方,我跟他一起去過一兩次,是我陪他,不是他陪我。但是很抱歉、很遺憾,沒有像他有那樣的心得,而且那么豐富。 法國我也去過幾次,我們對法國農民,我想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第一印象是從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第一句話聽來的,說法國農民是一口袋馬鈴薯,沒有組織,不能代表自己,只能由皇帝代表他,所以把拿破侖三世選上去,法國農民是最反動的。 后來我感覺,今天法國的工人組織能力遠遠沒有農民那么強,歐洲各國的農民現在占總人口的比重其實只有10%上下甚至更低,但他們就能影響整個議會大多數的投票。說實在的,比工人還要厲害。 這些年整個歐洲工會衰落,但是農會很厲害,正好相反。所以我覺得人有沒有組織能力,根本不取決于你是農民還是工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你有沒有權利,因為人本身就是社會動物,從來沒有一個民族不會結社,只有允不允許結社的問題。 我們有些人老認為外國人喜歡結社,中國人就喜歡當魯濱遜,一個人在荒島上跟誰都不搭理,哪有這回事?根本不是。 所以第二個,法國農民問題現在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要說法國有問題的,是于建嶸提到克利希蘇布瓦的一些新移民,從民族構成來講不是法蘭西人,大部分是來自馬格里布地區、來自非洲,從信仰上是穆斯林,從人種講大部分是黑人,這些人成為法國的新移民,他們在法國的權利和怎么融入法國成為很大的問題。 至于法國農民早已經不是問題了,假如有問題也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問題。印象很深的的當年我們加入WTO談判的時候,當時我跟一個法國人(越南裔,歐盟駐WTO多哈和會談判農業和會的歐盟談判代表)談,他跟我說我很不理解你們中國——大家知道在多哈和會中談判其實就是保護農民保護多少的問題,因為歐洲國家有保護農業的傳統,有很高的農業補貼,美國是主張自由貿易的,在多哈和會上為這個事情爭得不亦樂乎。 中國加入的時候,中國理論上要爭取有保護的權利,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待遇,發展中國家的待遇好像是保護的比重應該是15%。美國說不行,你不能享受這個東西。中國最后就讓步,結果我們接受了一個8%的比例。 他覺得很奇怪,你們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左派掌權,為什么向新自由主義投降?我們法國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有15%的保護,你們太墮落了,怎么向新自由主義投降,才8%?為什么不跟我們一起對抗美國?為什么站在美國一邊? 后來我說,你要搞清楚,這個8%其實是我們要爭取一個話語權,我們要代表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們才這樣要求的。我們真正對這個補貼的限額,說實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根本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在WTO談判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取消農業稅,如果真的要講,中國當時對農業的補貼程度是負的,也就是說,我們是從農業那里抽取的,而不是補貼的。當然和現在的情況有點不一樣。 所以對中國來講,農業補貼的力度多少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我們之所以還要爭它,是因為我們要爭取發展中國家代言人的地位,不愿被人列進發達國家而喪失了代表南方一大幫國家說話的老大資格,對于補不補貼根本不在乎,也從來沒爭過這個東西。 其實這位先生還是比較了解中國的,他本人不是法國人,而是越裔法國人,是越南人,當時是越南的一個孤兒,被法國傳教士收養以后帶到法國在法國成長,現在成為法國著名的外交官,成為整個歐盟WTO談判中的首席發言人,他對東方不是不了解,但仍然沒有足夠的想象力能夠想到中國這些事兒。所以我的感觸很多。 馮興元(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這本書我昨天、前天都在看,感受很深。 首先,法國的農民已經實現了英國法學家梅因講從身份到契約的轉換,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標志,發展到現在,農民從身份到契約完全完成了。契約背后就是基本權利。現在法國的農民把很多權利抓在手里,同時抓很多權益,各種福利各種補貼,一手抓權利,一手抓很多的權益(給你的權益)。 這種狀況我幾年前接待過歐盟自由民主議會黨團的成員,里面的法國朋友是議會成員,他們都是支持農業補貼的。德國自民黨的朋友完全不一樣,德國自民黨講經濟自由,這里面分兩派:一派是支持歐元比較少,歐元是集權的標志。一派覺得歐元是減少交易費用的一個機制,應該統一貨幣。 由于希臘危機的出來,兩派沖突加劇,自民黨一部分人退出來,建立了一個另類選擇黨,具體中文怎么叫我不知道,盡管以前我長期研究德國的,但我是研究制度的,后來研究中國問題需要再看。 從德國人角度來看,德國最失敗的三個產業政策為:第一,農業政策,因為需要大量補貼。第二個是船舶業,也需要大量補貼支撐。第三個是煤炭業。這三個的特點都是維持著一個陳舊的產業機構。 產業政策有兩類,一類是支持新機構的形成,一類是支持維護舊的、已經過時的機構。也就是說當你保護落后的,等于你在阻礙新的結構的形成。 法國是一種資本主義制度,產權在私人手里,和“權分”連在一起,所以農業市場是發達的,交易是活躍的,有大量補貼。而且法國是大的農業國,很多產品是過剩的,如牛奶。以前也發生過把牛奶大量倒掉,因為不降價,寧可不賣。 我看于建嶸這本書所講的,中國一看就會想到農業的目標是保障供給,但是實際上不是這回事,農業的目標大概有五個,有供給目標,有安全目標,有生態目標,有觀光目標,有很多。 法國農民說,現在還要給我補貼,給我們生態,生物多樣性都是需要的,這實際上就是公共產品,不是農民自己的事情。我維護一片綠地或者樹林,樹林相當于人類的肺,這不是我個人要用,而是整個法國和整個地球都需要,是一個公共品。怎么看補貼?剛才講的補貼有一定的正當性,在生態方面,如果服務這個目標的話。 第二,如果是農業科技,新的科技,由于最初投入大,而且法國農民主要是家庭農場,跟德國一樣,所以你讓家庭農場去搞科技創新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組織化的,如合作社、農協。法國有三個組織非常有意思,書里寫到:農業議會、農業工會、農民協會。 法國除了行會性質的,其他都是自愿參加的,那個非常好,不像德國那種,我們叫做社團社會主義國家,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是法定的,大家都要參加,德國工商會就是如此。法國工會發展非常大,但看這本書,人數好像只有二百萬,很吃驚,沒想到,因為法國工會罷工時的破壞力遠遠大于德國。 去年我在德國,正好碰到德國聯邦鐵路罷工,不是全部罷工,而是把干線給斷了,把你的時間表全部打亂,因為只要斷掉一部分,在購票機買的票顯的時間就不對,說沒有這個線,沒有這個線也能到,因為德國的火車票是在某一個站可以轉達,同一張票,很簡單,但很不舒服,包括你通知朋友的時間全部亂了。 飛機也是如此,原來是坐漢莎,取消了,火車的時間不行了,要轉到柏林航空公司,沒坐德國之翼的飛機。這些讓你不舒服。法國的工會破壞力非常厲害,估計法國企業家會非常怕罷工。 王度(藝術家,長期居住巴黎): 關于法國社會、法國農村、法國文化、政治方面的話,都是非常好,我覺得他們理解我的國家比我理解的還深。既然來了,我說幾句話。 第一,我聽他們三位說的有些非常對非常正確,有關是法國農民、農村、農業各個方面的重要性都非常大,文化方面、社會方面、政治方面都非常重要。雖然今年在法國做農民而且做農業人的數量并不大,很少,但他們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三位老師都提到這一點,法國做政治的人、政治家,尤其是法國總統都非常尊重,甚至有的時候很怕農民的想法,農民會說什么話。 比如在法國每年會在農業館舉辦很大規模的農業展覽,邀請法國各個地方的農民、做農業的人到這里介紹他們的食品。法國所有政治人,不管男女不管年齡,都一定要去參加這個活動,表示他們對農民的尊敬和關注。這個肯定是一個政治現象,也是社會現象。 現在法國城市化過程已經很完整,但是農民還是很重要,每一個法國人有機會,你知道法國人夏天放假時間比較多,肯定都會回到自己的老家看自己的祖先原來住的地方。這個現象跟中國有些像。 我從來沒住過法國農村,但我的爺爺奶奶、外婆外公都是農民,我們從住的地方回到他們那邊,每年幾次去那里看一下,跟住在農村的人說話,了解到農村的問題,以及他們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這非常重要,沒有這樣的機會,可能我們不認為我們是真正的法國人。 剛才秦老師說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從非洲移到法國的人,遇到很多障礙,包括受歧視方面的問題,可能跟文化、宗教、民族有關,可能也因為他們在法國沒有自己的農村、自己的老家,沒有根,這是一個障礙。 我的母親從法國西北部來的,他們有自己的語言,這些人一百年前移民到巴黎時有各種各樣的歧視,當地人看到他們不是真正的法國人。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怎么讓別的國家移民到法國,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主要的。 農民農村之所以有政治重要性、文化重要性、社會重要性,我覺得在很多法國人眼里,也是那種能夠保持法國的傳統、法國的文化,以及法國很多很重要方面的問題。所以每個人回到農村時,會特別尊敬,因為他們懂每個地方的歷史、每個地方原來的傳統、每個地方的方言、每個地方的一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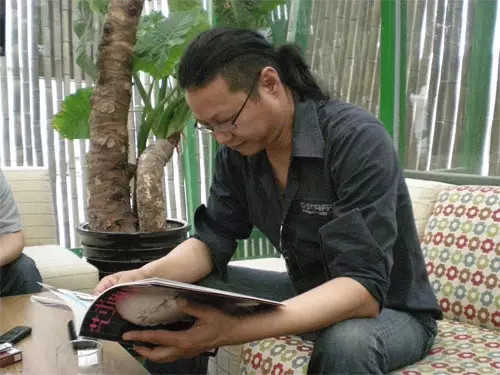

觀察中國 2015-08-23 08:54:29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返回列表

